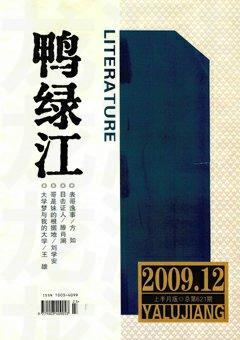遙望那尊青銅雕像
楊沛霖,錦州人,退休干部,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先后在省市級和全國性報刊發表文章五十余萬字,有的收入省作協編撰的《建國五十周年遼寧優秀文學藝術作品系列叢書〈散文卷〉》等集子中,出版了《寵辱不驚》等四部散文隨筆作品。歷任清原滿族自治縣常務副縣長、縣委副書記(兼),撫順市農牧局長,撫順市人大常委會委員、農經委主任等職。
春秋這段歷史,如果從公元前770年周王室東遷洛邑,諸侯爭霸始,到公元前475年越滅吳,七國并立迄,經歷了近三百個寒暑。其間百家和列國,學術和刀劍,雄辯和陰謀,游說和兼并交織在一起,有對話,也有碰撞,波譎云詭、風雷激蕩。
在這個星漢燦爛的時空里,春秋先哲們衣冠臨風,芒履倥傯。或馳騁沙場,龍驤虎躍;或折沖樽俎,縱橫捭闔;或運籌帷幄,挽狂瀾于既倒;或窮天地之理,宇宙之道,而為一家說。總之,宰輔將相,士子布衣,各自演繹著自我的角色,書寫著歷史經典。
相位傾圮 慨而當之
有一個春秋人物,當時以至后來,好像都沒有大紅大紫,可他身上有種東西卻吸引著我穿過兩千多年的時間隧道,走近了他。于是歷史深處,地平線那邊,一尊青銅雕像遠遠地進入了我思想的視野,質地斑駁,色彩黯淡,隱隱地散發著溫暖和情感,招呼我隔著歷史的門限作幾句交談。
這個人是子產,姓公孫,名僑。鄭國人,生年不詳,卒于公元前522年。他與老子、孔子同時代,老子早于他一二十年,孔子晚他十余年。孔子周游列國到鄭時,子產垂垂老矣,沉疴纏身,不足一年就辭世了。兩人見面否,未見史載,不敢妄說。但子產卻進入了孔子的眼界,孔、孟都有關于子產的記述。
子產的故國鄭,是個小國,位于現在河南新鄭一帶,夾在楚晉兩個大國之間。春秋后期,周王室衰落,諸侯國爾虞我詐,弱肉強食。據史料載,春秋期間,東周王國以外有姬、姜、媯等諸姓諸侯國一百七八十個。到子產時少多了,但兼并的險惡形勢沒有多大改變。晉、楚、齊、秦,以及后起的吳、越是一等國,魯、宋、鄭、衛是二等國,陳、蔡、曹是三等國。戰亂不斷,烽火連天。因此當魯襄公三十年,簡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3年),鄭國內訌,大政(相當于總理)伯有被殺,擬議子產接任時,他猶豫了。當時子產是少政(相當于副總理),不僅有社會基礎、政治影響,又沒有卷入這場惡斗,是最合適的人選。大族領袖、資深大夫子皮(名罕虎)找他談時,子產不無惶恐地說,干不了。原因有二:一是國家小,夾在大國間,強國虎視眈眈,隨時有被吃掉的危險;二是國內有權勢的大族多,各立門戶,驕狂自大,難以治理。子皮是個有遠見的政治家,有備而來,成竹在胸,他說:“虎(即子皮)帥以聽,誰敢犯子?”是啊,這個元老級資深政要率領大家聽命,還怕什么?還說:“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一番話既有見地,又蘊哲理。大約兩人都有志在天下的抱負,心有靈犀一點通,子產接了這個擔子。
擇能而使 鮮有敗乎
這個“善相之”說起來容易,做就難了。誰不想做個好官,留名青史?可要做到,除了高尚的人品和風骨外,還要有智慧、勇氣、實事求是的作風,缺了哪方面都不可以。子產上任第二年,還是這個子皮找到子產,要安排叫尹何的年輕人擔任采邑長官。子產了解情況后,搖頭說:“這個人太年輕,還不明事理,干不好,不行。”子皮不甘心,做工作說:“這個人老實,為人忠誠,不會違背我的意志,我喜歡他,讓他干吧。邊干邊學,會做好的。”
子產毫不松口,明確地說:“不可以。”接著講了一通大道理:“喜歡一個人,愛一個人,都是給好處,給利益。今天您給官,讓他辦政事,這不妥。還不會操刀,就讓割肉,會傷害自己。本來愛人,卻把人傷了,誰還會求您?”意猶未盡,又舉了兩個生活中的例子,“子有美錦,不使人學制(有好布料,不能讓人學手藝)。”“求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一開始登車就想射獵,不可能有收獲)。”最后還說了幾句充滿感情的話,“您是鄭國棟梁,做錯了事,讓人議論,你不好,我也不好。”子皮聽了,心悅誠服,慚愧地說:“善哉,我糊涂。”還發了一番做人的感慨,成為流行于世的箴言:“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吾小人也。”
歷史記錄了這件事,名之為“學而后入政”。掩卷思之,頗有深意:和諧不是沒有分歧,沒有矛盾,沒有個性。和諧是秩序,是人生境界,是人際關系和社會氛圍,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相處的法則。和諧需要包容和尊重,也需要堅持和守護,有時后者比前者還重要,還難做到。
其實,子產不惟重才,也善用人,《左傳》上說他“擇能而使”。馮簡子擅長決斷;子大叔能辦事;裨諶好謀,尤喜野外靜處獨自思索;子羽熟諳諸侯國情,且長于辭令。史料載,“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子產賢者用,能者任,惟才是舉,成為彼時的一種政治生態,社會景觀。
善否之議 可為師焉
當時民間有一種叫“鄉校”的地方,前人注釋為地方學校,可以在“鄉校”“以論執政”。有點像民國的茶館,喝茶聊天,且沒有“莫談國事”的約束;也有點像西方的“沙龍”,不同政見者談吐揮霍,各抒己見。宋司馬光在其《諫院題名記》中說:“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這可能是當時的一種氣象。
他上任的第二年,一個叫然明的政要,向他提出:“毀鄉校如何?”要除掉這個社會細胞。子產說:“何為?(怎么能這樣呢?)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他還有更深一層的思考,“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他把聽批評意見,看成防川,防大水,看成吃藥治病。這兩個俗常的比喻,好像淺陋了些,卻說到了本質。其實,本質總是簡單的,但與深刻并不矛盾。難怪嗣后孔子說:“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產的為政理念,傾向于“猛政”。對這一問題,他好像有過認真的思索。在人生大幕落下的前一年,他對子大叔說:“我死,子必為政。”還留下了“論為政寬猛”的意見,供子大叔參考。他說:“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大叔初為大政,“不忍猛而寬”,出了問題,吃了虧,復又接受了子產的理念。孔子從經世濟民的角度,借此闡述說:“善哉!政寬則民漫,漫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寬猛”之說,見仁見智,姑且不論,卻體現了他的施政本質、核心、出發點和落腳點。他汲汲以求的是社稷和天下,黎民和蒼生。這和前邊不廢“鄉校”是一致的,前者“知”,后者“行”,兩者是統一的。
茍利社稷 生死以之
子產上任后,推出了一系列富國強兵的措施。先是“作封洫”,改革田制,整頓田地的邊界、溝渠,以什伍編制農戶,以田畝納稅。魯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又推行“作丘賦”。原來屬于大貴族(采邑主)的屬民,只對采邑主進貢,不承擔國家義務。改革后,要服兵役,向公室繳納軍賦。這些改革促進了社會發展,得到了黎民百姓的擁護,卻侵犯了豪門貴族利益。“國人謗之”,往他身上潑臟水,說他父親被殺死,變成了蝎子的毒尾巴。由這樣人的子孫治理國家,有什么好處?他沒有驚駭和不安,他說,民心不可放縱,法度不可改變,還講了治國和執行法度的道理,表示“吾不遷矣”(我不會改變做法的)。還說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茍利社稷,死生以之。”
讀到這八個字,便怦然心動,不能自已。這是炎黃子孫不變的風節,中華民族永恒的精神。由子產始,以至蜀漢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氣節,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操,近代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抱負,以及溫家寶當選總理后在記者招待會上,引用林則徐這句話的自勉……仿佛有一條河,人格的河,文化的河,民族精神的河,波瀾壯闊,奔流不息,不斷有活水流入,也有流出,流向心靈的綠洲,道德的森林,以及中華兒女人文精神和生命價值的高地。語言是文化流動的線索,子產這句話,正是濫觴。他一生都在實踐這八個字。至圣至道,庶幾近矣。
“鑄刑書”,是子產又一超凡脫俗的政舉。公元前536年,他執政十余年了,決定把法條鑄于銅器上,有點后來的商鞅立木為信、劉邦約法三章的意思,也有點如今“公示”的味道,讓大家都知道,以收公開、公正、公平的社會效果,使社會管理和國家機器運行走上法治的軌道。
公布伊始,便遭致各方面反對。首當其沖的是晉大夫叔向,他是晉國大政,本是一位開明的政治家,“外舉不棄仇,內舉不避親”是他提出來的薦才原則;“叔向賀貧”,惟“憂德之不建”,不“患貨之不積”,是他留下的道德佳話。然而“鑄刑書”他卻接受不了,寫了封長信給子產,阻止“鑄刑書”的實施,把子產的“刑書”和三個前朝亡前的刑書,聯在了一起,詛咒曰:“吾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子產心如石鐵,答復叔向說:誠如君言,可我不敢接受您的勸說,也不會忘記您的關懷。我不是有大抱負的人,不想身后以及子孫怎么樣,最緊要的是當世,為黎民百姓做些事啊。
執拗的子產,一生走在改革的路上,歷盡艱難,不屈追索,這大約是古往今來一切大圣大賢生命的基本造型。
縱橫并行 睦鄰安邦
外交是用政治方法解決矛盾和糾紛,政治解決不了,就要訴諸戰爭;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最后的方法、手段和了斷。那時小國無外交,弱國也無外交。子產面對這樣的挑戰,以“小國忘守則危”警誡自己,主動進取,長袖善舞,留下了許多可圈可點的佳話。
上任翌年,子產陪同鄭伯(鄭的國君)訪晉。晉侯以魯襄公亡故為由,不予接見。禮節也很輕慢,客舍差,門戶小,車馬進不去。面對這種情況,子產拆了墻垣,大搖大擺地把車馬趕了進去。晉宮一時大嘩,晉侯派大夫士文伯問其咎。子產鋒芒不露,以退為進,從容地說,小國不容易,介于大國之間,誅求無時,少有安寧。我們盡心盡力地收齊了貢賦,趕到這里,卻不接見。貢品既送不到庫里,也不敢暴露外面,實在為難呀。他請求士文伯指教,不拆墻垣,貢品損失了是誰罪過,誰又擔當得起?士文伯把子產的話轉給了晉侯和趙文子等大夫們,大家爭吵了一氣,意見統一了,子產說得不錯,遠來朝貢,為難人家,確乎不妥,便認了錯。
公元前526年三月,晉國派韓宣子使鄭。宣子有個玉環,配對的另一個在鄭國,他想借這個機會得到。這是國寶級文物,韓宣子拜見鄭伯時,提出買玉環。子產接過話說:“非官府之守也,寡君不知?”替鄭伯婉拒了。同朝的子大叔、子羽勸他說:“韓宣子無所求,晉也沒有貳心。晉和韓宣子都不可怠慢。若有人進讒,翻了臉,悔之晚矣。何惜一環,惹大國不滿。還是給了吧,以求免災。”子產搖頭說,大國貪得無厭,要什么給什么,給不起呀。不節制他們,讓國寶流失,是失職。他還指出,韓宣子假公濟私撈好處,也是罪過,不好幫這個忙。韓宣子碰了壁,便換了路徑,找了玉環的主人。主人很聰明,推辭說,這件寶物要有國君或大夫同意才能出手。無奈,復又回來找子產。子產正色說,我們當初建國時,鄭桓公與商人從周地來到這里,蓽路襤褸,歷盡滄桑,建成了家園,盟誓說,不該買賣的東西不能交易;進行交易,不得強買強賣。憑著這個盟誓,國家才保以至今日。現在你以使者身分,讓我們背棄盟誓,恐怕不好吧。韓宣子明白了鄭的態度,放棄了這件事。
孔子在《論語·憲問篇》精細地記述了子產的外交風度:凡有出使或接待活動,都預有準備,先由裨諶起草方案和文書,再由子大叔主持討論,然后子羽修飾,最后子產自己潤色定稿。孔子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中贊嘆子產:“古人說,‘言語為了表達意思,文飾為了表達語言。不說話誰知道你的意思,說話沒有文飾也傳不到遠處。子產文辭傳得遠,因為他有準備。”范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簡編》中寫道:“《左傳》宣公十四年,所謂‘鄭昭(明)宋聾(愚鈍), 說明鄭是個機智的國家,在這個國家里,產生了法和縱橫兩家,子產是這兩家的創始人。”
鬼神虛緲 非所及也
子產負載著社稷使命,自然會遭遇來自社會層面的沖突和障礙。他在對立中尋求統一,矛盾中化解沖突,從容自然,像水結為冰,冰化為水那樣存乎一心,運用自如。
那時,人類剛從蒙昧原始中走出來,崇拜天地自然,尤其迷信鬼神。有人裝神弄鬼,吃這碗飯騙人,時稱“巫祝”。
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低,用火粗疏,火災不少。鄭人一次大火,“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這樣常有巫人預報火險,也有“蒙”對的,對也好,錯也好,子產向不理睬,反對事鬼敬神的愚昧活動。他認為,“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巫祝)焉知天道,是以多言矣,豈不或信?”這是彼時的科學吶喊,兩千多年前的無神論宣言,歷史上第一次對凌駕于世俗社會的迷信活動的嚴肅批判。一二十年后,孔子也發出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勸誡。人類的歷史,從來沒有停止過對這種愚昧行為的斗爭。
可是,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和心理,不是一時或幾個人的聲音能夠改變和顛覆的。子產遇到了這樣一件事,謠傳因內亂被殺的前任執政伯有,化作厲鬼來報仇雪恨,鬧得人心惶惶。面對這個混亂局勢,子產沒有簡單行事,而是另辟蹊徑,把伯有和另一位被殺大政的兒子立為大夫,重用了所謂“仇家”抑或“冤家”的后人,借助社會意識和信仰的力量,把人們的思維和輿論引向積極方面。這種順其自然的做法,果然有效,很快消彌了風波。子大叔問其緣委,他說:“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似禪似讖,如誑如謔,子大叔還不明白,繼續追問,他說: “找一個借口向大家解說。從政有時也得反著來,順著老百姓路子,不順著不信服你,就不跟你走了。”他出使晉,趙景子又問起,他說了更深一層道理:所謂魂魄“憑依”,是心靈感覺,自己制造幻象,安慰自己的心靈,我利用了這種心理。
是呀,一個人無論如何不能和整個社會對立,哪怕你是對的,真理在你手里。孔子說“從眾”,怕也是這個道理吧?子產是智慧的,他在陳俗和文明的平衡中,找尋傾斜和突破。在他的形而上的世界里,傾斜和突破是永恒的。
邢山石塚 千古廉相
春秋后期,我國開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私有制有了進一步發展。財富和貨幣的價值,決定物質生活,也決定社會地位。可是即使那時,也不得假公濟私,聚斂財富,巧取豪奪,中飽私囊,不然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不會有好下場。這個道理,抑或規律,見諸文字傳承下來,好像也是始于子產。魯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晉大夫趙宣子為政,加重了諸侯國的貢賦,“鄭人病之”,其他諸侯國也不堪重負。這時子產還不是大政,他給趙宣子寫了封信,陳述利病,大約說到了要害。受了大沖擊大啟發,趙宣子接受了意見,改變了做法,這是不容易的。信的內容不復贅述,有兩個觀點卻不能不提及。一是“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他是說,搜刮上來的東西留在晉國,諸侯便會對晉離心離德。留在你趙宣子手里,晉國人便會對你離心離德。諸侯離心離德,晉不會有好下場。晉對你趙宣子離心離德,你也不會有好下場。這里的“賄、貳、壞”三字,泛指行為也好,心理也好,抑或人生命運也好,昭示了相系相依、勢在必然的邏輯關系。這封信里還有一句話,意義更普遍,內蘊更深邃,他說:“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象因為有貴重的牙齒丟性命,聚斂不義之財,也會自焚其身。這些話已歷兩千余年,還活在我們的語言中,除了深邃的內含是人生和社會的需要外,還會有別的解釋嗎?
子產廉潔自守,家風淳厚。《賈氏說林》云:“子產死,家無余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亡。丈夫舍玞佩,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數計。其子不受,自負土葬于邢山。”酈道元的《水經注》有云:“子產墓在水上,累石為方墳,東北向鄭城,示不忘本耳。”
到了公元前522年,他在大政的職位上,慘淡經營,夙興夜寐,歷二十六個年頭了。果如其言,“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 鄭進入了太平盛世。他初為大政,實行改革,傷害了貴族和上層利益,傳誦說:“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后,又誦之說:“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成為一種信賴,依靠,老百姓心目中誰也代替不了他。《史記·循吏列傳》說,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年輕人不輕佻胡為),斑白不提挈(老年人可以賦閑),童子不梨畔(孩子不用下地干活)。二年,市不豫賈(做買賣講信用)。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農具放在外面)。五年,士無尺籍(沒有戰亂,得不到戰功),喪期不令而治(遇有喪事自覺執禮)。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左傳》云:“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更有清史學家王源說,子產堪稱春秋第一人。難怪讀子產,總有一種留連風景,意猶未盡,曾經滄海,除卻巫山的心情。
春秋,屬我國的青銅文化時代。青銅器的出現和使用,是生產力水平的標志,人類文明的一個起點。郭沫若先生說,周朝的青銅器是一種文化,歷史的文明。到戰國時,秦始皇不許民間留有武器,收去銅器,鑄了十二個銅人,從此鐵戰勝了銅,結束了這個時代。兩千多年過去了,歲月風云已經飄散,可總有一尊雕像,聳立在思想的原野上。它是文化的存在,人格和道德的抽象,先人關于理想、追求和生命價值無聲的詮釋。它從《左傳》的故事,《史記》的述說,《論語》和《孟子》的雋句中走來;從先秦的龜甲卜辭、銅鼎銘文中走來;它從遙遠的邢山走來,從累石為方的土隴中走來。我望著他,他也注視著我,視通萬里,思接千載,娓娓地訴說著歲月風云和世事蒼桑。
他是子產。相去遙遠,卻還活在我的世界中。
責任編輯 牛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