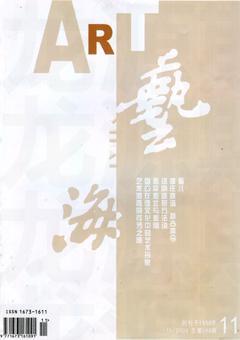舞美形式本體構成
譚 捷
舞美外部形式的本體,是以最基本的構成元素與舞臺空間的有機結合所構成的,元素與空間,二者缺一不可。舞美形式在戲劇藝術中多樣性的體現,其構成原則都不能背離本體意識,否則,舞臺美術就不復存在。戲劇舞臺空間不僅是戲劇內容賴以展示的必要條件,也是構成元素用以結構與表現舞美形式的決定因素。
元素與發展
舞美形式的構成元素是什么?有專家已準確定義為“線、形、光、色”,中國傳統戲曲舞美形式的守舊、砌末、臉譜、戲服等都充分體現著線、形、色的元素成分,而且,以色狀物在戲曲藝術中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表現手段,如:白旗為云、藍旗示水、紅旗狀火等,戲服亦有上五色與下五色之分,白色一般體現少年英雄,綠色表現忠誠,關公的鎧甲就只能穿綠色,其戲服的色、形與人物之間有著較嚴格的相互對應關系,行話謂之為“寧穿破 不穿錯”,絕不能隨便穿戴。“光”被引入舞美形式構成元素后,形成了“舞臺燈光”這一概念。
當代戲劇藝術相繼引入的音響與電聲效果,材質特性、數碼信息等因素,致使舞美形式的構成元素依隨時代與科技的發展,亦在有選擇地充實,這對舞美形式的發展創新有著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燈光在舞美形式的發展創新中越來越重要,已完全擺脫了燈光僅為舞臺照明的時代。舞臺氣氛與色彩,以及光色的流動,在較大程度上都是由“光”元素來完成。湘劇《李貞回鄉》就是以高科技數碼燈的精確控制與變換來進行時空轉換和氣氛渲染,其效果十分流暢自然。以舞臺布景表現形態來說,從最早傳統刺繡圖案的工藝性,到現代戲布景單一的繪畫性手段,已發展到今天的綜合性。綜合性的內容大致包括了工藝性、繪畫性、制作性、材質性、光電性、數碼性諸多表現方法與藝術手段,其藝術表現力更為寬廣靈活。花鼓戲《作田漢子也風流》中的現實環境與人物心理空間多次的有機轉換,就是運用三棵流動的樹來完成。這三棵立體樹的樹葉采用有韌性的包裝防震材料來制作,其優點是輕巧、不易破損、受光性好、易上色等。此材料本身就有半透明的晶體結構感覺,在數碼燈的色光下,呈現出一種晶瑩剔透的絢麗美感,如用傳統材料來制作,則無法達到和塑造出這種爛漫的氛圍。總之,正是因為構成元素的發展,舞美形式在創造中才有了縱向繼承的發展與變化和橫向借鑒的融合與多樣。
空間與開拓
關于舞美形式的創作,曾有個基本理論強調構思中的三性,即:形象性、有機性、交代性。筆者理解為:即感情的形象思維;舞臺行動、矛盾沖突與舞美形式邏輯的協調統一;對典型環境直觀性的具體表現與刻劃。現在看來,這一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舞美形式的創造,阻礙舞臺空間的拓展,影響當代戲劇藝術的創作思維、藝術方法、表現手段的發展與更新,其創造意識應從“交代性”中解脫出來。對戲劇環境與空間的塑造不能只單一地在有限的、靜止的物理空間強調表現直觀性或幻覺效應的形象。有形象不等于藝術,沒有相對的抽象就沒有藝術,帶各種規律的形式感是一定的抽象,抽象就是藝術的概括,這在舞美創作中很重要,有與無,虛與實可以相互轉化。
戲劇舞臺空間的拓展對舞美外部形式構成的重要性已為當今設計師們所重視,已成為一種基本的創作主導思維。舞臺空間的定義,是具象物理空間與抽象空間的統一體。人物心理空間的展現,意識流空間的外化表述,時空有機轉換或時空淡化,音響空間的運用等都屬于抽象空間。在空間的屬性上,具象與抽象不是絕對分離的兩極,抽象空間與表演結合后可轉化為具象空間。然而,這種具象空間并不是表象的、形似的、幻覺的物質感官關系,而是一種“存在”所給予人可以感覺到的意識領域——可感性,空間的運動與形象的可感性是舞美形式創作中值得深入探究的層次。“舞臺的運動空間概念可以解決生活的無限與舞臺的有限之間的矛盾”張庚先生的論述闡明了有限的存在與無限的意識聯想之間一種和諧的辯證關系。
有人亦提出戲劇舞臺時空觀要由明確性時空向模糊性時空拓展…… 所謂“模糊性時空”,并非時髦與新潮,中國傳統戲曲的時空觀就是虛擬性的相對模糊,它的時空轉換與寫意性的“環境”體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藝術表現的自由。虛擬性與假定性以及隨之反映出來的隨意性和模糊性雖不具備確定意義,其時空概念哪怕沒有物質外化的提示或暗示,但依托戲劇情節與人物行動的發展,對演員和觀眾來說,卻是非常明確的。“景隨人轉”、“境隨意變”即為此理,這種“景在演員身上”,“景在觀眾心中”的時空概念所具有的模糊性亦能折射舞臺時空的多義性,能化有限空間為無限空間,這也是戲劇舞臺時空所具有的的象征性特征。
當代戲劇的舞臺時空已由單一性時空向多元或多維復合時空拓展,但設計師不可獨立地去追求在舞美形式創造中舞臺空間的怎么個處理,戲劇個體的時空處理應有其形式邏輯的內在必然性,也就是戲劇藝術綜合性的協調統一。
(作者單位:邵陽市花鼓戲劇團)
責任編輯: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