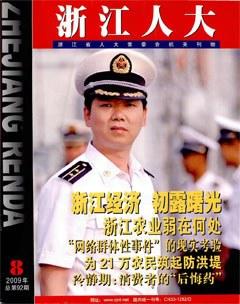保密和公開的角力
蘇永通 趙 蕾
互聯(lián)網時代,保密形勢在各國空前嚴峻。不僅中國,世界大國的保密制度均趨于越來越嚴苛,包括注重信息公開的美國。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于2009年6月22日對保守國家秘密法修改草案進行了審議。權威人士表示,這次修改主要是因為信息化的快速發(fā)展,以及電子政務的建設與應用,讓保密工作出現(xiàn)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
近期,澳大利亞力拓公司駐上海辦事處4人被上海市國家安全局以涉嫌竊取中國國家秘密拘捕。泄密造成的巨大損失又一次刺痛了人們的神經。
與此同時,一場2。年來罕見的保密檢查正席卷全國,不僅包括黨政機關,國有企業(yè)也在其中。不久前,國家保密局舉辦地方保密大檢查高級研修班,預示著地方大檢查也將拉開帷幕。
系統(tǒng)內稱之為“保密風暴”。2008年2月至9月,90個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委,接受了一輪拉網式排查,重點是計算機和移動存儲介質,某些要害部門一年內被查了4次,至少已有22人在這次風暴中受到處理。
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頒布實施,使得政府信息公開逐漸成為滿足公民的知情權的基本方式。在最新的保密法修改中,一方面參與討論者提出縮小定密范圍、防止濫用定密權等主張;另一方面修法者也強調了“越開放,越要保密”的主張。
保密與公開在中國延續(xù)了十余年的博弈,在新形勢下面臨著一場全新的角力。
秘密范圍遭受質疑
1998年,某省一農民因接受境外電臺采訪,被判“為境外非法提供情報罪”,所指的情報是當地的一起普通綁架撕票案。法律專家批評某些人扭曲解釋了保密法的“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
相反,某些真正的國家秘密,卻被扔進垃圾堆里。9個福建漁民,長期鉆在駐軍和軍校附近的廢品堆里挑挑揀揀,僅被截獲的就有數千份軍事資料。據了解,近幾年,廢品站成為保密檢查的重點。
據統(tǒng)計,中國每年產生數百萬份秘密文件,美國僅有10萬件。保密系統(tǒng)流傳一則笑話,說境外間諜對來自中國的情報非常頭疼,因為數量驚人,且大部分無密可言,為了不錯有價值的信息,他們又不得不緊盯住每一張紙片。秘密文件之多,由此可見一斑。
有專家表示,秘密文件過多過濫,不僅增加了保密成本,也影響了國家保密制度的權威,更重要的是,阻礙了政府走向信息公開的道路。
國家保密局在修法說明中提及,縮小國家秘密范圍是修改方向之一,但目前對于國家秘密,草案仍維持20年來一直備受批評的籠統(tǒng)定義和寬泛列舉。
國家秘密誰來認定?不服認定怎么辦?長時間不解密怎么辦?這些問題,草案均沒給出答案。而這些恰是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實施后,亟待保密法作出配合修改的核心內容。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后,“國家秘密”成為很多部門拒絕公開信息的重要理由。
現(xiàn)行保密法規(guī)定:“國家秘密是關系國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確定,在一定時間內只限一定范圍的人員知悉的事項。”而框定秘密范圍的7條事項,包括國家重大決策、國防、外交、國民經濟、科技和國家安全,最后一條“其他國家秘密事項”,可涵蓋各個領域。許多人認為,“利益”的解釋易被擴大。
據悉,與宣傳、推進多年的“陽光財政”相悖的是,1991年下發(fā)的財政部、國家保密局《關于印發(fā)<財政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范圍的規(guī)定>的通知》中,機密級事項包括:“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計劃單列市中、長期財政收支計劃、年度收支計劃、預算、預算執(zhí)行情況和決算。”
又如,災害“死亡人員總數”在2005年8月8目前確屬國家秘密。這也就不難理解,在2003年SARS事件中,官員被撤換后的數字劇變給人們帶來的沖擊。
而關于內部規(guī)定以及內部文件、敏感信息,其界限則更為模糊。
某部委信息辦主任告訴記者,在信息公開中,涉密文件反而容易處理,最難處理的是一些看來不適合公開的非密文件或事項,有些工作秘密未上升到國家秘密層次,但公務員法又要求公務員要保守工作秘密。讓許多政府工作人員煩惱的是,如何給申請人一個說法。
而有些官員,則沒有這樣的煩惱,他們還是習慣性地認為:“凡未公開的信息都是國家秘密。”
草案一審中,有委員指出,要盡量縮小國家秘密的范圍,特別是要分清工作信息和國家秘密。有委員援引惠及幾億農民的中央一號文件被某些地方定為密件為例,說明定密之亂已經影響政策貫徹實施。
北大教授姜明安建議立法機構可考慮,在秘密范圍難以具體確定情況下,列舉財政預算等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應公開信息。
縮小國家秘密的另一個方面是明確定密責任。草案一審中最受委員關注的是定密責任人制度,但草案僅強調人員責任,縣級以上機關單位享受定密權的規(guī)定未變。這與一些學者建議參照的美國“定密官”制度相去甚遠。據了解,美國聯(lián)邦政府原始定密官僅4000多人,須經總統(tǒng)行政命令或特別授權才有定密資格。鑒于此,有委員建議提高定密層級,主要集中在中央機關層次,而且要集中在重點的單位,對隨意定密的追究法律責任。
“越開放,越要保密”
由于信息公開與保密二者之間“此消彼長”的特殊關系,國外一般將保密立法與公開立法結合起來通盤考慮,比如美國《保密的國家安全信息》規(guī)定了3類禁止保密情況。而中國的保密和公開是分開立法,所以,保密法更加注重保密在情理之中——一位保密系統(tǒng)人士如此解釋。
提交一審前的最后一次座談會由中國法學會信息法學研究會組織。據與會者稱,會上,有個別專家說:“保密法是規(guī)定保密制度的,應以保密為原則,公開為例外!”此觀點遭到了許多專家的“炮轟”。
還有專家建議改“保守國家秘密法”為“國家秘密法”,以利于涵蓋整個立法,包括公開的內容。
尷尬的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屬于行政法規(guī),其位階低于保密法,依立法一般規(guī)律,本應按信息公開精神先修改保密法,再制定公開條例,然而由于種種因素,最終在保密法尚未修改的前提下就頒布實施了公開條例。
特別是定密環(huán)節(jié),實際上國家保密局也將此定為解決公開與保密矛盾的突破口。保密局法規(guī)室的同志認為,定密是一項源頭性工作,只有定密準確,才能既保障國家信息安全,又促進政府信息公開和信息資源合理利用。
“作為保密法上的秘密事項要盡量特定化。只有當事人能夠知道是絕密、機密、秘密的情況下,要求當事人保密才有點道理。但現(xiàn)在我們不知道一個東西到底是不是國家秘密,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在北京大學人民代表大會與議會研究中心于2009年4月召開的信息公開與保密法修改的理論研討會上,北京展達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澤指出,一個人只有明確知道這個國家秘密并泄露它才有可能是違法犯罪行為,但很多人不可能知道。這導致我們在對外提供任何信息的時候,都會有一種恐懼感。保密法這樣恐怕就成了一部恐怖法,讓當事人人人自危。
“如果沒有密級的異議和糾正機制,當事人權益難以得到保護。”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姜興長委員建議在保密法中增加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渠道。據記者了解,救濟程序或會寫入二審的草案中,制定國家信息公開法也在立法機關的考慮范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