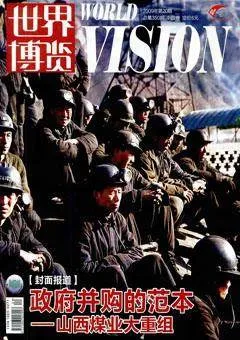難忘的“錦標賽”體制
上世紀50年代,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曾對中國經濟、社會,乃至政治造成過致命的打擊。中外很多學者都曾試圖找到這一幾近瘋狂的全民運動的誘因,并先后給出了多種答案。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周飛舟教授認為,單純的個人或人事因素是不足以解釋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的,而應該挖掘更深的制度原因。他在《錦標賽體制》一文中,借用經濟學中“錦標賽理論”,對“大躍進”進行了分析。
“錦標賽理論”是公司管理中委托——代理關系的激勵機制,對因為存在高昂的信息和監督成本,公司的委托人對于其代理人——公司的高層經理人實行了一種拉開薪酬差距、通過考察其業績排名而非實績的辦法來選擇誰能夠獲得晉升。雖然政治體制較公司而負責許多,但地方與中央的關系與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關系有可比性,而各地方政府之間也存在著某種競爭關系。
整個“大躍進”運動就如同一場錦標賽。中央是競賽的發起人和目標、規則的制定者,地方則是參賽的運動員。跑在前面的、勝出的運動員不但會享受到更多的經濟政策方面的偏向,地方政府的領導人也會由此得到政治榮譽以及晉升。落后的運動員會被批評為執行中央路線不積極甚至執行“右傾”路線,中央與省級政府間的這種關系在省以下各級政府間被進行層層復制和夸大,致使錦標賽在各級政府間全面展開。
周飛舟認為,“大躍進”不僅僅是毛澤東的個人思想導致的自上而下的動員過程。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實際上會內生出大規模放權和開展地區間競爭的要求,作為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的手段。在1957年毛澤東發表反對“反冒進”發言之前,由于一五期間社會主義改造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權,已經從某種程度上制約了地方經濟的發展,過度剝奪了地方的財政權利。當“反反冒進”講話出臺,馬上得到了地方政府和各企業,從下而上的積極推進。
R6i55DvaStkX7XVs6Y5oQr+4nRcY7oLZlDKfSwr/pxM= “大躍進”這場錦標賽有三大特點:第一,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決定了這場錦標賽的基本走向。地方政府變成了追求指標和效率的巨大公司或廠商,動員其所有能夠控制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實現高指標。評價地方政府表現的標準變得簡單清晰,效率成為最高的、惟一的指標。 第二, “層層加碼”是推動這場錦標賽的基本作用機制。每級政府都制定“兩本賬”,第二本賬的指標高出第一本賬,上級的第二本賬作為下級的第一本賬。在從上到下制定計劃時按照第一本賬,但是在執行計劃和對下級政府進行考核和評價時用第二本賬作為標準。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行為的信息流通不暢。為大躍進及后來的饑荒中的虛夸和瞞報現象提供了制度基礎。
第三, “軟預算約束”決定了這場錦標賽的失敗命運。地方政府投入往往沒有真正的預算,而是盲目擴大投入,不顧及產出效率。
大躍進的深層機制在于,看似高度分權的錦標賽實際上是在高度集權和國家對社會資源全面控制的基礎上展開的。這種控制表現政治控制、思想和媒體控制以及資源控制三個方面。首先是通過政黨一國家政治體系實現的政治控制。其次是通過黨內外的政治運動和以媒體為中心實現的對信息系統和社會氛圍的控制。再次是資源控制。政府對社會經濟資源的全面控制是錦標賽發動的另一個重要基礎。
通過這三個方面的控制,中央政府在經濟上的分權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恰恰也是這些控制手段導致了這場錦標賽的失敗。在高度的政治控制之下,地方政府為了表現政治上的忠誠,必然以“層層加碼”為手段。高度的資源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并不關心長期經濟效益,只以擴大投資規模為目標。同時,地區間的競爭關系,造成重復建設和地區保護主義。高度的思想和媒體控制則同時導致浮夸、隱瞞的信息混亂,使得中央政府在全面嚴密的控制之下部分失去了真實的地方信息來源。
也由于這種高度控制,中央可以于“大躍進”后期迅速收權,重建中央集權。“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指的就是這種由集權一放權邏輯導致的經濟波動和周期。這種高度集權的體制會周期性地產生出錦標賽的內在需求,只要條件成熟,它就會卷土重來。這在中國漫長的中央集權歷史上,屢見不鮮。(郎朗
- 世界博覽的其它文章
- 信仰者
- 夢幻女與經濟男
- 如影隨形
- 我們不需要形而上的談判
- 海明威夫婦的中國“蜜月”之旅
- 一個真實的寧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