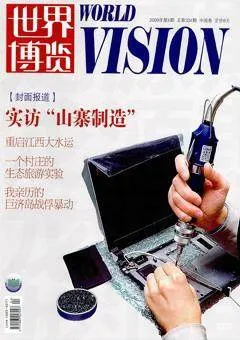漫游者的規則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過著自由不拘的生活——“風吹草低見牛羊”,是中國文人對這種無羈無束生活的浪漫寫照。然而,游牧這種利用邊緣、不穩定自然資源的經濟、社會、生態體系,處處充滿著危機與不確定性,毫無浪漫可言。人們對游牧社會的另一個誤解:認為“游牧”相對于農業而言是一種原始的人類經濟生產方式,在人類文明史上屬于由“漁獵”到“農耕”的中間進化階段。事實上,正因為游牧所利用的是邊緣、不穩定的自然資源,因此它需要人們對自然高度技術性的的理解與掌握,并配合經濟、社會各方面之種種精巧設計——此遠非8000年前或5000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原始農民所能企及。因此在人類歷史上,世界幾種主要類型的專化游牧都大約出現在公元前1000至前400年之間,遠較原始農業的出現為晚。最后也是最普遍的,人們對游牧人群有一種刻板意象,表現在西方卡通電影“花木蘭”中匈奴人猙獰如野獸般的造型,表現在將他們描述如“狼”的通俗著作之中。其實,由于游牧經濟及相關的社會組織特質,面對定居敵手時游牧者亦有其脆弱的一面。在這本《游牧者的抉擇——面對漢帝國的北亞游牧部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304頁,定價35元)一書中,著名人類學家王明珂著意為讀者澄清了對游牧民族的諸多誤解。
游牧民族所依賴的,最重要的是放牧的牲畜,這些動物的特點,對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很重要的影響。首先,能被人們馴養的動物——無論是常見于游牧經濟中的牛、馬、羊,或是定居農業聚落中的豬——皆為群棲動物。也就是說,喜好成群生活并有其“社會性”是它們的天性。牧人能控制、管理畜群,除了其放牧技術外,更基本的原因便是這些動物原來就喜歡結群活動,并有某種“社會秩序”,如性別、世代、族群間的優劣階序等。其次,游牧經濟中的馴養動物如馬、牛、羊、駱駝、駝馬、馴鹿等等,都是以草、葉、嫩枝、荊棘、苔蘚等為食的動物。這些植物或其纖維部分,大多是人類無法直接作為糧食吃下肚的。相對于這些動物的是豬。豬在野外所搜尋的食物,除了少數草葉外。主要為根莖、菇菌、野莓、野果、蝸牛,等等,這些大都是可直接作為人類“食物”的自然資源。
如此,飼養豬與飼養牛、羊等,在人類經濟生態上有不同的意義。簡單的說,在生存環境極端匱乏的情況下,豬是人的食物競爭者。養豬雖可為人類增添肉食,但豬也消耗人類的食物;兩相抵消,養豬并沒有為人類增加多少食物。肉食或雜食性的狗,就更會與人爭食而不宜作為牧畜了。但狗在人類馴養動物的歷史上有特殊地位,在游牧社會中它們常被用于放牧、守護以及協助狩獵。再次,游牧經濟中的主要牲畜如馬、牛、羊、駱駝、馴鹿等皆有很好的移動力,且其幼畜皆在出生數十分鐘內便可行走移動,這在配合游牧經濟中十分緊要的“移動”及減省牧業人力上至為重要。最后,產乳量高也是它們的動物性之一。而事實上,游牧人群難以賴畜肉為主食。經常宰殺牲畜為食難以維持游牧生計,因此,特別是在近現代之前(牧業被納入市場經濟之前),世界上各類型的游牧經濟人群皆普遍依賴乳產品為食。
牛需要大量飲水,因此養牛的環境需供水充足。牛怕熱、怕牛蠅騷擾,在悶濕,牛蠅多的環境中牛吃不好、睡不好,容易生病,所以通風、涼爽的環境較宜。不同種類的牛,也有不同的環境需求;如瘤牛較能耐熱及耐高度日曬,無瘤牛則這方面的能力較差。牛是反芻性動物,它們一天約花上八小時吃足相當分量的草,然后休息,慢慢反芻消化胃中的草。如此只要草食充沛,牛無需長時間、大范圍移動以覓食。牛也較能保護自己,所以日常牧牛花費的人力較少。因此在各種經濟生業之人類社會中,養牛與牧養其他牲畜通常不會矛盾互斥,養牛也能與其他生業如農業、狩獵等共存。然而在有些宜游牧的環境中,牧牛不見得有利。牛不易在厚雪覆蓋大地的冬天自行覓食,此時需賴人力來為它們提供草料,因此冬牧場雪多的地方無法養太多的牛。牛不易在崎嶇多石的山道上長途遷徙,因此多石的山區也不宜牧牛。牛又需消耗大量的水,因此水源匱乏的地方也不宜養牛。
在20世紀上半葉,居于中國東北的蒙古族人也遠較其他草原地區蒙古族人依賴狩獵。“狗”是狩獵生計的一項重要指標。在所有被人類馴養的動物中,除了狗以外,馬應是與人類關系最親密的動物了。馬對主人馴服、效忠,據動物行為研究者稱,這與馬群中的馬兒們服從領頭雄馬之習性有關。它們被廣泛用于各種類型的游牧中,作為載物、交通以及牧者坐騎之用,馬奶也可作為乳品以供食用。然而馬被大量牧養主要還是在歐亞草原,這也是馬最原始的棲息地,以及它們最早被人們馴養的地方。比超牧養牛、羊來說,養馬有其不利之處。它們的胃只有單胃室,對食物的消化利用不如牛、羊等有反芻胃的動物那樣徹底,因此它們消耗草食不甚經濟。它們的肉、乳產量與生殖率也不如牛羊。但在大多數游牧社會中,馬的肉與乳并非它們被牧養的主要目的。甚至于在許多盛行養馬的游牧人群中,養馬已超越“經濟”考慮,而蘊含更多的社會文化意涵與情感——它們被牧民視為忠誠的朋友與伴侶,以及社會身份地位的象征。
作者曾問一位蒙古朋友,為何許多蒙古牧人所養的馬遠超過其生計所需。對此,他的回答十分有趣。他說,若沒有幾十上百匹馬,出門時就不容易選到一匹宜于乘騎的馬。這只是說,對當代草原牧民而言,養很多的馬有其情感的、文化的因素而非全為生計。但我們仍不能否認馬在歐亞草原游牧上的重要性,特別是在過去,尚無現代化工具協助游牧之時。除了它們的乳、肉、皮、糞為人們生活所賴之外,馬卓越的移動力讓它們可利用廣大的、遠方的草場資源,可以幫助人們溝通訊息,以及讓人們快速遠離危機。這些都使得近代以前馬在歐亞草原游牧上有其優勢。
中國歷史文獻記載中漢軍擄獲的匈奴牲畜與人口數量,不一定能正確反映匈奴游牧社會中實際的人畜比例。我們無法知道,是否每一個被捕的匈奴人都帶著他所有的畜牲,或牲畜被擄獲時它們的主人也成為俘虜。更可能的是,畜群比人更容易被漢軍截獲。因此學者們統計出每一匈奴人擁有約19頭牲畜,此數值應是偏高。中國文獻中匈奴部眾驅畜來降的例子,或較能反映當時該部落的人畜比例。《后漢書》記載,83年北匈奴部落首領率38000人,馬20000匹,牛、羊10余萬來降,大約每人只有馬0.52匹,牛、羊3~5頭。《晉書》記載,287年匈奴都督率眾驅畜產來降,該部落之眾有11500人,帶來的牛有22000,羊105000頭;人畜比約為每人牛2頭,羊9頭。據俄國學者的統計,在20世紀初時,一個五口的蒙古家庭需要14匹馬、3匹駱駝,13頭牛、90頭羊才能生活。前述匈奴部落的人畜比,看來遠低于俄國學者所稱近代蒙古牧民的最低生存水平。然而在游牧社會中,所謂最低生活所需牲畜量很難估計;因為游牧生產中的“風險”難以估算。雖然這些匈奴部落有可能是在遭到畜產大量損失后才率眾來降的,無論如何,他們與近代蒙古牧民在畜產上的差距,可能反映著其游牧經濟形態,以及對輔助性生業的依賴,都與近代蒙古牧民有所不同。
《史記》中對匈奴人的狩獵只有很簡短的描述:“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僅此簡短的描述,表現了狩獵在匈奴人生計上的重要性以及在其生命歷程及生活上的特殊意義。在許多游牧社會人群中,狩獵都普遍有其特殊功能。人們也許會認為,游牧人群擁有大量家畜,所以肉食無缺。事實上,游牧者所擁有的家畜是生產“本金”。為了生存,他們需盡量吃“利息”,避免吃“本金”——為了保證在遭受突來的天災、畜疫后仍有足夠的牲畜可繁殖,牧民都希望保持最大數量的畜牲,不輕易宰殺它們來吃。在此情況下,行獵以補充肉食,成為許多游牧人群避免宰殺其牧畜的重要生計手段。西漢時,南單于及其民眾曾遷到長城附近,歸附漢帝國。后來他們請求歸北,理由之一是“塞下禽獸盡,射獵無所得”。由此可見狩獵對他們的重要。《新唐書》中也記載,降于大唐的突厥人曾抱怨稱:“禁弓矢,無以射豬為生。”
前面所引《史記》對匈奴狩獵生活的記載,提及的獵物有鳥、鼠、狐、兔等。民族志數據顯示,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蒙古高原西部之薩彥一阿爾泰地區牧民最普遍的獵物是松鼠、兔、狐、貂、獾,以及羚羊、鹿及狼等,其中又以松鼠、兔為最普遍。現今蒙古草原上數量最多的動物就是各種鼠類,如田鼠,黃鼠、兔尾鼠、沙鼠,等等。雖然根據各種游記及蒙古史詩記載,游牧者所獲獵物多是大型動物,但這些材料往往將狩獵當作一種英雄行為來記錄、歌頌,因而無法反映游牧人群日常生計的獵食行為。由前述《史記》相關內容,及近代民族志記載看來,匈奴人經常獵得以補充其肉食的主要是小型動物。再者,草原上的大型草食動物都有移棲性,以追尋不穩定的、季節性的自然資源,而匈奴各部落皆有其固定牧地,因此應非所有匈奴牧民都常有機會獵得大型動物。相反的,小型動物如鼠、狐、兔、獾等都是定棲性動物,匈奴人應能經常獵獲它們以作為肉食。雖然如此,在一固定牧區過度捕殺也會造成“射獵無所得”的結果。
,
通過對歷史上的游牧民族的考量,可以看出,我們每一個人都被范定在層層的邊界之中。最主要及最基本的是我們所存在的空間,對于人來說,難以生存的資源環境邊界:過于干旱的沙漠,荒寒的凍原,不宜植物生長的高原,野獸噬人的森林,難以立足的沼澤。層層的自然環境因素都對人造成種種“邊界”。在這些自然環境邊界內,人利用種種辦法來利用有限的資源,同時也設法突破自然環境對人類造成的邊界。在人類歷史上,自新石器時代馴養動物與種植作物以來,人類便在擴張其可利用的邊界。而其中一個巨大的突破,便是利用草食性馴養動物的游牧。約自公元前1000年開始,人們先是利用馬、牛、羊,后來又利用駱駝、牦牛、駝馬、馴鹿,讓人類活動的足跡廣布于農人難以利用的歐亞草原,并逐步深入沙漠、凍原,攀上高山與高原。
其次,利用種種生計手段利用環境資源,人類普遍以“結群”方式來分配、爭奪與保護資源領域,這又造成了一種“邊界”。這些共享與保護資源的人類社會群體,如家庭、家族、部落、部落聯盟、國家,也造成家族與家族間、部落與部落間、國家與國家間的“邊界”。再來便是,在家庭、部落與國家內部還有一些次群體,因此他們間又有些“邊界”。如在游牧社會之多妻家庭中,每一妻子與親生子女形成一次群體,而與家庭中其他的母親,子女群體有所區別。部落中常含有更小的部落,通常也是一家族部落,部落與部落間,小部落與小部落間,皆以各自的“祖先”來團結與區分。如此便形成大的外層邊界,其又有內層邊界。
各個人類群體內還有性別與階級邊界。男性與女性有別。在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中,男女身體之別被強化為性別“邊界”,如此區別男女間的勞動分工、社會權力與資源共享。人類社會中又常有王室、貴族,武士、平民、奴隸,或征服者與被征服者,本地人與外來者,等等之區分。經常,透過一些歷史記憶,王室、貴族、武士等為征服者的后裔,平民或奴隸為被征服者之后裔。即使在今日“公民社會”,在共享公民權利的人群中“歷史”仍造成了意識形態上的邊界,以區分誰是社會主流(主要民族或族群),誰是社會邊緣(外來新移民、原住民與少數民族)。
種種邊界的維持,也是維持一種秩序。邊界維持賴于人類各種社會政治組織、制度及其施于個人的威權,這是將個人約束在“邊界”內最現實的情境與力量。邊界維持又賴于支持此社會政治秩序的歷史記憶;相信“歷史”,生活在“歷史”中,也讓我們接受“歷史”所造成的社會人群邊界。種種人群邊界的維持,又賴于神話、宗教信仰。神話將一層層邊界外的人群世界妖魔化,讓本群體的英雄祖先神圣化,因此邊界讓人恐懼而又崇敬——邊界使得圣潔與污穢成為一體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