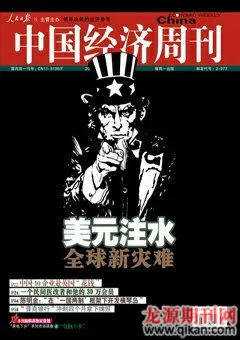回到村莊 重拾希望
我清楚的記得十年前的那場金融危機,東南亞經濟遭到重創,中國當時也深受影響,在外地做生意與打工的村民們回到了故鄉,他們不談“金融危機”這樣的概念,見了面只說,外面生意不好做了,或者在外面賺不了錢了,所以都不約而同地回到故鄉。村里的一些人家樓房蓋了一半,錢續不上,就停工在那兒,有些無奈,也有些令人感傷。
又一場危機不期而至,通過電視鏡頭我們看到,男人們還有年輕的女孩子們又紛紛回到了村莊,回到屬于自己的土地上,村莊熱鬧起來了,村莊里的小店也紅火起來了,村莊里的小學教室開始坐不下由城市回來的農村娃。通過電視鏡頭,我們看到,那些天天盼自己男人回家的媳婦嫂子們,滿面泛著幸福的紅光,對她們來說,錢多錢少都得過日子,關鍵是自己的男人回來了,孩子們有爸了,晚上點燈有說話的伴了,有什么比得上這樣美滿的生活呢?
當我們計算國家GDP或鄉村勞動力在城市創收時,我們有沒有計算過,農民們的幸福指數呢,特別是留守兒童與留守村婦們的幸福指數?那些在城市里打工的村民們,除了得到一些并不能算理想的收益,他們的幸福收益又是多少呢?
村莊還在,家還在,幸福也還在,生活就可以繼續,希望就可以重新萌生。
對村莊里的農民來說,無論如何建設城市,城市都不可能屬于自己,自己的戶口永遠被捆綁在土地上。農民的存在似乎是“應招”性質,城市需要時,他們就坐著火車扛著包袱,自費來到城市,低成本地勞作;而城市的建設業已“完成”,或告一段落,他們就打道回家,某些時候甚至可能是勞而無獲。但無論如何,城市是他們工作與收益的希望所在,而鄉村,只有生活本身,土地里長不出希望,沒有任何想象的空間。
靜態的村莊不復存在,動態的村莊正在成長,我們如何應對動態的村莊,讓村莊與城市互相滋補,共生共長?這是整個社會必須面對的嚴峻問題。
當村莊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時,村莊同時也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當我們主流社會大談村莊社會因經濟而出現波動的時候,我們忽略了文化的意義,我們忽略了非物質文化生活對村莊的價值與意義,當一個陜北老漢坐在窯洞門口曬太陽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意識到,那是一種綠色的經濟與綠色的文化“消費”?當一個男人帶著老婆孩子在田間地頭勞作的時候,那是不是一種田園牧歌式的幸福生活?當國家實施中小學義務教育之時,當各地實施最低生活保障之時,以城市經濟為中心的思維應該從我們主流意識形態中汰除,正是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思想,使我們對村莊充滿危機感與威脅感,似乎村莊社會離開城市經濟之后,村民們沒有城市經濟發展帶來的收入之后,村莊將出現動蕩,會出現不隱定因素。這是對村莊的子虛烏有的想象。
村莊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回到村莊,最不容易的是犯罪,因為村莊總能為人的生存提供基本的保障,各種親緣關系總能給有困難的家庭予以幫助。而在城市卻不同了,城市是陌生人社會,城市對鄉村人的援助體系并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所以鄉村的人們在城市更容易走到歧途,甚至鋌而走險。最近一位失業的大學畢業生在京搶劫,就是身無分文,想回家看望重病的父親而無法成行所致。
改革開放三十年,是物質經濟發展的三十年;后改革年代,應該是非物質經濟文化發展的時代。物質經濟時代使每一個都追求物質利益,將物質利益看成第一追求,似乎只有錢能帶來幸福,只有錢才能證明成功,但是,錢真的能帶來幸福嗎?錢真是代表成功嗎?當村莊里的人們涌向城市,當村莊里的人們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當村莊里的人們討要不到工錢,我們發現,正是追逐物質利益,物質拜物教,使城市人坐收村莊之利,他們成為發展的主體,而村莊卻日益淪為城市的附庸,成為自然生態與文化生態意義上的淪陷之地。村莊沒有確立自己的主體性,因為城市將自己塑造成幸福的中心,幸福的發源地。
村莊的主體性來自村民們對土地的擁有權,無恒產者必無恒心,有恒產者,才有自主性,才有自信心。當一些人擔憂土地回到農民手中,會造成無端流失,會造成大量農民無地無產,因此會影響社會穩定,那么,這些人想過沒有,土地如果進入市場流轉,那么會產生巨額的稅收,國家為什么不能用土地增值的部分為農民建立養老與失地保險呢?城市工人在上一輪國企改革中失去了工作,但并沒有影響社會穩定,為什么?因為他們獲得了基本生活保障,而且年輕健康者還可以重新就業;農民如果自己不愿意耕種土地,將自己的土地賣出,那么他可以到規模經營的農場里就業,成為新的“農民工人”,這樣的農業就業,比到城市就業總是強多了吧:一是在熟人社會里工作,拖欠工資的事件就會大大減少;二是在自己的村莊附近就業,不影響正常的家庭生活。近30年大量農民進入城市,造成和平年代最大規模的家庭分居,這難道不是一種巨大的精神財富的損失嗎,和合圓滿的家庭生活值多少錢?經濟學家能計算得出來嗎?
現在農民成為精神上的流民,在城市他們是暫住,回到鄉村,他們還是暫住,他們覺得還是應該回到城市獲得利益,盡管在村莊里得到的是一種生活上的價值,在家庭中自己還原為一個實在的人,而在城市他們只是一個符號,一個工具。農民的悲劇性在于,他們在鄉村里得到價值時,得不到利益,而在城市里得到一些利益時,卻無法得到生活的價值。
其實我們都成了拜物教教徒,而我們每一個人卻都不自知,我們除了金錢,似乎什么都無法安慰我們的心靈,什么都使我們得不到安全感與成功感,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當一個國家衣食無憂之后,所有的問題就都成為文化問題,都成為意識形態問題——宗教上的信仰問題,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問題,經濟上的公平平等問題,生存倫理上的正義博愛問題。而我們的主流社會卻沉緬于經濟發展不能自拔,經濟無論如何發展,能解決信仰與終極關懷問題么,利益無論如何發展,都不可能成為價值。中國城市、鄉村社會,應該在追求價值上開始新的進程。沒有價值追求,只有利益追求,必然疲憊、崩潰在經濟泥潭里。
村莊現在需要的,還有管理與觀念上的升級,也需要技術與文化上的升級,村莊民主化管理制度的建立現在正是一個好時機,因為村民們從城市大量返鄉,利用這樣的機會進行民主選舉與村莊規劃,使村莊在發展模式與經濟出路上,有一個共識與發展方向。中央新政使村莊獲得了一定的經濟保障,譬如農業稅的減免,農村學生中小學學費的免除,以及正在進行的農村醫療與養老保障,都使村莊獲得了一定的經濟保障,也是生存權力的保障,也是發展權力的基礎。
村莊現在最需要的,是公民權力的保障,與城市市民一樣擁有公民權力,一方面是在自己的村莊選舉真正的權力代表,還有就是民意代表。村莊需要恢復權力生態。在傳統農業社會里,村莊具有高度自給自足能力,也具有較高的自治能力,村莊里的長老與教書先生在自然村莊里具有協調民間社會的能力,也是民意的代言人,而在現代民主制度下,在過去權力失衡的民間生態中,需要重新培養村莊里的自治生態,既要有經濟發展的帶頭人,更需要民意協調的代言人。
村莊不是用來擔憂的地方,不是需要城市憐憫的地方,村莊是中國經濟與文化的大后方,十年前的金融危機之所以得以化解,是因為鄉村的人們退回到鄉村之中,積蓄能量,以空間為中國經濟后發獲得時間,而這次世界金融危機沖擊中國東南沿海,但鄉村仍然以博大胸懷,接納著無數返鄉的親人。村莊可以一年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不需要城市,但城市如果離開了村莊,就會失去發展的力量。
危機之時,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在思維上將村民公民化,使他們在將來的日子里,進入城市之時,以公民的身份獲得城市工作的權力,如果將農民僅僅看成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低成本的勞動力,村莊就會永遠得不到真正的尊重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