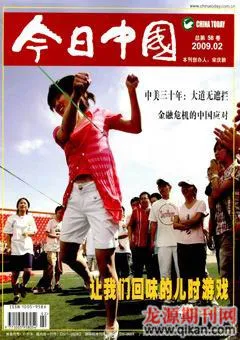臺海書緣
與陳文豪教授相識,是在1991年蘭州召開的國際簡帛學國際研討會上。陳教授出身澎湖海上,性情卻一如大陸北方人。坦誠、熱情、豪爽的性格,使得他成為大陸許多學者共同的朋友。在臺北喝“金門高粱”,在北京喝“二鍋頭”,相處時多,我們的友情日漸深厚,但聯系我們兩地兩心的,并不僅僅是酒緣,也許更重要的是書緣。
最近在一本印制華美的雜志上看到介紹一些學者工作環境的圖版,題目似乎是“坐擁書城”,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陳文豪教授的書房。我曾經參觀過他在臺北和彰化的三處書房,四壁是高高的書架,地板上又堆積著未及整理的書籍,客人幾乎難以立足。圖書的數量可以稱作汗牛充棟。

和陳文豪教授相識之后不久,我就受囑為他購買并郵寄大陸出版的相關學術書。陳文豪教授原先任教于臺北中國文化大學,現在彰化師范大學就職。他多年任臺灣中國上古秦漢史學會秘書長,主要研究方向是秦漢史和簡帛學。涉及這兩個研究領域的大陸出版的學術論著,他都不遺余力地積極搜求。到臺中主持彰化師范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后,因為這個研究所以歷史地理學作為研究主題,歷史地理學的論著也成為陳文豪教授收集的對象。起先按照他寄來的書目選購,后來也多有我自己購書時自作主張為他代購的情形。大略估算了一下,自2001年以來,我所經手他的書款,就有人民幣3.5萬元左右,美金近萬元。粗略估計,這七八年寄給陳文豪教授的書籍,應當在6000冊以上。
說到寄送書籍,不得不提到海峽兩岸間的郵政之難,寄出要到指定的郵局,檢查、包裝、計重、交款……手續十分繁瑣。印刷品包裝要求5公斤1包,超重是不行的,因為書籍較重,每次都要分數包郵遞。但寄出時稱重合格,幾天之后卻因超重被退回,只得再次包裝付郵的事也時有發生。好在兩岸直郵已然開通,兩岸郵寄相比簡便了許多。
事實上,我并不是在大陸為陳文豪教授代購書籍的惟一朋友。據我所知,各地接受這樣委托的學界同人至少有六七位之多。可以說,陳文豪教授最及時、最全面地掌握著大陸相關學科的學術新動向,這一點甚至超過了不少大陸學者。往往是拿著他開具的書目到書店尋找時,書店的朋友告知,這書還沒有進入發行程序呢。文豪教授通過互聯網檢索到的新書目,面世的時間,似乎要比圖書本身上市的速度早半拍。
陳文豪教授也幫我買過不少書。一些價值不菲的臺版學術著作,是他主動寄贈的。例如《居延漢簡補編》這樣的大書。此外如勞 的《秦漢史》、李學勤的《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劉樂賢的《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等,這些秦漢史研究的前沿性研究成果,通過文豪教授的無私惠寄,使得我能夠及時地領略和學習。
明代學者蔣德璟有《題桃源索隱冊六則》的文字,其中第五則寫道:“二酉”石室據說是秦人藏書處。秦始皇焚書時,有人挾書隱居,且為藏之名山。相傳有樵夫入石室取書,“出皆應手灰滅”。傳說大禹登會稽山的宛委峰,得金簡玉字之書;孔子登泰山,見七十二家論著。大禹和孔子兩位圣人,“有書癖亦有書緣”,可惜毀壞二酉石室藏書的樵夫不是這樣的人啊。
“有書癖亦有書緣”,形容對書誠心的愛重,真正的理解。這里所謂“書緣”,是說人和“書”的“緣”。我們這里借用這一語詞,轉其義而用之,是指友人之間因“書”而成就的“緣”。
東漢大學問家王充,因為“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終于成就了名著《論衡》,這在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東漢時期的荀悅也是在書店讀書,然后實現學術積累的。《太平御覽》卷六一四引司馬彪《續漢書》寫道:“荀悅十二能讀《春秋》。貧無書,每至市間閱篇牘,一見多能誦記。”荀悅所撰寫的《漢紀》,成為漢史研究者必讀的史學經典之一。陳文豪教授有一篇討論漢代書業的論文《漢代書肆及其相關問題蠡測》,對這種文化現象進行了分析和總結,文章全面探討了書肆的起源及漢代書肆發展興盛的歷史過程。陳教授認為,作為傳播文化的重要媒介的書籍的流通,對于當時社會文化的進步有顯著的影響。我的一篇文章《漢代社會的讀書生活》,說到“漢代圖書收藏”和“漢代民間的書籍流通”問題,關于書籍流通的形式和意義的思考,就是受到陳文豪教授的啟示。
陳文豪教授每次來京,我都會陪他去一些書店買書的。北京師范大學東門的盛世情書店,北京大學西門的第三波書店,藍旗營萬圣書園,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附近的考古書店等等,自然還有琉璃廠的中國書店。我惟一一次違章停車,就是陪同陳文豪教授購書,在琉璃廠街頭被貼了違章處罰單。
我曾經五次赴臺。每到臺北,陳文豪教授也必會陪我到書店買書。臺灣的書店大多安靜素雅,售書人員對各專業書籍都較為熟悉,足以勝任導購工作。對于服務質量印象最深的是樂學書局。這里不僅學術圖書數量集中,門類齊全,工作人員咨詢服務態度也非常好,郵寄的安全快速,尤其讓讀者放心。第一次領我到樂學的是輔仁大學邵臺新教授。可惜他后來病重長期住院,不能夠一起逛書店了。樂學書局的黃經理和陳文豪教授非常熟。我們在這里一邊看書,選書,一邊低聲談天,談共同的朋友,談兩岸書業的發展與學術的交流,全身心沉浸在書香和友情之中,真是何樂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