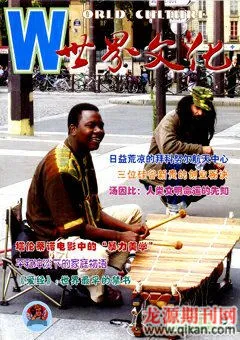湯因比:人類文明命運的先知
中國近代以來一直面對來自西方的挑戰。如何應對持續不斷的外來挑戰,是中國人不得不直面的問題。因此,“挑戰與應戰”理論在中國有著特殊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談到“挑戰與應戰”,就應該知道將該理論應用到歷史研究的首創者——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湯因比被譽為“近世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20世紀最偉大的思辨主義歷史哲學家”,“文化形態史觀的集大成者”,“最勇敢的歷史學家”、“國際智者”甚至“先知”等等。而他窮一生之力完成的代表性巨著《歷史研究》,則被譽為“我們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20世紀精神史上最重要成就之一” 和“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著作”等。湯因比和他的著述為什么會獲得如此高的贊譽?
湯因比于1889年4月14日出生在倫敦,1975年10月22日在英國的約克郡去世。他的母親是英國第一代女大學生,著有《蘇格蘭歷史故事》等書。他的叔叔阿諾德·湯因比則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湯因比在叔叔曾經就讀過的牛津大學巴里奧學院學習,專攻希臘羅馬史。他畢業之后從事古代史教學工作。從1919年起,湯因比擔任倫敦大學科雷斯講座教授。1925年,他擔任倫敦大學國際關系史研究教授,直到1955年退休為止。在教學和研究之外,湯因比還積極參加各種社會和政治活動。1915年,他任職于英國外交部政治情報司;1939—1943年間擔任皇家國際事務學會外事部研究室主任;1943~1946年間擔任英國外交部研究司司長。他學識淵博而又積極參與現實政治,故得以參加兩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的各種和平會議。此外,他長期負責主編皇家國際事務學會的年刊《國際事務概覽》(1920—1946),這個活動促使他在進行歷史研究時關注現實和未來。
湯因比的主要聲望來自他的歷史研究成果。他一生著述等身,主要有《民族與戰爭》、《希臘的歷史思想》、《漢尼拔戰爭》、《文明經受著考驗》、《一個歷史學家的宗教觀》、《人類與大地母親》以及《1924—1938年國際事務概述》等。這些論著既有斷代史作品,也有通史性作品。不過全面反映他的歷史觀點并使他獲得全球性聲譽的,還是煌煌12卷、總字數達五百余萬的《歷史研究》。從1920年開始直到1972年,湯因比在五十余年忙碌的學術和社會活動中, 始終致力于《歷史研究》的構思、創作和修訂。他于1934年出版了《歷史研究》第一到三卷,1939年出版了第四到六卷,1954年出版了第七到十卷。1961年,隨著第十二卷《再思考》的出版,這項里程碑式的研究最終完成。這部書由于篇幅過于龐大,即使專業歷史學家都難以卒讀,因此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未能流傳開來。1946年,英國人索麥維爾為該書前六卷所作的縮寫本出版。這個縮寫版廣受好評,一時洛陽紙貴,成為英美世界的暢銷書。10年之后,他又完成了對該書第七到十卷的縮寫工作。麥索維爾的簡編本在一定程度上損傷了湯因比這部大作的文學性,同時又不得不簡略了眾多論證性的歷史材料,但是在擴大湯因比的影響力方面發揮了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湯因比本人在1972年他83歲高齡之時,在簡·卡普蘭女士的協助下完成了《歷史研究》插圖一卷本。這個版本推出后同樣獲得巨大的成功。
《歷史研究》的主要內容是以“文化形態史觀”綜合考察人類歷史,注重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并對人類的未來進行預言。湯因比堅信,“在人類事務的研究中,同時采取一種研究普遍性規律的方法和一種研究個別事物的方法,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歷史是什么?在湯因比看來,就是記錄他稱之為文明的單位的興衰和滅亡以及各文明相互交流的過程。湯因比認為,歷史研究最適合的單位,既不是民族也不是國家,而是文明。他提出:“歷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單位既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也不是另一極端上的人類全體,而是我們稱之為社會的某一群人類。”文明實際上就是文化化了的社會。按照這個定義,他認為世界上一共有西方基督教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國文明、埃及文明等在內的21個文明,其中14種已經滅亡,7種尚存。后來湯因比又增加了愛斯基摩文明等5種“發展停滯的文明”,于是文明的數量就成為26個。此后,湯因比又認為文明的數量有37個。
緊接著湯因比提出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為什么有些社會在出現初期就停滯不前,沒有發展到文明的程度?湯因比拋棄了種族決定論和環境決定論,提出“挑戰與應戰”理論。他認為,如果一個社會中有少數具有創造能力的人,并且這個社會所處環境恰好能夠激勵這少數人應對來自自然和其他社會的挑戰,那么應戰成功的社會就能夠進入文明階段。而一個社會如果缺少有創造能力的人,并且所處環境的挑戰過小或者過大,這個社會就會陷入停滯乃至被消滅。這種挑戰和應戰不會一次性結束,而是不斷重復發生。
湯因比不僅在《歷史研究》中大量地用各種資料論證“挑戰與應戰”理論,而且也把這種理論應用于他的其他著作。如他的專著《漢尼拔的遺產:漢尼拔戰爭對羅馬生活的影響》一書就是典型例子。他在這部兩卷本的羅馬史中認為:共和時期的羅馬因為獲得一個龐大帝國而面臨新的形勢,羅馬和意大利因為與迦太基人之間的第一、二次布匿戰爭而發生了巨大變化,羅馬人未能回應這二者的挑戰,最終導致共和制的滅亡和君主制的建立。當然,湯因比指責羅馬人在公元前2世紀沒有采用君主制,這種觀點毫無歷史依據。
湯因比認為,文明一般要經歷起源、生長、衰落和解體的過程。今天的文明是已經滅亡的文明的“后代”。文明的起源是“挑戰與應戰”的結果。文明生長的動力則是少數有創造力的人能夠影響大多數人的行動。湯因比認為少數人的創造性思想是文明發展的原因,卻否認了思想正是文明的本質所在。文明的衰落則是原本有創造力的少數人變成了統治者,不能再對挑戰做出成功的回應。在文明的解體階段,其過程大致分為“大一統國家”的建立、間歇期,“大一統教會”出現和蠻族的民族大遷移四個階段。之后,新的文明在舊文明的廢墟上重新開始。這種文明解體的模式實際上只適用于某些文明。
湯因比與他的思想前輩斯賓格勒(1881-1936)實屬同時代人,只不過斯賓格勒早在1936年就去世,而湯因比則一直活到1975年。二者同被視為“文化形態史觀”的代表人物,在觀點上也頗多相似之處。他們都著力打破“西方中心論”或者“西歐中心論”;認為歷史研究的基本單位是文化或者文明;不同時期的文化或者文明在哲學意義上是“同時代的”;文化或者文明都和生物有機體一樣,有起源、生長、衰落和解體的過程。甚至湯因比與斯賓格勒在行文中都一樣具有詩性特征和神秘色彩。如湯因比在闡述“挑戰和應戰”理論時,古希臘羅馬的詩歌、神話和戲劇、《圣經》、歌德的《浮士德》紛紛出場。他猶如古代的苦修者得到天啟一般,提出“借助神話的光亮我們對挑戰和應戰的性質有了某些深入的了解”。
但是湯因比在許多方面不同于斯賓格勒。在文明的命運問題上,湯因比不同意斯賓格勒的宿命論觀點,也不贊成歷史循環論。他認為文明滅亡之后還可以在其廢墟上浴火重生。在文明的相互關系方面,斯賓格勒認為文化或者文明之間沒有交流和學習。而湯因比反對這種觀點,認為各文明之間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在研究方法上,斯賓格勒輕視史料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工作,認為憑借激情和直覺就可以充分理解和研究歷史。而湯因比則在體系化論證自己理論的過程中表現出專業歷史學家的素養。他不僅熟悉眾多歷史時期的第一手材料,而且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并能將二者很好地融合在自己的體系內。在研究態度上,湯因比也與斯賓格勒截然不同。斯賓格勒是徹底的悲觀主義者,認為一切文明都會滅亡,即使唯一幸存的西方文明也不例外。而湯因比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同時仍舊保持樂觀態度,認為“雖然據我們所知,有16個文明死了,另有9個已經在死亡的邊緣,我們的這個第26個文明卻不一定非服從命運的安排和統計數字的盲目計算不可。創造性的神火還在我們的身上暗暗地燃燒,如果我們托天之福能夠把它點燃起來,那么天上的所有星宿也不能阻撓我們實現我們人類努力的目標”。
當然,湯因比以一己之力進行如此大規模的研究,其中自然存在著各種問題。例如他出于對古典歷史的熟稔和熱愛,在研究其他文明時執著于“希臘模式”,所以他甚至在討論哥倫布航海之前的美洲歷史時都喜歡使用古希臘文明的內容。湯因比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斷地根據新資料更正自己,但是很多論述中的觀點和資料陳舊。例如他對猶太人的歷史的認知仍舊停留在《死海古卷》發現之前;而他對非西方文明的歷史如中國歷史的認識,其局限性就更加明顯。
很多人會理所當然地批評湯因比過于低估社會和經濟力量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的確,湯因比的著作會讓熟悉希臘羅馬歷史的讀者會情不自禁想起圣奧古斯丁。他強調基督教、東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等高級宗教的作用,并否定其中任何一種的獨特性。湯因比為什么不把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寄托在技術進步和科學發展?他本人自幼深受《圣經》的熏陶,他的父親患精神病身故,長子自殺身亡,他本人的第一次婚姻極為不幸。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眾多朋友和同事在戰爭中死亡。這些無情的事實都使他對物質的作用產生了深刻的懷疑,“任何一種物質上的成功都是虛榮、欺騙和對人性的背叛”。他認為,人類擁有的物質力量越大,那么這個物種所面臨的危險就越大,所以他希望從精神上拯救人類。也正因為這個原因,他在自己的另一部名著《人類與大地母親》的結尾處寫道:“人類將會殺害大地母親,抑或將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濫用日益增長的技術力量,人類將置大地母親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導致自我毀滅的放肆的貪欲,人類則能夠使她重返青春,而人類的貪欲正在使偉大母親的生命之果——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價。何去何從,這就是今天人類所面臨的斯芬克斯之謎。”惟有回歸精神家園,才是人類的終極自由之路。
大時代使得湯因比能夠成為開拓廣闊新天地的一代史學名家。從1914年以來,湯因比經歷了人類已知歷史中最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目睹了輝煌的大英帝國斜陽落日般的沒落,體會了西方文明在擴張到極限后的急劇收縮,科學技術在空前發展之后帶來的負面作用。湯因比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巨變時期順時代思想潮流脫穎而出。1969年,湯因比在自己八十歲生日之際的一封信中寫道:“我的八十年——1889-1969:如果我可以選擇時代的話,我會選擇在這個獨特的八十年間生活嗎?我作為西方中產階級的一員,若考慮個人舒適的話,就會選擇維多利亞時代的八十年——這個時代正好逃過了拿破侖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是,如果我是一個產業工人,我當然會選擇我本人的八十年;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還會選擇同樣的八十年。這個時代對中產階級而言動蕩不安,在歷史學家看來則是引人入勝。我既是歷史學家,也是中產階級,但我首先是一個歷史學家,所以我慶幸自己生于1899年并且一直活到1969年。” 倘若湯因比生活于維多利亞時代,大概他會以紳士的身份舒適地度過一生,而不會成為享譽世界的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