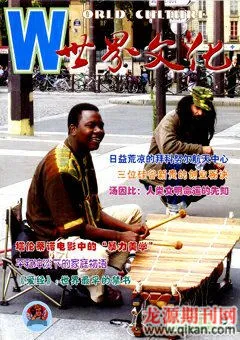“不滅的美”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196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繼泰戈爾之后第二位獲此殊榮的亞洲作家。而在4年后,川端康成卻以自殺的方式告別了人世。
1972年4月16日下午,他對妻子說“出去散步”,然后一個人來到自己兩三個月前在海濱公寓租的工作室。到了晚上他還沒有回家,他的助手島守敏惠在9點45分左右來到公寓,當他向川端的房間走去時,聞到一股刺鼻的煤氣味。在警備員的幫助下他打開了上了鎖鏈的房門,發現川端康成在盥洗室里口含煤氣管靜靜地躺在棉被上,枕邊放著打開了瓶蓋的威士忌酒和酒杯。有關當局推斷死亡時間是下午6時左右。川端康成的死震驚了文壇,為什么川端康成會在他聲名顯赫、事業巔峰之時以這樣一種方式終結了自己輝煌而燦爛的文學創作生涯?沒有留下只字片語的川端康成,他的死就如同他的文學作品一樣留給后人無限的話題。
“參加葬禮的名人”
對于死亡,川端康成是再熟悉不過了。他2歲時父親患肺結核去世,翌年母親因長期伺候父親也身染肺結核不治而亡。父母雙亡的川端康成隨祖父母一起生活,而7歲時疼愛他的祖母也棄他而去,祖母過世三年后唯一的姐姐芳子也患病身亡。姐姐死去后,川端康成與耳背眼瞎的祖父相依為命,可是當川端康成15歲的時候祖父也離他而去了,從此天地之間只剩下他一個人。從幼年到青年,川端康成頻繁地參加至親的葬禮,就有了“參加葬禮的名人”稱號,他“像殯儀館的人”,甚至“連衣服也凈是墳墓的味兒”。青少年時期,正是一個人世界觀、人生觀形成的重要時期,過多的親歷了親人死亡的川端康成,在日常生活中也總是能“嗅到死亡的氣息”,“生”總是被“死”包圍著。到了日本戰敗后,川端康成又頻繁地參加好友的葬禮:片岡鐵兵、島木健作、武田麟太郎、橫光利一、菊池寬相繼離世,川端康成忙于在各個葬禮上宣讀悼詞。北條誠戲稱他由“參加葬禮的名人”不久變成了“致悼詞的名人”。川端康成自己寫到:“懂得寂寞的年齡來臨時,似乎就會遇到最寂寞的事情。幾年以來友人相繼死去,而我的生命卻無論如何也不能消滅,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橫光利一悼詞》)一方面,西方尤其是美國文化大量侵入戰后的日本,日本民族傳統文化備受摧殘,這使一向注重日本傳統美學的川端康成感到莫大哀愁。另一方面,好友的相繼離世又使川端康成少年時就形成的孤兒氣質更甚,難以擺脫的孤單感總是與他如影隨形,他甚至想到“為了免遭死人的悲哀,只有自己死掉。”過多遭遇親人、友人死亡的川端康成常感到生命的無常、世事的難料。他認定了生是徒勞的,死是絕對的,任何人都無法超脫。晚年時,川端康成精神負擔越來越重,他神經脆弱,心緒不寧,完全靠服用安眠藥度日,藥量逐漸加大,整天處在似真似幻的狀態。也許生死對此時的川端康成來說已不存在界限,想把自己戰后的生命作為余生獻給日本傳統美的川端康成是如此看重自己的生命質量。但他也是個普通人,生命對于他來說太過于沉重,選擇“心甘情愿地進入長眠”未嘗不是解脫之道。
《源氏物語》與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的一生執著地追求日本傳統的美,不遺余力地表現日本傳統的美。日本文化傳統對物哀、幽玄的審美追求深深滲透進川端康成的生命中。年輕時,川端康成就醉心于日本古典文學的世界。川端康成說過他年輕時讀過的大量的古典作品,到了中老年“還是朦朧地留在自己的腦海里。色調雖然淡薄,卻還是感染我的心。就是閱讀當代文學作品,有時我也感到千年、千二百年以來的日本古典傳統在我心中旋蕩”,日本的傳統美已經匯進了川端康成的血液。川端康成對平安朝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語》推崇備至,認為《源氏物語》是“冠絕古今的”,他在中學時就開始熟讀《源氏物語》,即使在戰爭期間也不泯對《源氏物語》的熱情,經常“在東京去的往返電車上和燈火管制下的床鋪上看以前的《湖玉抄本源氏物語》。”晚年,他著手將《源氏物語》譯成現代漢語。《源氏物語》已成為作家生命的一部分,《源氏物語》所代表的日本古典美傳統成為川端康成文學的基礎和底流。
《源氏物語》以光源氏為主人公寫了他與眾多女性的戀情,但無論是誰都沒有好的結局。藤壺、紫姬、三公主、空嬋、末摘花、明石姬等眾多女性,她們或出身高貴,或品貌出眾,多才多藝,他們追求真摯的愛情婚姻,但最終都沒有逃脫死亡、出家、空守三種命運。再反觀光源氏,他企圖在與女性交往中獲得人生的意義和心靈的慰藉。然而,他漁色獵艷所得到的不是幸福與甜美,而是傷感與哀愁。整部《源氏物語》流露著悲怨之情和悵然若失之感。川端康成深深地沉浸在《源氏物語》的情感基調里,日本著名文學評論家長谷川泉就認為“川端源氏大概仍然是有著濃密的血緣關系吧”。《源氏物語》中稠得化不開的“哀”感,所謂的“物哀”總是在佛教的來世觀中得到解脫,這也成了川端康成的解脫之途。
“物哀”的內在精神內涵與無常感有相契相合之處,川端康成從小就對生命的無常感有著深切的體會,而“物哀”的審美情趣又深深地嵌進了他的藝術生命里。尊重傳統的川端康成沿著日本傳統的審美之路前行,自然也會發現佛教的輪回轉世觀念中寄予著拯救的力量。他把輪回轉世看作是“闡明宇宙神秘的唯一鑰匙,是人類具有的各種思想中最美的思想之一”。川端康成崇尚“無”,在窮極的“無”中凝視世界的無常。在他那里,“有”和“無”是混雜在一起的,“無”是最大的“有”,是產生“有”的精神實質。生存和虛無都具有意義,死并不是人生的終點,它和生處于同一變化過程中。
川端康成的孤兒氣質使他形成了一種虛無悲觀的美學思想,他一直企圖超越虛無,也曾為此努力過,但很顯然把虛無和存在視為一體的川端是無法憑借一己之力完成這一超越的。而川端康成又希望通過文學“把我們對現實所發生的事的期待,持續地聳立在我們的內心世界里。”文學提供給我們一個窺視川端的視角,隨著他的文學作品越來越劃向虛無,川端的生命也歸于毀滅了。
“不滅的美”
川端康成自己在《臨終的眼》里說:“優秀的藝術家在他的作品里預告死亡,這是常有的事。”川端康成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并未把自己歸入此范疇。但當我們打開川端康成的作品時就會發現他的文學經常和死亡聯系在一起,他思考死亡,認為死的來臨會使藝術趨于佳境。在他看來死是最高的藝術,是美的一種表現。他常常把生、死總括起來感受,它們之間并沒有截然的界限,生即是死,死即是生,他往往憑借死把生引向永恒。《千只鶴》中的太田夫人,她死后比活著的時候更美,而且正是由于她的死,亂倫的罪惡被忽視過去了,道德上的缺失不再成為她的標記,留下的只剩下美與永恒。代表作《雪國》里,川端康成把自己幻化為主人公島村,當他看到大火奪去了葉子的生命時,作者是這樣描寫島村瞬時的感覺:“待島村站穩了腳跟,抬頭望去,銀河好像嘩啦一聲,向他的心坎上傾泄了下來。”個人的短暫生命被宇宙永恒所吞噬。葉子“由于失去生命而顯得自由了。在這瞬間,生與死仿佛都停歇了。”而島村總覺得“葉子并沒有死。她內在的生命在變形,變成另一種東西。”很顯然川端康成并沒有把死作為人生的休止符,在某種程度上死是生命的起點,是“無常”的流轉之相的一環,是一種美。
從表面上看,川端康成對于自殺一向持否定態度。在《臨終的眼》中他說過“無論怎樣厭世,自殺不是開悟的方法,不管德行多高,自殺的人想要達到的圣境也是遙遠的”,可是最終川端康成卻以他不贊成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人生。縱觀川端康成的一生可以看出,川端康成雖然反對自殺,不愿為死而死,但卻把死看成是一種“滅亡的美”,他十分欣賞自殺身亡的畫家古賀春江的一句名言:“再也沒有比死更高的藝術了,死就是生。”川端康成的一生都與虛無結伴而行,他抓不住“生”,卻選擇了以自己能把握的方式“死”。在日本自殺和恥辱完全不沾邊,用自殺來擺脫絕境是高尚的行為。川端康成的生死觀表現了他對日本傳統文化心態的追求和向往,他企圖通過死與生達成和解,延長自己的精神生命,給死一種美的形態。他把自己的生命也忘我地融入日本的傳統中去了,去追尋那千百年來不滅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