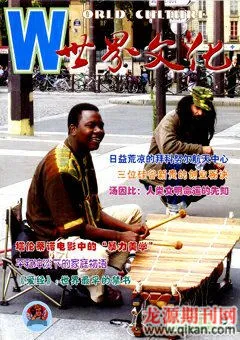多恩的真誠
約翰·多恩,1572年生于倫敦的一個富商之家,1631 年3月31日卒于倫敦。自小信仰羅馬天主教,但在1615年其42歲的時候改信英國國教,并于1621年起被任命為倫敦圣保羅大教堂的教長,成為當時著名的布道者。多恩是玄學派詩歌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創作啟迪了包括喬治·赫伯特、安德魯·馬維爾等一大批杰出詩人在內的所謂“玄學詩派”。作品包括愛情詩、諷刺詩、格言詩、宗教詩以及布道文等。詩歌節奏有力,語言生動,想象奇特而大膽,常使用莎士比亞式的機智的隱喻,人們稱之為“玄學派(Metaphysical poets)”。多恩和他開創的玄學詩派在18世紀遭到人們冷落,到了20世紀,現代派詩人葉芝、T.S.、艾略特等都從多恩的詩歌中廣泛汲取營養,多恩因而被看成是現代派詩歌的先驅,被公認為大師。“多恩是英國詩歌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多恩一生的生活和創作比較分明的分為兩個階段,他早年的創作主要是愛情詩和諷刺詩;晚年的主要成就是宗教詩和布道文。曾就讀于牛津和劍橋兩所學校,但未獲任何學位,卻廣泛閱讀了神學、醫學、法律和古典著作,因此在寫作中,他有時顯示出其不凡的學識、機智和幽默。后來在倫敦度過了一段世俗而耽于情欲的生活:1598年,他被任命為伊麗莎白宮廷中最重要的一位爵士托馬斯·伊戈爾頓的私人秘書,曾在歐洲大陸游歷,是宮廷中瀟灑倜儻、前途無量的紳士,1601年和托馬斯·伊戈爾頓爵士出身名門的侄女結了婚。從務實的角度說,這段婚姻是不明智的,遭到了上層社會的拒絕,多恩的事業陷入了低谷, 三十多歲的多恩已風光不再,他疾病纏身,窮困潦倒,郁郁不樂。這段時期之前的創作以愛情詩見長。
多恩的愛情詩不僅超越了一切伊麗莎白時代的傳統,而且超越了他以前所有情詩的典范式情感。“看在上帝面上,請閉上嘴,讓我愛你。”他的詩歌常以這樣驚人的句式和口氣開場,有人說多恩既能使人驚訝,令人憤怒,也能溫柔博學,他時而幻想,時而熱情,時而虔誠,時而絕望。有的時候,他會在一首愛情詩中將幾種情感集于一處。甚至在一些祈禱詩中也帶有一些情欲的色彩,這些作品反映的是全部人性,他赤誠地面對生命。以下兩句經常被人引用,這兩句話中濃縮了多恩詩歌的大部分特點:
愛情的神話的確在人的靈魂中萌生,
而人的身體如同記錄神話的書頁。
總體看他的愛情詩詩風放肆、大膽、奇妙,也比較輕浮,當時許多詩歌暗地里在男學生中非常流行,大家欣賞這種充滿了詭變油滑的調子。詩作中的很多奇喻也都頻繁被人轉用,好比《跳蚤》,由一只跳蚤可以通過吸食男女情人的血互相融合來誘勸女孩子對他的服從,男女雙方已經通過一種特殊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它先吮吸我的血液,然后是你,我們的血液在它體內融合在一起。”這樣跳蚤的體內就成為情侶秘密舉行婚禮的場所。還有他曾這樣描寫太陽,對于那些沉浸在愛情歡樂中的情侶來說,“太陽”是“愛管閑事的老傻瓜”, “月、日、鐘頭,那都是時間的破爛”。可見他寫詩歌寫得很聰明,用詞很新奇。然而有幾首卻寫也得非常真誠動人,尤其是寫給他妻子的那幾首。
一場熱病?
哦,可別死,因為在你逝去之后
我將會把所有的女人厭憎
以至當記起你是其中之一的時候,
連你,我也將不會贊頌。
然而你不會死,我深知;
把這世界撇在身后,才是死,
而在你從這世上離去之時,
整個世界將隨你的呼吸化為蒸氣。
或假如,在你,這世界的靈魂,
走后,世界尚存,那也只是你的尸體,
最美麗的女人,不過是你的鬼魂,
最杰出的男人,不過是腐臭的蛆。
哦,爭吵不休的各種學派,探索
什么樣的火將焚毀這人世,
卻無一有才能來鉆研這門學科——
她的這場熱病也許就是?
然而她不會就此消耗殞逝,
也不會長久遭受這不公的煎熬
因為需要有許多腐朽的機體
供給這樣一場熱病長久的燃料。
這些火燙的發作不過是流星熠熠,
它們在你體內的燃料很快就將耗盡
你的美,和所有部分,那也就是你,
則是不可變動的天穹。
然而緊抓住你,正合我的心意,
雖然它不可能在你體內堅守。
因為我寧可擁有你一個小時,
也不愿永久把其他一切占有。(傅浩譯)
在他的艷情詩中我們看到的更多是技巧和聰明,如果說他是真誠的,只能說他對女人這一事物本身很真誠,但不是專給予哪個的。隨著年齡增長才固定到了他太太身上,此后感情忠貞不移。
42歲時,經過認真的反復思考,多恩拋棄了對于家庭的忠誠,聽命于英國國教教會,開始了他人生和創作的第二個階段,直到他成為圣保羅大教堂的教長后才有了聲望,成為他那個時代最著名的牧師。那個早先撰寫愛情詩的勇敢放浪的年輕人變成了一個忍受上帝折磨敬畏神明的人,時時被死亡的想法和悔罪意識的侵襲所困擾。他排斥那“詩歌,我少年時的情人”,轉而熱愛“神學,我中年時的伴侶”。隨著時間的流逝,死亡對他的困擾也越發強烈。
有的人在讀了他的艷情詩后讀他的宗教詩,簡直訝異于竟是出自同一個人之手。所以有人不免懷疑早年那個放蕩不羈的多恩在多大程度上真誠地面對宗教,其傳記作家鮑爾德甚至說,多恩轉向宗教是出于沽名釣譽的勢利心理。但如果我們擺脫這種對詩人先入為主的不信任感,靜靜讀他那些晚期所寫的宗教詩歌那么會比較容易感覺到其中的真誠和境界:他努力以個人的不足,探索罪孽與懲罰。這是一個越來越沉重的靈魂,他似乎背負著罪行,這罪行有的來自于自己早年混亂的生活,有的來自于對人類總體的思考,有的則完全是出于宗教信仰,他艱難的前行。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讓他變得比較深沉,相比而言前期艷情詩歌則只是屬于年輕人的。
他的宗教詩充滿的是深層的真誠,他體會到了人的不足與無法完美,對這個罪行深感不安,“罪感”讓西方自有基督教后的文化充滿了神秘、崇高與憂傷的迷人風味,能引導人反觀自身,時時自省,為了約束和懲戒本性里的惡,于是渴望懲罰,這懲罰無論來自自己的雙手還是來自于他人,都在內心里獲得幸福感。具有負罪感并嗜好自虐的詩人并不少見,懲罰和懺悔就是靈魂擺脫這既定軌跡的重要方式。而多恩憂心忡忡的是這罪行如此之深,我們將無法擺脫。他不禁禱告上帝,別再把那罪歸還我們,既然您讓您的獨子用鮮血已經贖清。然而他越研究人、越研究自身、越與上帝對話,他越感到沉重。他不斷地詢問,您能饒恕嗎?這罪由我犯下,您能把它從罪惡中滌除干凈嗎?尤其是與您的懲戒相比,我還有更多的罪行。與多恩相比有的人即使只是在跟上帝對話,也要竭力為自己的錯誤和罪責開脫,總是會提及到很多導致犯錯的意外因素,多恩卻能夠如此坦蕩地面對自己和人群整體的罪,如果不是純粹的真誠也是一種勇敢。所以他轉向宗教是一種政治投資這種觀點值得懷疑。來看一首禱文:
啟應禱告之一,圣父
天國和他的父親,借助他
您創造天國,為天國創造我們,又為我們
創造別的一切,且永遠統治,請來把
我重造,我現在已毀壞破損:
我的心由于墮落,變成糞土,
由于自戕,而變得鮮紅。
從這鮮紅的泥土中,圣父阿,請滌除?
一切邪惡的顏色,好讓我得以重塑新形,
在我死去之前,可以從死亡之中飛升。
伯羅認為,多恩晚期的布道文、挽歌也好,早期的情詩也好,都不曾脫離后人稱之為“玄學”的關鍵要素———多恩始終在用奇思妙想,用出人意料的比喻和推理與他假想的持不同意見的聽眾辯論;他其實是在個人恐懼和群體給予的寬慰感之間徘徊,他展示了西方文化中以及人性深處令人矛盾不安的兩面性,一是對肉體的熱烈的愛和贊美,二是對靈魂升華的渴望。因此我們怎么能武斷他的哪一面是不夠真誠呢?矛盾性正是多恩的迷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