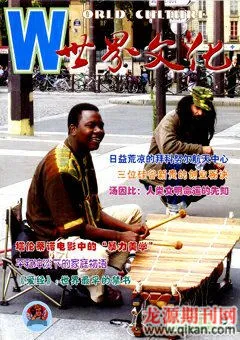一幅畫激發的靈感
《等待戈多》,這部風靡歐美大陸的荒誕派戲劇扛鼎之作,恐怕很少有人知道這是貝克特受到一幅油畫的啟迪和滋養而創作的,而對于這幅畫知道的人怕是更寥寥無幾了。貝克特作為20世紀舉足輕重的戲劇家和作家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貝克特和繪畫藝術的淵源似乎并不為大眾所知,事實上,貝克特可以說是個不折不扣的繪畫鑒賞大師,而他自己的創作也和繪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正如魯迅先生所指出的那樣:譬如蜜蜂,只有采過許多花才能釀出蜜。縱觀古今中外,凡是有所成就、能夠稱為大師的人物,無一不是通今博古,具備多方面的文化素養,塞繆爾·貝克特也不例外。貝克特出生于愛爾蘭一個新教家庭,早在青少年時期,他便對文學和各種形式的藝術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大學就讀于都柏林的三一學院,主修法文和意大利文,后來又跟著哥哥學習了德文,這為他日后廣泛涉獵歐洲文學、哲學大家的作品創造了有利條件。除了對文學哲學作品的喜愛之外,貝克特對其他形式的藝術品也十分迷戀,尤其是對繪畫藝術可以說到了癡迷的程度,他可以在一幅畫面前停留幾個小時,而對于大師名作他更是情有獨衷。其實,貝克特和繪畫藝術的淵源頗深。他在上世紀20年代初就迷戀上了繪畫,他的嬸嬸錫西·克萊辛是個頗有天賦的畫家,曾在都柏林大都市藝術學院受過教育,正是她培養了少年貝克特對繪畫的朦朧愛好。到了大學時代以及此后的時間里,他對繪畫的關注熱情有增無減,他最經常去的地方就是美術館,愛爾蘭國家美術館,倫敦、巴黎、柏林等歐洲各國大大小小的美術館都是他駐足的地方,遨游在大師們的作品中對他而言是一種莫大的享受。此外,貝克特交往的很多朋友都是畫家、藝術評論家及藝術品經營商等,他們之間的交流也在無形中加深了貝克特和繪畫的聯系。
貝克特對繪畫的興趣也是多層次的,并不局限于哪一家,哪一派,他不僅喜歡17世紀的荷蘭繪畫,而且尤其對現代繪畫傾注了很多熱情。貝克特生性聰明,記憶力驚人,很多作品他只要看過一遍就能牢記在心。它們的布景、色彩,人物的姿勢、形態、一顰一笑他都反復體味、推敲其中的精妙之處,并且尤為可貴的是,貝克特的鑒別比較能力也日益精深,就這樣他的藝術素養在無形中慢慢豐富厚重起來,也為日后的戲劇創作打下了堅實基礎,使他終生受益無窮。
相比音樂而言,繪畫是一種靜態的空間藝術,而我們也可以跨越時空的界限和心儀的它們目光融會,發出由衷地贊嘆。就在1937年的一天,在德國德累斯頓美術館的一個角落里,一場穿越時空的邂逅上演了。貝克特在這里發現了帕斯卡·戴維·費德里克一幅名為《兩個男人共賞月》的油畫,并立刻為之吸引,從那時起《等待戈多》的某些場景就開始在他內心深處的某個地方慢慢醞釀。直到十多年后,貝克特自己作為導演在柏林席勒劇院執導該劇時,他的腦海中仍然能夠清晰地浮現出這位德國浪漫主義畫家的作品,它已經深深地印在了他心里,只要需要隨時可以調用。
那么這幅激發了貝克特創作靈感的畫到底畫的是什么呢?這幅《兩個男人共賞月》,是19世紀浪漫主義時代德國的主要風景畫家費德里克的作品。這位畫家出生于德國東部靠近波羅的海的格拉夫瓦爾德,20歲時到丹麥求學,后來進入德累斯頓美院,此后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德累斯頓生活直至逝世。1805年,歌德將魏瑪政府的藝術大獎頒發給了這位當時名不見經傳的浪漫派風景畫家。他一生創作頗豐,主要以風景畫居多,作品有《冰海沉船》、《霧端的漫步者》等。
費德里克最初是以故鄉波羅的海的創作而聞名,這些畫作大多以深褐色為主,體現出新古典主義對于結構的強調,同時,他也非常注重對光線效果的控制,大多顯示出夜間的模糊效果。而在求學期間,他學會了如何運用一種現代的方式來展現壯闊的自然景觀,并發明了用細密輪廓來描繪圖畫的方法。后來他嘗試以宗教和全國性主題為風景畫題材,如《枯橡樹的夏景》。他偏愛用鮮綠和藍色來表現自然風光景物,極力反對用科學的理性來分析自然景象。他一生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風景畫,大多描繪蒼涼廣闊的風景、海洋、船只、哥特式建筑廢墟、沉思自然的孤獨者。畫面充溢著靜謐、空無的氣氛,而人物在這樣恢宏浩蕩的背景下無疑就成了點綴,這種畫面景觀和人物的組合形成的鮮明對比使觀者對自然產生強烈的敬畏感,對人生和未來有一種茫然的困惑。或許是由于自身命運的坎坷和人生的無常,使費德里克偏愛逆光中的風景,尤其是人物孤獨的背影,這樣往往使得作品彌漫著一種神秘氣息,使之后來成為“象征主義”繪畫者靈感的來源。
這幅《兩個男人共賞月》是典型的費德里克式的作品,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這樣一幅畫面:夜晚空曠寂靜的野外小路上,兩個男人站在一棵高大的禿樹旁靜靜地凝望著月亮,其中一人親密地把手搭在另一個人的肩膀上,月光勾勒出他們的輪廓。整個畫面以褐色為主,只有月亮微微的淡黃算是一抹亮色,同樣我們看到的是人物的背影,在大自然的曠野中顯得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此外,色彩和光線的控制也顯示出很高的水平,為整個畫面營造出一種朦朧的神秘美感。我們應該也不難體會到畫家對這幅畫傾注的感情,人類的孤獨迷茫,未來的不可知,但卻仍舊懷抱一絲幻想:那黃色的光雖然微弱,但畢竟是一種希望的象征,這也正是浪漫主義時代整個人類情感的濫觴。
身處20世紀動蕩時代的貝克特站在這樣一幅畫前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什么一下子攫住了貝克特,深深打動了他,觸發了他創作的沖動,這些我們都無從得知,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貝克特把這幅畫刻在了自己腦海中,從人物動作、色彩、布景,連最微小的細節都不放過,就像他對所有其他大師作品的癡迷一樣。然而,貝克特之所以成為貝克特并不僅僅憑借這份欣賞和癡迷,更多的是一種吸收借鑒,他有一種非凡的力量,使他懂得從一種藝術形式中汲取營養,然后將其吸收轉化,再加以創新為我所用。
我們知道戲劇是一種綜合性的藝術,它融合文學、音樂、舞蹈、繪畫等其他藝術形式于一體,而貝克特對繪畫的青睞在他的戲劇中也表現得很明顯。貝克特一直非常關注“圖像”,從這一點來看,說貝克特是個視覺藝術家也許并不為過,在他的戲劇和晚期的電視作品中他都非常注重舞臺形象的塑造。難怪藝術批評家沃納·斯皮斯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那種可以同時體現繪畫、物體藝術、行為主義、或錄像制品的傳奇時代的基本文本在哪里?”接著,他回答道:“在這一方面我們首先遇見了貝克特。”可見貝克特作品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同時也彰顯了繪畫對貝克特戲劇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是在舞臺形象的塑造上,對大師名畫的熟稔和高超的鑒賞力使貝克特受益良多。仍以《等待戈多》為例,費德里克的油畫給貝克特帶來了創作靈感,但我們發現貝克特最終呈現給觀眾的舞臺形象和營造出的氛圍卻與這位浪漫主義大師的油畫迥然不同,帶給我們新的更強的震撼和視覺沖擊,而這恰恰是貝克特的力量所在。另外,除了費德里克的這幅畫作之外,《等待戈多》的布景還明顯受到荷蘭畫家老勃魯蓋爾的作品影響,如其中一幅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當然,貝克特對這幅畫進行了二度創作,使之更符合自己戲劇的要求,幸運兒和波卓一前一后上場,瞎了眼的波卓跟畫中倒地的人物相似。而劇中4人摔倒在地的場景又跟老勃魯蓋爾的另一幅畫《世外桃源》非常相似。貝克特1937年在慕尼黑的舊美術館看到過這幅畫。由此可見,繪畫藝術對貝克特的戲劇影響多么巨大,也表現了貝克特在對不同藝術形式的駕馭方面的非凡能力。
有人把荒誕派戲劇稱為“反戲劇”,因為它確實與西方傳統的戲劇大相徑庭,似乎它的出現完全割裂了與傳統的聯系,是一種斷裂,但通過對《等待戈多》背后名畫的探尋,我們不難發現,其實,正因為有了深厚傳統的滋養,貝克特才能承前創新,確立自己的風格。
最終,貝克特成功了,《等待戈多》給他帶來了世界范圍的聲譽,他也因為在戲劇和小說方面的貢獻而榮膺1969年諾貝爾文學獎,這無疑是對他創作生涯的最大肯定,也是他長期接受藝術熏陶、不斷孜孜以求提高自身藝術修養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