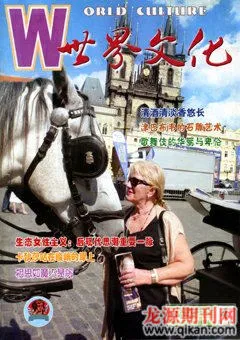《保佑我,烏爾蒂瑪》
魯?shù)栏!ぐ布{亞(1937- )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美國奇卡諾(墨西哥裔美國人)文藝復(fù)興的一員主將,迄今已出版長篇小說10部、短篇小說集2部、史詩2部、散文集1部、青少年文學作品8部,并有7部劇作上演,贏得了“奇卡諾文學的教父和領(lǐng)袖”、“最受好評、影響最廣泛的奇卡諾作家”等美譽,在西語裔族群內(nèi)部和主流社會都享有不凡的聲望。長篇小說《保佑我,烏爾蒂瑪》(1972)是他的處女作,如今已被公認為奇卡諾文學的經(jīng)典之作。前美國第一夫人勞拉·布什曾列出“各年齡段讀者必讀的10本最好的書”,這部作品便是其中之一。
《保佑我,烏爾蒂瑪》以20世紀40年代中期的美國新墨西哥州瓜達盧佩鎮(zhèn)為背景,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講述墨西哥裔主人公安東尼奧·馬雷(昵稱托尼)6歲到8歲的經(jīng)歷,具有成長小說的典型特點。托尼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有三個哥哥、兩個姐姐,父親來自大平原上一個世代放牧的家族,崇尚居無定所、自由自在的生活,母親的祖先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家族長年在河谷從事農(nóng)耕,過著安穩(wěn)、虔誠的生活。故事開始前,托尼從未離開過家,頂多由父母帶著在禮拜天去教堂,或夏末去舅舅家?guī)兔κ崭钋f稼,他的小世界單純寧靜,唯一的價值觀是母親灌輸?shù)奶熘鹘探塘x,唯一的煩惱是父母期望的截然對立令他無所適從:是迎合父親的愿望做一個牛仔,還是聽從母親的安排成為農(nóng)夫,甚至神父?從7歲前的這個夏天開始,托尼的小世界逐漸向外面的大世界延伸,遭遇了眾多陌生的人和事之后,他的生活變得復(fù)雜和動蕩。先是父母把孤苦無依的老人烏爾蒂瑪接到了家里,這個聞名遐邇的民間藥師不僅與托尼結(jié)成了忘年交,還讓托尼認識到不光神父和醫(yī)生能夠治病救人,兼用草藥和巫術(shù)的民間醫(yī)術(shù)同樣具有這種功效,其解咒驅(qū)邪的能力甚至令宗教和現(xiàn)代醫(yī)學望塵莫及。緊接著,托尼成了一名小學生,走出說西班牙語、吃玉米粉圓餅的家,進入說英語、吃三明治的學校,上學第一天,托尼便意識到自己是個異類,只能從其他班上同樣背景的孩子那里找到集體的溫暖。不久,二戰(zhàn)結(jié)束,三個哥哥從戰(zhàn)場歸來,見過大世面的他們難以適應(yīng)小鎮(zhèn)的生活,又相繼去了遠方的大城市,托尼由此知道,在新墨西哥的農(nóng)村以外,還有一個迥然不同的城市世界。一年級的最后一天,托尼從小伙伴那里聽到了河谷水神金鯉的傳說,后來又親眼看到了金鯉,這才明白除了天主教的上帝、耶穌和圣母瑪麗亞,還有不少人信仰異教的神靈,就連他自己也深受吸引。此外,托尼發(fā)現(xiàn)抽象的天主教教義根本無法解釋成人世界的善與惡:妓院這等淫邪之地,為什么大人們會去光顧,連哥哥也不例外?飽受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的二戰(zhàn)老兵盧皮托開槍打死了治安官,隨后又被鎮(zhèn)上的居民射殺,他們是不是都該下地獄?特雷門蒂奧和三個女兒利用巫術(shù)作惡多端,上帝為什么不懲罰他們,反而聽任他們下咒傷害盧卡斯舅舅和特列斯?當積善行德的烏爾蒂瑪挺身而出,與這伙邪惡勢力作戰(zhàn)時,上帝為什么無動于衷,聽任他們殺死了納西索和烏爾蒂瑪?shù)氖刈o精靈貓頭鷹,又最終置她于死地?
這部小說淋漓盡致地展示了托尼面對陌生大世界時的惶惑、恐懼、懷疑、彷徨和負疚,這些事情難以理解,不可捉摸,卻又不可避免地影響著他的生活,影響著他所愛的親人和朋友。他試圖去把握這個紛繁蕪雜、充滿了矛盾與沖突的大世界,卻發(fā)現(xiàn)自己既有的價值信念和認知框架是無能為力的。將他帶出困境、送他走上成熟之路的是烏爾蒂瑪,她扮演了成長小說中必不可少的引路人或?qū)熃巧鯛柕佻數(shù)淖饔貌皇墙o托尼的問題提供確定的答案,而是引導(dǎo)托尼去正確地思考問題,這是找到答案的前提和關(guān)鍵。在烏爾蒂瑪看來,世間萬物環(huán)環(huán)相扣、因果相連,是一個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體,恰如“匯聚到河流并注入大海的正是來自月亮的甘甜雨水。假如沒有月亮之水補充給海洋,海洋便會干涸。海洋中苦澀的海水被太陽帶到天空,又重新變成月亮之水。沒有太陽,就不會形成消解黝黑大地饑渴的甘露。”因此,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一個事物,只看到局部,看不到事物之間的普遍聯(lián)系;也不能采取單一的視角,以偏概全,看不到事物的方方面面;更不能固守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看似不可調(diào)和的對立面往往構(gòu)成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相互轉(zhuǎn)化的關(guān)系。在烏爾蒂瑪?shù)膯l(fā)下,托尼認識到自己遭遇的諸多矛盾沖突(父母對他的不同期望、天主教的上帝與異教的金鯉、天主教與民間醫(yī)術(shù)、西班牙語文化與主流文化、城市與農(nóng)村等)其實并非相互排斥,勢不兩立,他所要做的就是要兼收并蓄,在消化吸收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出一個全新的、完整的自我。恰如特雷莎·卡諾扎所言,這部小說的主旨“不是說成長要求人們在矛盾的選項中進行排他性的選擇,而是說智慧與經(jīng)歷能夠讓人們的視線越過差異,看到統(tǒng)一與和諧”。從烏爾蒂瑪?shù)难詡魃斫讨校心徇€領(lǐng)悟到,宇宙間善惡兩股力量此消彼長、循環(huán)往復(fù),此乃生命的常態(tài),個人應(yīng)該學會發(fā)現(xiàn)人世間的真善美,在積極向善的同時,保持生活的勇氣,以“心靈的魔力戰(zhàn)勝人生的悲劇”。故而在小說的結(jié)尾,托尼能夠坦然面對烏爾蒂瑪?shù)乃劳觥?br/> 《保佑我,烏爾蒂瑪》有著濃厚的自傳色彩。安納亞的兒童時代便是二戰(zhàn)前后在新墨西哥州的一個小鎮(zhèn)度過,父母分別來自游牧家族和農(nóng)耕家族,同樣推崇本族裔的民間醫(yī)術(shù),兄弟姐妹也是從小信仰天主教,在家說西班牙語,在學校說英語,哥哥同樣是二戰(zhàn)老兵,就連他因游泳差點致殘的經(jīng)歷也寫進了書中的溺水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這部小說是安納亞的個人記憶或私人敘事。然而,為自己的成長樹碑立傳不是安納亞的創(chuàng)作目的,在他眼里,“作家有點像巫師,能夠用故事影響整個族裔,治病救人。這一直是故事的功能之一。我常寫我們族裔的巫師和女巫,這使得我與這個傳統(tǒng)相聯(lián)。”換句話說,安納亞意在借助這部私人敘事,履行治病救人、服務(wù)公眾的使命。如果我們回溯到《保佑我,烏爾蒂瑪》的創(chuàng)作和出版年代,便不難發(fā)現(xiàn)安納亞針對何種疑難雜癥開出了救世良方。
眾所周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社會,民權(quán)運動、反越戰(zhàn)運動與青年學子的“反現(xiàn)存體制”運動糾結(jié)聚合,訴諸激進手段推進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全方位的破舊立新,血腥沖突、政治謀殺、街頭游行、校園動亂此起彼伏,席卷全國。1963年,安納亞從新墨西哥大學英語系畢業(yè),成了阿爾伯克基市的一名中學教師,他一邊攻讀英語專業(yè)及指導(dǎo)與咨詢專業(yè)的兩個碩士學位,一邊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保佑我,烏爾蒂瑪》,還參與了反越戰(zhàn)運動。安納亞回憶說:“越南戰(zhàn)爭導(dǎo)致的全國性大爭論考驗著這個國家,考驗著各個社群和家庭。我認識的大多數(shù)教育系統(tǒng)的人都反對這場戰(zhàn)爭。我散發(fā)請愿書,要求中止越戰(zhàn),費盡心力組織了阿爾伯克基的第一個教師工會”。與此同時,安納亞注意到墨西哥裔同胞掀起了奇卡諾運動,全面清算美國社會對本族裔的政治壓迫、經(jīng)濟剝削和文化消音:1965年9月,加州南部墨西哥裔農(nóng)業(yè)工人罷工;1967年6月,墨西哥裔武裝襲擊新墨西哥州阿里巴河縣法院;1968年,東洛杉磯墨西哥裔高中學生集體罷課;1969年3月,第一屆墨西哥裔青年大會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召開;1970年1月,德克薩斯州聯(lián)合人民黨成立;1970年8月,墨西哥裔在洛杉磯舉行大規(guī)模反越戰(zhàn)示威。“奇卡諾人的政治運動在蔓延,”安納亞在自傳中寫道,“肯尼迪總統(tǒng)遇刺,奇卡諾人深受震撼。黑色星期五被視為反動勢力的象征性反擊,他們掌握著這個國家的權(quán)力,不愿與被壓迫的人民分享。在如此動蕩的歲月里,我逼迫自己學習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復(fù)雜工序。”歷時7年,安納亞終于完成了《保佑我,烏爾蒂瑪》。1971年,這部小說的手稿榮獲旨在推動墨西哥裔文學創(chuàng)作的昆托·索爾文學獎,翌年出版,立即風靡整個墨西哥裔社區(qū),安納亞由此成為奇卡諾運動中文化領(lǐng)域的中堅人物。
作為六七十年代激進政治的見證者和溫和的參與者,安納亞非常清楚整個美國社會正處于一個重大的轉(zhuǎn)型期,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社會對立漸趨嚴重,各種不同的新主張、新思潮紛紛涌現(xiàn),對傳統(tǒng)的價值體系造成強有力的挑戰(zhàn),新舊力量之間的角逐往往訴諸于暴力沖突和流血斗爭。如霍斯特·湯恩所言,在那個年代,許多美國人都體會過“面對不可思議之事的驚駭”,每個人都想對這場社會大變革達成理性的認知,都想知道美國政治和文化的確切走向。具體到族裔政治,這個時期除了黑人民權(quán)運動和奇卡諾運動,還有亞裔運動、波多黎各人運動、印第安文藝復(fù)興等,各個少數(shù)族裔均以前所未有的聲勢,要求在各個領(lǐng)域獲得與白人同等的權(quán)利,改變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在白人主流社會,保守派和改革派各執(zhí)己見,爭論不休。在各個少數(shù)族裔內(nèi)部,激進派與溫和派、分裂主義與同化主義的不同聲音不絕于耳。如果說今天實行多元文化主義的美國是一個成年人,六七十年代便是他的兒童時代,恰如《保佑我,烏爾蒂瑪》中的小托尼,面對生活中紛至沓來的變化,面對新舊差異、矛盾沖突,茫然四顧,不知所措。在安納亞看來,烏爾蒂瑪?shù)闹腔鄄粌H適用于年幼的托尼,也適用于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社會:人們應(yīng)該以整體的、全面的、辯證統(tǒng)一的眼光去審視和認知社會的新舊矛盾,在盡可能獲得理性把握的基礎(chǔ)上,海納百川,以平等、開放、包容的胸襟彌合對立,調(diào)和差異,將矛盾與沖突最終轉(zhuǎn)化為和諧與統(tǒng)一。有評論指出,安納亞通過這部小說傳達的信息是“和諧和對他人(包括我們別無選擇時血戰(zhàn)到死的敵人)的同情”,此話不無道理。不僅如此,托尼將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傳統(tǒng)、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綜合融會,建構(gòu)新型自我的做法,其實也是安納亞對個人和族群如何調(diào)和主流文化與族裔文化之矛盾,建構(gòu)新型文化身份的有益建言。
“在這部小說出版的年代,它是獨一無二的;它為墨西哥裔提供了文學滋養(yǎng)。它成了一面鏡子,可以映照過去的安定世界,也成了一把標尺,可以衡量未來的世界”,正因為如此,它贏得了墨西哥裔讀者的認同,截至1978年,在沒有重要媒體刊登書評的情況下售出8萬冊。1994年,華納出版社將這部已經(jīng)重印21次、售出30萬冊的作品推向美國主流社會,至今暢銷不衰。《保佑我,烏爾蒂瑪》之所以能夠跨越種族鴻溝和時空差異,成為美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西語裔暢銷作品,不僅是因為小說中反映的奇卡諾文化特性很容易得到相同族裔讀者的認同,勾起不同族裔讀者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因為這部墨西哥裔成長小說中包含著每個人、每個時代、每個社會都需要的智慧。畢竟,普天之下,誰不向往自身的和諧統(tǒng)一與人類社會的和諧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