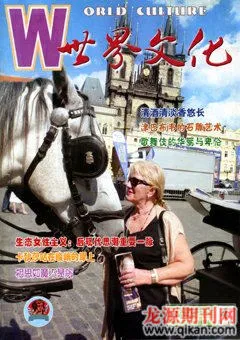自由是人無法逃逸的宿命
讓·保羅·薩特(1905~1980),二戰(zhàn)后西方存在主義哲學(xué)和文學(xué)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作品思想深刻、內(nèi)容豐富,涉及小說、戲劇、評論、哲學(xué)等多種形式,其中,自由是他反復(fù)彈奏的主旋律——自由并非人的理想,而是人無法逃逸的宿命。
薩特在文學(xué)方面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他獨具風(fēng)格的戲劇創(chuàng)作,他的戲劇是他哲學(xué)思想的闡明和解釋,有關(guān)自由和選擇等本體論哲學(xué)問題的藝術(shù)闡釋,在《蒼蠅》、《禁閉》)、《死無葬身之地》、《臟手》、《魔鬼與上帝》、《阿爾托納多隱居者》等劇本中表現(xiàn)尤為突出。下面,我們就逐一分析《蒼蠅》、《禁閉》、《魔鬼與上帝》三部戲劇中自由觀的發(fā)展變化。
《蒼蠅》取材于古希臘埃斯庫羅斯的悲劇《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主人公俄瑞斯忒斯是阿伽門農(nóng)和克呂泰涅斯特拉的兒子。阿伽門農(nóng)率希臘聯(lián)軍遠(yuǎn)征特洛亞,歸來后被他的妻子和她的情夫埃癸斯托斯殺害。不滿三歲的幼子俄瑞斯忒斯被大兵帶出,十五年后重返故鄉(xiāng)阿耳戈斯,報了殺父之仇。
俄瑞斯忒斯的復(fù)仇行為體現(xiàn)了人獨立自由的意志,他的一系列選擇體現(xiàn)了對世俗、虛無和神祗的超越。當(dāng)俄瑞斯忒斯遭遇到邪惡的國王埃癸斯托斯、堅信無為主義的家庭教師、充滿奴隸意識的城邦百姓和因復(fù)仇而悔過的姐姐厄勒克特拉等相反力量的阻止時,他仍堅持自我。他拒絕了天神朱庇特為他安排的“命運”,殺死了仇人(叔父和母親),替父報仇,從而實現(xiàn)了自由。《蒼蠅》形象地表現(xiàn)了薩特存在主義的自由觀。所謂的“自由”是一種選擇和行動的絕對性,人擁有精神上的絕對自由以及追求自由的絕對權(quán)力。劇中的埃癸斯托斯引誘了王后,殺害了國王,然而他卻“沒有欲望,沒有愛情,沒有希望地活了這么多年”,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自由選擇的結(jié)果,而是受“惟命是從”的傳統(tǒng)因素的影響,因此埃癸斯托斯是一個沒有自由的“自在的存在”。而俄瑞斯忒斯正好相反,他堅信“我自由了,……自由像雷一樣打到了我的頭上。”他自由地選擇了為父報仇,選擇了不受制于那個讓人“惟命是從”的“秩序”,而且在明知可以回避復(fù)仇女神(劇中的蒼蠅)的情況下,選擇了向城邦百姓講明真相:“我愿意承擔(dān)這罪行的責(zé)任……你們的過錯,你們的悔恨,他們深夜的苦惱和憂慮,埃癸斯托斯的罪行,這一切都是我的,我承擔(dān)一切。”然后離開阿耳戈斯,將那群蒼蠅帶走。薩特堅信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人就是人的未來”、“人注定去創(chuàng)造自己”等觀點在此表露無遺。
《禁閉》是薩特早期創(chuàng)作的另一部重要哲理劇,全劇幾乎無情節(jié)線索可循,是典型的“境遇劇”。在薩特的存在境遇里,自由是無處不在的、自由是沒有標(biāo)準(zhǔn)的,人只要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人便自由了。每個“自我”總是生活在與他人的關(guān)系中,被編織在周圍的環(huán)境里,薩特在這部探討自我與他人關(guān)系的戲劇里提出了另一種生存境況——在他人的目光下,“我”成為他人的對象,力圖從他人的評判中確認(rèn)自身,也就是說,個人的自由必須建立在他人的自由之上。
劇中的三個罪犯——戰(zhàn)爭逃兵加爾森、同性戀者伊奈司、溺嬰犯埃司泰樂被置于一座特殊的地獄。這個地獄就是一個典型的存在主義“境遇”—— 一間第二帝國時代的客廳,沒有刑具,沒有窗子,沒有床,燈光長明。每個人都無法逃脫睜著眼睛注視他人與被他人注視的境遇。加爾森為了躲避在戰(zhàn)爭中當(dāng)逃兵而被槍斃一事的揭露,拼命想逃離這間屋子。可是門卻怎么也打不開。他無法獲得自由的原因是他總在另外兩個鬼魂面前極力掩蓋自己,不敢承認(rèn)自己是個逃兵,也就是說,他一直被“逃兵”這個可恥行為的傳統(tǒng)觀念束縛著,因而只能成為一個沒有“自由”的“自在者”而存在。換言之,加爾森總想沖出這個令人痛苦的境遇是因為他不敢以自己的本來面目示人,而當(dāng)他勇敢地說出自己的真實面目時,自由之門洞開。
加爾森在經(jīng)歷了一系列被窺探、被追問的折磨后,勇敢地做出選擇,由一個懦夫、膽小鬼變成了一個敢于面對自我與他人的“自為者”,他對人的“存在”觀念也發(fā)生了本質(zhì)的變化:認(rèn)識到了自由選擇的命定性、非逃避性和選擇“境遇”的有限性。一切都只與人自身相涉,因此人無論如何必須做出自己的選擇,因為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其次,由于上述原因,自由的選擇必須對其后果負(fù)責(zé),因為沒有任何東西左右或決定自由的選擇,所以自由的選擇本身就決定了它的非逃避性,它不能逃到某種其他‘境遇’中,比如《禁閉》中的那間客廳的門外;這樣一來,自由的選擇就有其‘境遇’限制,就是說,人的選擇(其行動)必然處于‘他人’的‘眼光’之下,想逃避也是逃避不了的;又因為自由選擇的非逃避性和‘境遇’限制性,自由選擇的命定性才具有其絕對性和對他者的否定性。”任何人都無法逃離他人的“目光”,人們總是用他人擁有的、他人給予我們的手段來評判我們自己,因此,要想獲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須實現(xiàn)人與人之間價值觀念上的相互獨立性,他人價值觀念的實現(xiàn)、自由的實現(xiàn)就成為自我獲得自由的前提。
《魔鬼與上帝》是一部以農(nóng)民起義為背景的戲劇,場面宏大、氣勢滂沱,融歷史傳奇與現(xiàn)代哲理為一體,該劇通過對人與上帝、人與絕對關(guān)系的討論,將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觀念上升為戲劇沖突的核心內(nèi)容。主人公格茨是一個貴族與農(nóng)民的私生子,不僅遭到貴族們的唾棄,也受到百姓的詛咒。他在戲劇中經(jīng)歷了三個重要的人生階段。
早期的格茨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實行絕對的惡,把與上帝對抗作為自己存在的理由,他通過作惡來證實自己的存在,并從中感受到自己的生存價值。劇情一開始格茨就狂妄地宣稱:“惡是我生存的理由”,“他(上帝)知道我殺死了兄弟,他非常痛心……我犯下了滔天大罪,公正的上帝也無法懲罰我。”在傳統(tǒng)觀念中,上帝是善的化身,格茨以為通過作惡就能使上帝顯靈,然而上帝并沒有出現(xiàn),因此他就無法通過上帝來確認(rèn)自己的存在。上帝愈是不顯靈,他就愈想作惡,“我作的惡跟他們作的惡不一樣,他們是為了追求奢侈的生活,或者為了謀取私利才作惡的。而我是為了作惡而作惡。”然而,這種絕對的惡如同絕對的自由一樣,是不存在的,他只是用惡來掙脫善的束縛。因此,當(dāng)神甫海因里希告訴他:“上帝的意旨是使善在人間行不通”、“人人都作惡”時,格茨改變了立場,他決定摒棄暴力、廣行善事,以此繼續(xù)和上帝對抗。這就是中期踐行“絕對的善”的格茨。他把自己的土地分給農(nóng)民,請教師教農(nóng)民識字、宣傳博愛思想、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太陽城”……然而,這些諸多表現(xiàn)為“善”和“愛”的行為,并沒有產(chǎn)生真正的“愛”,最終結(jié)果反而是更壞的惡。“我的善心比我的劣跡更具有毀滅性”,棄惡從善的格茨并沒有在行善的過程中給別人帶來任何幸福,在農(nóng)民領(lǐng)袖納斯蒂看來,格茨的行為只能給農(nóng)民一時的幸福,卻嚴(yán)重地削弱了農(nóng)民的斗志,使他們的反抗性喪失殆盡,最終將使農(nóng)民的土地得而復(fù)失。格茨原本是一個為了反抗上帝而無惡不作的人,但當(dāng)他決心行善,并愿意承擔(dān)一切罪惡之時,上帝的意志依然沒有在場,他反抗的是虛無。無論是作惡還是行善,結(jié)果都是以毀滅生靈的慘敗告終。格茨踐行“絕對的惡”和“絕對的善”之所以處處碰壁的原因是個人的自由在現(xiàn)實中會受到方方面面的約束和限制。
后期的格茨在善與惡的抉擇中終于意識到上帝是虛無的,覺醒后的格茨摒棄了單純的善惡觀念加入到人的實際斗爭中來,在實現(xiàn)其社會價值的同時獲得了人的自由。行善,僅有抽象的向善的愿望是不夠的,還需要腳踏實地地去踐行,不能“沒有行動,而只是做了愛的姿態(tài)”,只有勇于承擔(dān)責(zé)任,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善人,從而實現(xiàn)個人的自由。放棄了一味行善的格茨選擇了參加農(nóng)民起義軍,并重新當(dāng)上了將軍,試圖憑借自己的自由來領(lǐng)導(dǎo)更多的人取得自由。雖然格茨自己也不能確定到底能否成功,但是他選擇了這樣做,也就是選擇了自己的自由存在,他不再是為對抗上帝而存在,而是為自己而存在,他在投身于社會的實踐中看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從而獲得了自由。
薩特強調(diào)實現(xiàn)個人自由必須打破他人和社會的藩籬,人就是“虛無”,人的意義必須由自己決定,而不是寄托于某種理想中,激勵人們奮起追求個人自由,實現(xiàn)個人價值。二戰(zhàn)后,薩特積極批判社會,并熱心參與社會政治實踐活動。在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fēng)暴”中,薩特鼓勵學(xué)生起來行動奪取政權(quán),其自由觀已發(fā)展為實現(xiàn)社會群體整體的自由。總體而言,薩特的自由觀發(fā)展過程是:精神自由——個體與他人的共同自由——社會整體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