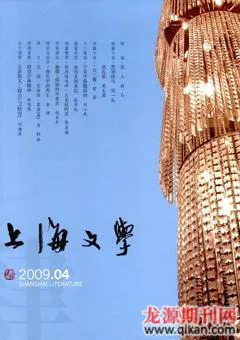仰望古典精神
“一個人的成熟度是最不以年齡劃分的。”從本期作者林鳴崗身上,再次非常典型地印證了這個顛撲不破的公理。
林鳴崗是旅法著名畫家,主攻西洋油畫。之所以特別要加上“西洋”二字,是2002年第一次見到他的畫冊《人物素描》時,我完全被震驚了,雖然當時的中國已經非常“全球化”,我看過的各種中外畫展也有相當數量,但林鳴崗的人物素描給我的第一波感受是:“哎呀,這才是真正的藝術!”
這是因為,他的每條線里面,都盛著“藝術”兩個字,其濃度若用深淺顏色來標明的話,應為紅色——這種感覺,我許多年前也有過一次,那是“文革”中看到日本松山芭蕾舞團演出的《白毛女》,同樣的人物,他們的“藝術感”怎么和我們的如此不同?特別是女演員們個個輕盈柔美,動作嫵媚,即使不懂技巧也能感覺出松山版的《白毛女》演繹出了芭蕾藝術之美。
與藝術的“遠”與“近”,是藝術家們終生思考的問題,無限地走近藝術,是人類永遠的追求。
那么,林鳴崗為什么能離藝術的珠穆朗瑪更近一些呢?除了他在法國受過科學而嚴格的技術訓練之外,我個人以為,重要的應與他的“成熟度”有關——已經過了知天命之年的林鳴崗,在世俗的成熟度上卻老是過不了成人關,他的心思只愿意對藝術之門開放。比如,《仰望古典精神》一文,這么充滿感情,熱烈地歌頌古典主義,頂禮膜拜之際大聲呼喚回歸,在今天這個處處浮辭艷彩的世界里,還有幾個藝術家能想到?能做到?能愿意做?
韓小蕙
古典主義是一種精神產物,超越一切的風格,超越一切的流派。它絕對是最大的、最悠久的流派。它沒有國界,兩千年前發端于古希臘、古羅馬,越過意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德國、俄羅斯……15世紀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并于17世紀三四十年代盛行于法國,先后流行了兩百年。法國的布瓦洛1636—1711,著有《詩藝》一書,繼承并綜合了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的觀點,完整地提出了符合當時時代要求的古典主義理論。這一古典主義文藝理論著作,被俄羅斯的普希金稱為“古典主義的《可蘭經》”。它推進了德國古典主義的哲學、美學,形成世界古典主義哲學、美學理論的高峰。如今世界的“流派”太多了,世界的“主義”也太多了,但不管是以前還是將來,我想沒有一種主義或流派會比它更高深,更有永恒的生命力!因為時間和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她長存的理由。當代“流派”和“主義”層出不窮、花樣百出,但很多都是過眼云煙,瞬間即化為烏有的東西,有的不過是它身上的幾片葉子和幾根枝椏,很難和它根深葉茂、粗大壯實的大樹本身相比……
古典主義和藝術迫使我們有一種神圣仰望,向上追求理想的境界。它是具有永恒價值寶藏的大山,使我們在欣賞的時候,心中泛起愛意,給我們欣喜和溫暖。它具有隱藏的道德和人格力量。它高舉永不過時的唯美、均衡、理性、數學大旗,是人類精神里最有價值的財富,取之不盡,用之不完。古典主義不是單單屬于繪畫、文學、音樂、建筑領域里的東西,它是人類經過長久實踐,探索出來的一條陽光大道。任何學科只要具備這種精神,都會勇往直前,無往不勝。最偉大的藝術家,最偉大的人物,都時時受著古典主義的引導,只有它才把一個個藝術家引進更高的大殿,有了更多神性的啟示,接近神靈的境界。古典主義的終極目標是對真、善、美的追求,沒有功利思想,只有犧牲與奉獻精神。難道這些東西也過時嗎?
美的永遠守護者
古典主義總有個“審美”的理念。這就迫使制作者先有個“美”的認識和高于一般生活的“審美意識”和追求。一個人只有追求美,才有可能接近善,離開惡。如果連丑、惡、假都分不清,更不知美為何物了。只有美才可能是善,丑接近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就是這個道理嗎?離開了美,也就離開了人與動物的區別。因為只有動物不知美為何物,無法區別美與丑,善與惡。
古典主義者永遠使用優雅的手法去塑造愉悅視覺、震蕩心靈的作品。即使表達死亡、血腥、恐懼、憤怒、暴力也仍然從容不迫,感覺像是在花園里遇到的事。而不僅是一張張污面垢發的再現,呆頭、傻笑的描述。即使表達情色,也決不是兩腿分開的架勢。他們的語言永遠是杰出的、鮮活的。有高低徘徊,有濃淡相間,有光影晃動,有色彩照應。既不是平庸的寫生作品,也不是拙劣的即影即有的照片。總是讓人在長久的凝視中慢慢去接受藝術家的理念。在不知不覺中感受一種永比真實世界更有情趣的畫面。魯本斯、大衛不都是這樣嗎?這就是為什么有現代大師稱號的達利和畢加索一見到維拉斯貴支的作品就要點頭彎腰。
古典藝術表達最卑鄙的欲望,最可恥的行為,仍然使用最委婉的形式。就像茅屋里面住著一位美麗又可愛的公主,還棲息著一只漂亮的孔雀。在卑鄙和絕望中,仍充滿著陽光和希望。我們常常會在絕對寧靜中享受一種崇高和敬畏之情,我們的動物性減少了,似乎變成另一種有點高尚的人類。我多次到羅馬的梵蒂岡,每次都要細看“拉奧孔”,每次都會感到心靈的震撼。當我重新再讀萊辛的《拉奧孔》時感受就更加深刻了,一件兩千多年前的雕塑作品,能被后代的人詠讀再三,頂禮膜拜是一種什么力量和魅力?而且同樣能深深感動一個遙遠的東方人。我相信同樣感動的決不是我一個人(溫克爾曼、萊辛還是德國人呢)!我完全贊賞他的論斷“凡是為造型所能追求的其他東西,如果和美不相容就須讓路,如果和美相容,也至少須服從于美”。“拉奧孔”這件具有千年魅力的藝術珍品,每個細節都驚人地顯現了古人對藝術審美力和對自然的深刻理解。“拉奧孔”臉部微小的口型變化引起兩個美學家的關注,并且得出了一致的見解,不能不說明他們所具有的杰出審美能力!“美”是永恒的話題,“美”是伴隨人類永恒的理念。所以黑格爾說“古典藝術是真正的藝術”。歌德說“凡是美的,即是古典的”。因為古典藝術中“內容和完全適合內容的形式到獨立完整的統一,因而形成一種只有的整體,這就是藝術的中心”。甚至還說“古典型藝術是理想的符合本質的表現,是美的高度達到金甌無缺的情況。沒有什么比它更美,將來也不會有”。他還對古典和浪漫進行一個劃分。
古典:純樸的、異教的、英雄的、現實的、必然、職責。
浪漫:傷感的、基督教的、浪漫的、理想的、自由、意愿。
溫克爾曼曾高度贊賞古希臘人的藝術。認為“古希臘人的藝術,它是人類一切藝術的典范”。溫克爾曼還說“對我們而言,成為偉大的唯一道路,而且可能的話,成為無法模仿的道路就是模仿古代……我們必須像跟自己交朋友一樣與希臘人結為知己。”我也多次看到這些藝術精品。每次都是心情激動、流連忘返,甚至熱淚盈眶。
古典主義追求的是什么
古典主義追求的是什么?是數字的精神,和諧的原理、邏輯的思考。也許她約束了你,但又讓你在約束中發展起來。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只有限定的自由才傳遞真正的挑戰和價值。達芬奇早就說過“自由導致死亡”。如同我們居住在地球的人類,渴望飛翔天空,但只能借助太空船來實現,我們無法拔著自己的頭發飛到天上。古典精神追求永恒的生命價值,鄙視粗俗,崇尚精微,迫使每個人都用第三只眼睛,第二個腦袋去看世界,去思考世界,去創造世界。它總是希望把每個人引入一個祥和、寧靜、大愛的境地,追逐一種理想和光明的大美天地。偉大的傳統是豐富的,有無窮生命力的,我們不但要學習和研究,還要繼承和發展。如果一個傳統對個人、民族、國家有用,那么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和愛護。我們對偉大傳統尚缺乏理解,卻急急忙忙到處找尋新的傳統,把偉大傳統棄之一邊,不斷被邊緣化,當今世界一片“庸俗化、金錢化、市場化”,能真正造福人類嗎?在我看來古典主義是萬泉之首,是最大、最多、最深的主脈河流。即使現代派、現代主義有層出不窮的變化和發展都或多或少受到她的影響。
古典主義最懂得和諧對比等等辯證法,激昂—虛靜、壯闊—平穩、高雅—樸實、含蓄—隱喻。始終讓群星繞著太陽,而如果讓太陽逼近群星,那么群星不僅黯然無光了,還要被消滅,恰到好處就是不可動搖的典范。他們都十分尊重科學的藝術方法。世界上最偉大的建筑物、最偉大的音樂、最精美的繪畫、最可讀的文學作品,如果能夠流傳永世,一定由于這幾個因素——高技巧、高難度。看別人之所未看,想別人之所未想,做別人之所未做。只有具備古典精神這種品格的人,才有可能問鼎。他崇尚理性,永遠高舉理性的大旗,拒絕非理性的東西。人之所以區別動物,人是具備理性天賦的。理性才能創造萬物。
其實最純粹的抽象藝術,也是理性占大多數的,因為當他拿筆的時候,也是理性的產物。他為什么不拿刀和棍?他的第一筆色彩,如果選的是紅色,也是理性的產物了,為什么不選黑和白?他的心中“紅色”,可能是某種長久思念的東西,所以他使用了“紅色”。總之有一種“大自然的神力”在冥冥之中,完全控制了他,他也不過是一個被大自然使喚的人罷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抽象”,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抽象畫”了。他早已被這個世界“同化”或者“物化”,從他呱呱墜地的第一聲哭聲到他喝的第一口奶水,都不是抽象的東西。人還能比自然更偉大嗎?
如果一件作品,能把人引向崇高、美妙、愉悅、激昂,那就是成功的,達到與人共享、共樂、共鳴的境地。而那些把人引向低賤、迷茫、惡心、墮落(泛起動物性的感覺),降低或拒絕人的神圣和尊嚴感的作品,只能屬于魔鬼的化身,撒旦的言行或可憐的皇帝新衣了。壞藝術更使人墮入迷茫、失意、混亂,也常常把人引入金錢、名利、政治的泥坑深潭。盧浮宮的作品屬于前者,蓬皮杜中心的東西屬于后者。印象派大師雷諾阿雖然沒有看到蓬皮杜中心建成,但臨死前曾說過一句“盧浮宮還是我們的老師!”這句話頗耐人尋味。
古典主義追求完美,這就決定它是拒絕丑惡、排斥丑惡、堅持審美的。審美愉悅的第一性就是其永恒的核心價值。從古希臘文藝復興、19世紀,“美”越過兩千多年,“唯美”一直是藝術的最高法則,一直是人類公認和欣賞的價值標準,大概沒有什么變化和爭論。雖然有起伏,但是基本是一致權威的、不可動搖的、連貫的。尼采曾否定理性主義的古典內核,追求絕對自由和非理性的“酒神精神”,但是這世界畢竟是被“理性”地統治了幾千年的地方。19世紀以來,人類文化藝術的創作運動,已被導入非理性、無意識的深坑里,成了主導的位置。這就不能不讓人擔心否定“上帝已死”帶來的惡果。到了21世紀的今天,“美”被許多人拋棄,取而代之的是“丑術”和“惡術”。可是我很懷疑,這種大戲還能延續多久?這種“黑暗時期”如果不是一種無知的偏見,就是一種不可告人的商業金錢游戲的秘密。我們又在變本加厲地重演一場“指鹿為馬”和“點石成金”的鬧劇。但我相信歷史總會很快翻過這一頁,我們的后代將驚訝地發現,我們這個時代是“美盲和色盲”的一代。我們折騰了好大一陣子,留下的都是一堆垃圾。不斷被否定,不斷被刷新,結果不斷被拋棄……
價值在哪里
我總覺得,一個民族要是有古典理性精神的追求,一定是不朽的、偉大的、不可戰勝的。因為古典精神同樣需要團隊精誠合作,需要團隊的整體信念。一個人是無法勝任和創造偉大業績的。巴黎的城市建造就是充分體現這種精神的杰作。17世紀正是歐洲最推崇古典主義的時代。所以那個時代幾乎每個歐洲國家都給我們留下了非凡燦爛的文化遺產——文學、建筑、音樂、繪畫,甚至在思想史哲學史方面。論工藝之精良,論審美之高超,論難度之艱深都令人嘆服。法國人用二十八年建造凡爾賽宮,又用數十年時間建造盧浮宮,用兩百年時間建造巴黎歌劇院。是什么力量和精神使他們能萬眾一心,一代又一代、一磚又一磚地修砌這些藝術珍品?實在值得我們深思。許多東西都是各個領域的翹楚和永遠的典范,成為非常難于超越的高峰。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給人類留下了一批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2008年8月,我到西班牙參觀巴塞羅那圣家族教堂。我長久地站在那個奇妙的,目前全世界最大、最高的教堂前,感動的不是它的本身,因為世界美輪美奐的教堂很多(由于未完成它的造型還有點古怪呢),但是安東尼·高迪一生為這個教堂獻身的精神讓我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安東尼·高迪清貧一生,為了教堂的經費還常常親自挨家挨戶募捐款項,他花了六十年的時間。整個教堂已建了一百二十年了,因為“耶穌不著急”,所以現在還在不停修建。我望著高聳入云的柱子,心想這是人造的嗎?我驚嘆那完全融入大自然的設計概念——一棵柏樹、一片棕櫚葉、一只小蜜蜂、一只小蝸牛都是其創造的靈感。有的是直接模仿,把人與物、人與神、物與神徹底融會在一起。在一個風雪交加的日子,安東尼·高迪不幸被電車撞倒,人們并不知道躺在地上的是一個劃時代的建筑學家,衣著簡樸的他被人當成叫花子、流浪漢,被人遺忘了。由于延誤醫治,三天以后他就與世長辭。他的去世引起成千上萬西班牙人的震動,人們這才驚覺一個天才橫溢的藝術家永遠離開了……如今這座圣家族教堂成了巴塞羅那的城市坐標,甚至是西班牙的坐標。他設計的許多建筑物都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定保護的“文化遺產”。望著身旁的無數中國人、日本人、法國人、意大利人組成的絡繹不絕的參觀隊伍,我想安東尼·高迪沒有消失,他和我們在一起。他用自己有限的生命線,塑造了無限的藝術空間,把我們捆綁在一起。他留給西班牙人太多的財富,也留給我們太多的東西……我自然想起達·芬奇、貝多芬等等,達·芬奇窮盡物理、人體、化學、天文、地理;倫勃朗誓死捍衛他的《夜巡》;曹雪芹十年血淚的《紅樓夢》……難道是金錢的力量趨使他們去創造奇跡嗎?每當我看到達·芬奇的手稿就面紅耳赤,每當我聽到貝多芬的曲子就熱血沸騰,他們留給后人的價值應該如何用金錢去計算呢?如果我們真的來計算的話。當今世界,我們不講或少講一些“利益”的人還存在嗎?
如果我們見木不見林,見物不見人,那么我們永遠就不理解古典主義,古典主義的產生一定是由個人人格魅力的產生開始的。西方的強盛如果沒有古典主義的統領不可能實現,這也是他們長期累積的結果。法國總統希拉克曾對中國的青銅器情有獨鐘,許多人都說這是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崇拜。可是如果讓我說,其實是他對中國古人“精微文化”的認同與向往。青銅器在那么早的時間里出現,凝聚著中國人的智慧和才能,濃縮著中國人的科學探索精神。直到現在我們想要復制,都無法解開古人奇妙的冶煉技術,令人束手無策,這就是引起東西方人士濃厚興趣的根本。如同我們極為欣賞古希臘的雕塑,卻無法做出超越他們的作品一樣。世間凡是一切“精美”構成的東西都會引起人們長久地關注。世間凡是一切粗制濫造、不學無術的東西一定不會長久流傳。遺憾中國人后來的“煉丹術”,卻是愚昧的象征,變成別人洋槍大炮的發端。
人和神的交往
也許地球是圓的,人類總是在同一條線上來回走著,總是在懷疑、肯定、叛逆、順從的境地中,永遠重復著自己的話語和道路。只有少數神靈般的圣人才高高站著,指引著一些人。我們幾人能仰望和回首?我們總是像一群綿羊匆匆地啃著地下的草兒,埋首走著自己的路,浪費許多生命和寶貴的財富,糟蹋著可憐的地球。
生命的超越,藝術的升華需要有東西給我們指引,這個東西是要費腦筋才能找到的。人到底比動物高超一些,學會了用腿走路,直立而行,不像動物,四只腳必然踏地,背負青天。人雖然具有思考創造的能力,但還是要兩腳踩大地,頭頂藍天。這就決定他的一切命運和因果關系,或者這就是神秘的宿命論,永遠無法解脫的鏈鎖。
真正的古典主義者可以以自己的一生行為和信念來完成作品,哪怕只有一件。用一生時間去鑄造一件作品(最多幾件作品),多讓人敬畏呀!這不但是藝術的魅力也是人格的魅力,我們還有什么樣的東西能超越這種境界?他們總有崇高的自我犧牲精神,一步步走向完美的殿堂,這些藝術作品常常又是藝術家自己人生的寫照。西班牙的安東尼·高迪,意大利的米開朗基羅,荷蘭的維米爾,倫勃朗,德國的貝多芬,奧地利的莫扎特不都是這樣的人嗎?的確,也許我們每個人都希望名成利就,過上錦衣玉食的日子,不希望在窮困和饑寒中度日,但問題在于你是否心安理得不義之財和“嗟來之食”?是求“道”還是求利祿?
無論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還是黑格爾、康德、馬克思、恩格斯、羅丹、列賓,哪個不在古典主義精神里浸潤而發揚光大呢?英國19世紀的“拉斐爾前派”,高舉15世紀“文藝復興”的大旗,創造了非凡的業績,距離“文藝復興”那個時代已經四百多年了,實在也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情。近代大雕塑家羅丹叫人們精研“古希臘的雕塑”,也為自己留下最偉大的作品,他的“地獄之門”、“吻”、“義民”許多作品成就了近代無法跨越的經典。19世紀的俄羅斯無論在音樂、文學、繪畫領域里,都在世界藝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說到底也離不開古典主義精神的影響和造化。厚積薄發,向偉大的傳統汲取養料,幾乎是所有大師的通途。而那些不敢向大師靠近的人,永遠只能在大師的腳底徘徊,最后被時光和歷史淘汰得無影無蹤。最為奇妙的是,15世紀偉大的“文藝復興”運動,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命運,不單單是歐洲人的命運。給這場運動以啟發和靈感的竟仍然是一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古羅馬人的智慧和文化!人類已經多次在遠古的祖先那里找到改變自己命運的靈丹妙藥,真希望再來一次“文藝復興”,讓我們重新認識人類自身丟失的偉大傳統,我一直很懷疑所謂的現代人是否真正會比古希臘人、古羅馬人更幸福?他們早已擁有矯健的體魄,因為有奧林匹克運動。他們早已擁有一流永恒的藝術品,因為有無數精美絕倫的雕塑品常伴左右。他們也早已擁有耳熟能詳、朗朗上口的文學作品,因為有那些令人神魂顛倒的神話故事。他們無論精神與肉體都已“豐衣足食”,他們還缺什么……
古典精神還有很突出的一點,就是把人,把自己交給“神”,交給最偉大的造物主。他們是一群有堅定信仰的人,就是所謂具備強烈“宗教感”的人。他們多數是一群不為金錢與名利隨便折服的人,對作品有精益求精、一絲不茍,高度的無私奉獻精神,只有這樣才會真正激發人的思維能力,總是在高處攀登,于細密、精微之處見功夫,總是把人引入大境界、大愛、大美。中國人早在《中庸》里就說過“盡精微,致廣大”,徐悲鴻把它作為座右銘,一生推崇古典主義絕對不是偶然的偏愛,這是他深諳東西文化的深切體悟。古典主義總是挑戰人類的極限,拒絕平庸、鄙視庸俗。還有一點,就是他們必須具備偉大的敬畏和謙卑之情,無論站在哪個高峰,都有心懷可仰望的另一個山頂。它常常使我們的歪惡私心被壓抑,被消解,離開了一點“原罪”和“私欲”。接近更加美好的事物,也就接近真理一步,接近美好的事物,也就避開了污穢骯臟的東西,因為有了更純潔的指引,有了更高的約束。他們就是一盞明亮的燈塔,照亮我們這些凡人,我們才會心懷感激之情,愉快地活下去,與周圍的一切共享、共榮、共生、共滅,找尋生命的終極目標,走到底。這就是“神圣的”接近“神性的”古典主義精神。
古典主義——我時常在仰望你!你給我帶來許多祥和與安寧,莊嚴與崇高,希望與力量。
2009年1月完稿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