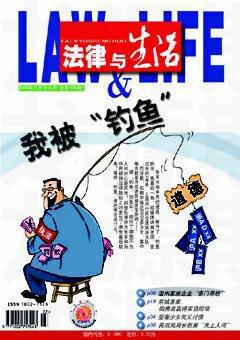別把“釣魚執法”用在人民身上
真正的誘惑偵查是為了打擊已經犯罪的嫌疑人,為了保護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危。
追根溯源,我們所稱的釣魚執法其實就是刑事偵查中的所謂警察陷阱,也稱警察圈套、偵查陷阱、陷阱取證,是指在偵查刑事犯罪案件的過程中,偵查人員為了取得犯罪證據,特意創造某種機會和條件,誘使、暗示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活動,或者為其犯罪活動提供某種便利,從而獲得犯罪證據并緝捕犯罪嫌疑人的偵查手段。
在中國,群眾對釣魚執法,打擊罪犯其實是拍手稱好的,可為什么到了上海這種釣魚執法卻變得人人喊打呢?
合法“釣魚”可反貪
釣魚執法一般是針對已經構成犯罪的嫌疑人,對已經掌握一定證據的犯罪嫌疑人,為了抓獲需要,可以嚴格掌控適用。
對于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來說,由于其具有高度的隱蔽性,證據一般又具有“一對一”的特點,所以檢察機關采用常規的偵查手段往往難以取得充分的證據,經常造成查處上的困難。通過采用提供機會型的誘惑偵查方法獲取賄賂犯罪的證據,進而打擊賄賂犯罪,正是檢察機關對當前犯罪形勢日益復雜,狀況越來越嚴重狀況的積極回應,是目前檢察機關打擊、預防賄賂犯罪的現實需要。
貪污賄賂對社會、對國家的危害遠甚于非法營運。既然上海的交管部門為了整治交通秩序能挖空心思用到刑事偵查手段,那檢察院本身就是搞刑事偵查的,為何不對那些犯罪嫌疑人適用誘惑偵查呢?一些官員在貪污、受賄等腐敗犯罪上,完全是可以被合法“釣魚”的。
最高人民檢察院2005年曾委托成都3名博士起草《職務犯罪證據問題研究》。該報告建議,設立受賄案件誘惑偵查制度,允許檢察官在犯罪嫌疑人主動索賄等情況下與行賄人一道參與“行賄”并取證。不知道是何原因,目前還是沒有明確規定出臺。盡管如此,但我們卻沒有明確禁止的法律規定,只要適用方式得當,我們完全可以用好這一武器,為反貪工作作出重大貢獻。
政府道德的界限
誘惑偵查有三種方式:“顯露式”、“勾引式”、“陷害式”。
第一種方式“顯露式”,就是當事人本身有違法或犯罪的企圖,且已經實施,但是尚未顯露出來,在抓捕中警察應該采用“機會提供型”和“緝捕措施型”的措施。
第二種方式“勾引式”,就是當事人本身沒有任何的違法或犯罪意圖,而執法部門采取行動勾引當事人產生違法、犯罪意圖。適用方式為“行為啟動型”。
第三種方式“陷害式”。刑事偵查上稱為“犯意誘發型”。上海“釣魚執法”采用的就是“陷害式”, 這是一種沒有法律效力的取證方式,理所當然受到大眾的譴責。從法律的角度講,追究犯罪行為必須要考察當事人的主觀故意,“故意”是犯罪的典型構成要素。“陷害式”因為被誘惑對象本來就沒有犯罪的故意,而被警察引誘從事犯罪活動,就是說當事人沒有犯罪意圖,不能追究刑事責任。
任何國家都不能誘使公民產生犯意實施犯罪并隨后對其進行懲罰。國家的職能應當是打擊和抑制犯罪,而不是制造犯罪,這是政府道德的基本界限。另外,我國《刑法》第29條規定:教唆他人犯罪的,是教唆犯罪。在“釣魚執法”中,如果出現教唆行為,警察也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為了群眾的利益
真正的誘惑偵查是為了打擊已經犯罪的嫌疑人,為了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危。而上海的“釣魚執法”是為了部門的私利,是為了打擊人民群眾的經濟利益。這種區別是最根本的。
在刑事案件中,線人、臥底,冒著生命危險來打擊罪犯,他們這種誘惑取證自然是合理合法的。筆者認為,只要是為了社會安寧,為了廣大人民群眾,就算把刑事偵查業務的誘惑取證用到民事行為中,也不見得就完全失效。比如,我們平時的生活中,記者假扮客戶深入制假窩點偷拍,最后把不法商販的罪證拿到電視上播放,這一行為為的是咱們老百姓,所以,他們依然是群眾所津津樂道的英雄。
有些人在各種媒體上對釣魚執法極盡諷刺與嘲笑之能事,把誘惑取證說得是一文不值。君不知,手段是為目的服務的金牌原則,只要是真心實意為百姓好的,不管是釣魚執法,還是偵查誘惑,我們老百姓都歡迎。
(唐紅炬,原系刑事法官,現為廣東同益律師事務所律師)
(摘自《法律與生活》半月刊2009年11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