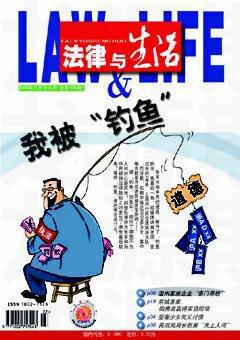記憶之四:公權機關介入“重婚案”
2001年8月,一起發生在北京的,由妻子狀告丈夫重婚并且要求離婚的當代“秦香蓮”案轟動了全國,因為它打破了人們的慣性思維,這起案件被稱作“我國首例公安機關介入調查的重婚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傳統局面的改變?
余長鳳:勇敢的當代“秦香蓮”
案件因余長鳳而起,余長鳳是河南新縣的一個農村婦女。1987年,她與丈夫王某結婚,婚后生有一個兒子叫小龍。
幸福的日子維持了沒幾年,1998年,王某認識了一個叫陳某的發廊小姐,自此,一家人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他們認識之后就在一起同居了,就開始老打我,沒事兒找茬兒就打。” 余長鳳的生活陷入了苦痛。
就在家庭矛盾日益升級的同時,偏偏禍不單行,余長鳳又患上了視網膜色素變性,視力最后只剩下了一絲光感,勞動能力也越來越不行了,而就在這時,王某卻拋下家里的妻兒,帶著第三者陳某到了北京,那年是1999年。
王某離開家的時候,兒子小龍只有10歲,還在上小學四年級,由于王某拒絕給兒子撫養費,小龍很快就輟學了。母子倆只能投靠親戚,今天這家住住,明天那家住住。2001年,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靠從親戚那兒借來的2000塊錢,余長鳳帶著13歲的小龍踏上了千里尋夫的征途。
“我們找得多苦啊,每天早上5點多就起來。有時候吃一頓,有時候吃沒吃飯都不知道,拿著地圖找著找著就不知道往哪兒走了,問了多少路上的行人,走錯了多少冤枉路。”多年后,回憶起那段日子,余長鳳原本以為干涸的眼淚再一次流了出來。
為了找到丈夫的下落,余長鳳在兒子的攙扶下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那幾雙磨破的舊鞋,見證了母子倆的艱辛。最終,在北京市真武廟的一個胡同里,母子倆找到了王某和陳某的住處,并且得知他們已在北京生下了一個女兒,余長鳳決定要將丈夫送上法庭——狀告丈夫重婚和遺棄,然而口說無憑,這讓法院很難立案。
小龍用自己的日記記錄下了那段日子的艱辛。
9月25日,天都涼了,我依然穿著褲頭背心。媽媽帶著我在西單找了半天,想給我買件衣服,但都太貴了沒買。
10月28日,我站在樹下,望著飄落的樹葉,有一種凄涼的感覺。很快就會進入冰天雪地的冬天。到那時不知我們的案子會有什么樣的結果,更不知饑餓還要伴隨著我們多長時間。想到這里,我的眼淚禁不住流了出來。這是我最傷心的一次……
其實,1999年在老家的時候,余長鳳就曾經以重婚狀告過一次王某。但是,鄰居們知道王某有可能因此而判刑坐牢,誰都不愿意出來作證。這場訴訟只能草草收場。 事隔兩年,余長鳳再次起訴王某和陳某,依然遇到了和之前一樣的難題——證據不足。王某和陳某當年在北京開了個小飯館,飯店里的工作人員都清楚二人是以夫妻名義生活,并且私下里也都同情余長鳳,為她鳴不平,但是一說到作證,大家都沉默了,因為王某是他們的老板。
左衍云:促成全國首例公安介入重婚案的法官
一心想要討說法的余長鳳沒有想到,就在她打官司的3個月前,一部涉及所有人的婚姻幸福和家庭美滿的法律——新《婚姻法》剛剛獲得通過。新修訂的《婚姻法》中最大一個亮點,就是提出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公安機關應當依法介入重婚案的調查取證。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受理案件后,在北京、河南兩地都進行了調查,原北京市西城區圖壁廠居委會的治保主任倪文瑞等人紛紛給公安機關出具了有關王某與陳某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證明,二人很快被公安機關以涉嫌重婚罪刑事拘留。
2002年5月23日,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就此案向西城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公訴機關當庭出示了幾十位證人的證言,來證實王某與陳某是以夫妻名義長期穩定居住,包括一份陳某生女兒時的臨產記錄,上面是王某以丈夫身份簽的字。最終,法院經過審理判決王某與陳某犯重婚罪,判處王某有期徒刑一年,判處陳某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
北京市西城區法院立案庭原庭長左衍云如今已經退休,談到當年的情景,她仍舊記憶猶新。
“我永遠都會記得那個孩子當時渴望的眼神,他的眼神讓我決定,一定要幫助他們。”
按照當時的法律規定,重婚案件屬于自訴案件,余長鳳如果想要立案,必須提供被告明確的住址和證據,但以她當時的狀況根本無法做到。而她提供的一個重要的犯罪地點馬上就要拆遷,如果不及時去取證,最起碼的證據就會滅失。
左衍云決定親自去王某和陳某的租住地調取證據,之后,她將案子轉給了公安機關。
左衍云并沒有想到,自己的行為會在日后產生這么大的影響,“我只是覺得既然新《婚姻法》有了這樣的規定,那么就應該按照規定實施。”
巫昌禎:60年的見證
200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45條明確規定:對重婚的,對實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遺棄家庭成員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向人民法院自訴,公安機關應當依法偵查,人民檢察院應當依法提起公訴。這是我國《婚姻法》首次增加了制裁性的條文。
有一位見證了新中國婚姻法60年變遷的學者,推動了這次具有震撼意義的變化,她就是著名婚姻法專家巫昌禎教授。
也許很多人都淡忘了,正因為提出增加這條制裁性的條款,巫昌禎曾被批評為一個保守的老太太。
“好多人提出來這是隱私,法律管不了這么多,有的說得很難聽,我結婚了,不是賣給你了,我可以跟別人上床,跟別人發生關系,性關系不該受限制。”
而與此言論對應的,是國內一些沿海開放城市“包二奶”現象的日益增多,“當時很有名的一個重婚案子,一個包工頭,包了六個‘奶,其中有一個‘奶是舉行婚禮了,其他的都是事實重婚”。
全國婦聯為此在全國展開調查,從農村到城市,調查結果是,同意增加制裁性條款的,將近90%。 “老百姓的意見在那兒擺著呢”,巫昌禎的心放下了。
作為新《婚姻法》實施后我國首例公安機關介入調查的重婚案,因為王某的過錯被認定,余長鳳離婚后,最終獲得了6.2萬元的賠償。
如今,當年陪著媽媽風餐露宿、渴望讀書的小龍也已經21歲,在河南鄭州一所大學就讀。一條看似微不足道的法律條文,改變了余長鳳母子的命運。
如今,巫昌禎教授已經80歲了。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學法律的大學生,她用自己寶貴的60年見證和推動了新中國婚姻法律制度的變遷。
1950年,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出臺,這部法律徹底推翻了“生死婚姻自己不能當家”的封建婚姻制度,提出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并從此深入人心。
之后,這部法律又經歷了1980年和2001年兩次修訂,1980年的《婚姻法》在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又強調了婚姻的質量,強調了在婚姻關系當中每一個個體的權利。而2001年的《婚姻法》又是在1980年《婚姻法》的基礎上對個人權利、對家庭幸福和美的進一步推動。
每一次修改都是時代的縮影,有著明確的時代意義。
而以巫昌禎為代表的一個又一個學者的心血,也都凝結在這樣的法律當中。
如今,2001年的《婚姻法》也已經經歷了8年歲月的考驗,談到這部法律未來的前景,巫昌禎依舊意氣風發:“從2001年開始,國家就在考慮編纂《民法典》了,我是負責婚姻家庭篇和繼承篇的,也就是說,未來婚姻法將回歸《民法》,成為《民法典》的一個組成部分。” 巫昌禎指出,回歸后的《婚姻法》將著重在夫妻財產制度以及結婚制度等方面做進一步的完善,以適應越來越復雜的經濟關系的變化。
(摘自《法律與生活》半月刊2009年11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