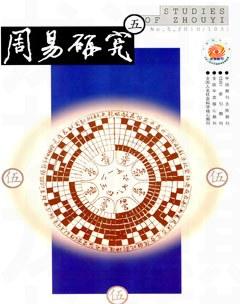周原殘陶簋銘文重讀
姜 勇
中圖分類號:B22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3882(2010)05—0061—02
1979至1980年,陜西省周原考古隊發掘岐山風雛和扶風召陳的西周建筑基址,中有殘陶簋一件,圈足環刻七字(圖一)。陳全方先生釋為“器燮故害成焉王”;高明先生釋作“器口型蔽成象王”。李學勤先生目驗該器,認為銘文中正向之“王”字,似是燒前所刻,乃周王室用器標示,當與其余燒后橫向所刻六字分讀;銘文書寫風格,屬西周中晚期之際。其說可信。
與“王”分讀的六字,李先生釋為“器謂文書成象”,較高、陳之說為勝。對此六字,他最初的感覺是“銘文體例與常見器銘不同,可能與《易》有關”,但“銘文簡古,很難確釋”。后來將“文書成象”之“象”與易象、卦象聯系起來,“猜測這件簋或許和已發現的一些商周陶器一樣,上面刻有表示《易》卦的筮數。也可能有更復雜的圖形,恐觀者不解,故云‘器謂文書成象。”李先生將此六字讀為一句,“器”為全句主詞,“文書成象”作為短語而為全句賓詞,故而有體例簡澀之感,及進一步的猜度。但實際上,此六字當從中間斷讀,作“器謂文,書成象”。如此則三言為句,文義曉暢明白。此銘文當是由其時工藝制作及紋飾、文字之事概括出的一句通語,并非專說此陶簋本身,更與易象、卦象無關,不必作易學材料考慮。顯然。是“可能與《易》有關”的強烈的定向期待。干擾了李先生的釋讀。
然而即便三字為句,“器謂”云云,仍嫌其不合上古表達習慣。問題恐出在銘文第二字“燮”釋“謂”有誤。“燮”,又可隸為“燮”——“叟”。李先生釋為“謂”,參考了《金文編》,說:“字下半從‘又,上半是‘胃的象形字。”他強調“燮”即古胃字,不同意《說文》、王筠《釋例》的以“網”為“胃省”而非獨立之字;“無論如何,陶簋銘文中的這個字可視為從‘胃(或‘胃省)聲。”這些都是可信的。但問題是,從“胃”或“胃省”聲,僅僅解決了該字之讀音,對其所從之“又”,李先生無說。看來,讀“叟”為“謂”,在釋讀程序上存在著跳躍或紕漏,容有重新斟酌的余地。
“叟”從又會意,從胃得聲,不見于《說文》。其義雖不易驟定,但不妨提出兩種理解的可能:(1)其字用為“績”,或即“績”之初文。胃貴之聲通,于省吾釋《小雅·賓之初筵》“式勿徒謂”句有說:“徒謂之謂①如此,陶簋銘上句當讀作“器績文”。燮下所從之又,即會刻繪動作之義。(2)其字有萃、集之義。萃,義為聚集。《易·萃·彖傳》:“萃,聚也。”《易·序卦》:“萃者,聚也。”《易-雜卦》:“萃。聚。”《說文》:“萃,卿鬼。”朱駿聲《通訓定聲》:“萃,按:草聚貌。”《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杜注:“萃,集也。”橐,亦有聚集、叢盛義。《易·泰·初九》:“拔茅茹,以其橐,征吉。”孔疏:“橐,類也。以類相從。”(《易·系辭》:“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大雅·召曼》:“如彼歲旱,莫不潰茂”,鄭箋:“潰貌之潰,當作集。集,茂貌。”胃、萃、集,古韻并屬微部,可互轉通。集,《說文》:“從希,胃省聲。”《易·泰·初九》:“以其桑”,《釋文》:“古文作苘。”按,馬王堆漢墓帛書正作“背”。《字匯補·草部》:“茼,《古文易》:‘拔茅連茹,以其臂。今作苘”。《爾雅·釋木》:“謂襯采薪。”《釋文》:“謂,舍人本作集。”這樣,簋銘上句當讀作“器蘗文”或“器萃文”。
“器績文,書成象”兩句為“互備”修辭,即器、書皆有績文成象的意義或功能。“器繢文”或“器集(萃)文”,以簡潔的語詞表達了三代的器、文關系。古人制器,每于表面施以紋飾、形象之“物”,謂之“文物”。《左傳》所謂:“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又馬王堆漢墓帛書《二三子問》:“夫文之教,采物畢備。”擬象之“物”包羅甚廣,舉凡動、植、自然現象、人、兵器、工具乃至文字,無所不及,是所謂“畢備”。績飾每施以五色,兼用刻鏤。《周禮·考工記》:“畫績之事,雜五色。“設色之工:畫、績、縫、筐、慌。”《淮南子·傲真訓》:“鏤之以剞劇,雜之以青黃,華藻镩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皆道其事。要強調的是,物象紋飾并非只為娛樂美化,而是含有政治、宗教、教育、審美等多層次功能和意義的視覺圖像。此即陶簋“器叟文”之所指。
此外,甲骨卜辭中有一未釋字形,上為立人之形,或似以手掇取器蓋之狀;下為壺形器,器身書有一“文”字(圖二),亦可說是“器受文”的直觀表達。
無論如何;該陶簋銘文與易象并無直接關系,不必作易學材料理會。
另,友人河北工業大學孫偉龍君在審閱拙文上述討論后,賜札指疑如下:“書成象”三字中,“成象”二字無疑,“書”字可疑,理由有三:1)所謂“書”字,下部與書字迥異。2)書字未見從(是)作是形者。3)其字就字形字距來看,顯然應為兩字,參考同銘文字書寫情況,將其釋為一個字,殊為可疑。
筆者回復意見:1)關于“‘書字下部與書字迥異。”今檢出頌簋、頌壺、頌鼎諸書字,實與陶文“書”字全同,惟后者拓片下部點畫不甚清晰。2)所謂“書字未見從是作迪形者。”此無非古文構形中的“增繁”現象,不在話下;“未見”云云,權為默證則可,尚不足以推翻。。如銘中“文”字作“敲”之形,亦未見諸甲金《文編》,然而釋“文”實無妨。且由“故”之字形,更知書刻者多有好繁興趣。3)所謂“其字就字形字距來看,顯然應為兩字,參考同銘文字書寫情況,將其釋為一個字,殊為可疑。”近是而非必。此銘當為工徒所刻,且為原器損毀后戲習之作,可能最大。既出工徒習刻之手,自與鄭重其事者不同。又因前三字布置局促,所遺空間尚多,故于“書”下增一“是”形,以求六字分布勻稱。
以上往來意見,附此以備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