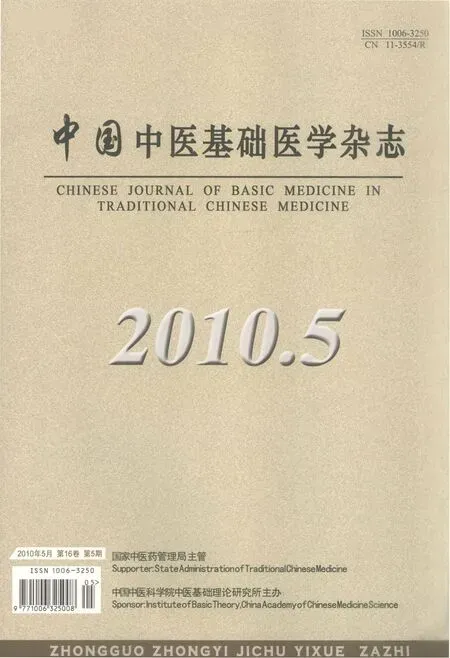古代中醫對乳腺癌的認識
楊秋莉,王學芬,張向農
(1.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臨床基礎醫學研究所,北京 100700;2.山東招遠市中醫院腫瘤科,山東招遠 265400;3.青島市立醫院中醫科,山東青島 266071)
乳腺癌居女性惡性腫瘤的首位,占全身惡性腫瘤的7%~10%。近20年來,我國乳腺癌的發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在大中城市尤為突出。據2007年統計,京滬兩地女性乳腺癌發病率分別達到4.5/萬和5.49/萬,已接近西方乳腺癌高發國家的水平。
古代中醫對乳腺癌已有深入的認識。歷代醫家經過長期的臨床實踐和研究,對乳腺癌的防治積累了寶貴的理論和經驗,從病名、形態、癥狀的描述,到對本病病因病機的闡述,以及對疾病的治療調養等方面均有豐富的文獻記錄。本文通過對古代相關文獻進行梳理,以期為臨床工作者提供更開闊的辨治思路。
1 對乳腺癌癥狀和體征的描述
中醫學對乳腺癌的認識在東晉時代就有記載,至元明清各代又有進一步的發揮。常用病名除了“乳巖”之外,尚有“乳石癰”、“奶巖”、“石榴翻花發”、“石奶”等命名。
古代醫書中對乳巖的癥狀描述有很多相似之處,宋·陳自明《校注婦人良方》[1]中記載:“若初起內結小核,或如鱉棋子,不赤不痛,積之歲月,漸大如巉巖,崩破如熟,或內潰深洞,血水滴瀝。此屬肝脾郁怒,氣血虧損,名曰乳巖。”
元代以后,對乳巖的文獻記載逐漸豐富,對疾病發生、發展的過程及治則方藥也有充分的認識。如明·《外科正宗》[2]中的描寫為:“經絡痞澀,聚結成核;初如豆大,漸如棋子,半年一年……日后腫如堆栗,或如覆碗,色紫氣穢,漸漸潰爛,深者如巖穴,凸者若泛蓮,疼痛達心,出血則臭。”陳實功曾指出預后,“其時五臟俱衰,四大不救,名曰乳巖,凡犯此者,百人必百死。”將乳巖的發病過程描述得非常生動,符合現代對乳腺癌發病規律的研究。
明清時代瘍醫專著豐富,并有更全面的認識,但多數醫書的記載相互參考引用,描述大同小異。
對乳房結節的性質、預后和鑒別,醫家也多有論述,如《外科啟玄》[3]中對乳核、乳疳、乳巖等分別作了描述。清《外科證治秘要》[4]中指出:“乳痰即乳巖之根也。”指出乳巖初起與乳痰、乳廦大略相同,失治誤治漸成絕癥。吳謙在《醫宗金鑒》中[5]對乳勞、乳中結核、乳巖等分別作了詳細的描述,對乳巖的癥狀、轉移及預后的認識較為詳盡準確,難能可貴的是書中指出“堅硬巖形引腋胸……即成敗證藥不靈”,說明認識到乳巖晚期可轉移至胸壁和腋下。
對特殊類型的乳癌也有所記載。《外臺秘要》[6]中有“乳癰大腫堅硬,赤紫色,衣不得近,痛不可忍”的描述,與炎性乳癌或乳癰近似。《證治準繩》[7]中援引《集驗》論曰:“凡婦人女子,乳頭生小淺熱瘡,搔之黃汁出,浸淫為長,百種療不瘥者,動經年月,名為妒乳病。”與現代對乳頭濕疹樣癌又稱Paget氏病的認識相吻合。
雖然男性乳腺癌較為罕見,在乳腺癌中只占1%左右,古代醫家對此已有一定認識。《證治準繩》[8]中提及:“夫男子患乳巖者少矣,其起又甚微渺,而三為盲醫所誤。”《馬培之外科醫案》[9]中曰:“乳巖、乳核,男女皆有之,惟婦人更多。”
建國以后,由于醫學的發展和西方醫學的傳入和普及,對乳腺癌的認識以現代診斷標準為依據,重視病理診斷,醫書記載多與現代醫學同步。
2 對乳腺癌病因病機的認識
中醫學對乳巖病機的認識多從整體出發,根據臟腑經絡學說進行辨證分析。最大的共性是強調情志因素的重要性,認為多數乳巖患者具有情志抑郁或刺激史,致肝氣郁滯、橫逆犯脾、氣與痰結、經絡不通,是乳巖的主要病機之一。
2.1 乳巖發病與臟腑經絡的關系
2.1.1 主責于肝,木郁克脾 眾多醫家認為,本病發病的關鍵是情志不遂,肝郁脾虛。朱震亨[10]強調“若不得于夫,不得于舅姑,憂怒郁悶,朝夕積累,脾氣消阻,肝氣橫逆,遂成隱核”;馮兆張[11]則指出:“此乃七情所傷,肝經血氣枯槁之證。”清·竹林寺僧人[12]也認為,“乳巖屬肝脾二臟郁怒,氣血虧損。”
傅山《青囊秘訣》[13]對病因病機的論述則更為詳盡:“乳巖乃性情每多疑忌……失于調理,忿怒所釀,憂郁所積,濃味釀成,以致厥陰之氣不行,陽明之血騰沸。”
2.1.2 肝虛血燥,腎虛精怯 古有乳巖發病“女損肝胃,男損肝腎”之說。陳實功認為,男子乳巖因“怒火、房欲過度,以此肝虛血燥,腎虛精怯,血脈不得上行,肝經無以榮養”。李梴[14]曰:“肝虛血燥,腎虛精怯,不得上行,痰瘀凝滯,亦能結核。”
2.2 乳巖發病與氣血陰陽的關系
2.2.1 辨屬陰陽,觀點不同 竇漢卿[15]認為,寒客乳絡致惡血不瀉,提出“陰極陽衰”的病因學說,強調早期診治思想,女子“此毒乃陰極陽衰,奈虛陽積而與,血無陽安能散,故此血滲于心經而生此疾也。”清·林珮琴《類治證裁》[16]云:“乳巖結核色白,屬陰,類由凝痰,男婦皆有,惟孀孤為多,一潰難治。”王維德[17]則強調氣火郁結、凝于乳絡,認為“乳巖乃心肝二經,氣火郁結,七情內傷之病……不可照陰疽例治。”
2.2.2 氣血虧虛,久病難愈 傅山對乳巖有“凡三十歲內血氣旺者可治,四十以外氣血衰敗者難治”的論述。他在《青囊秘訣》還指出,由于氣血大虛,使乳癰變成乳巖后久不愈合:“人以為毒深結于乳房也,誰知是氣血大虛乎?”
3 對乳巖治則方藥的記載
由于乳巖是難治之證,醫書所載治療方藥并不豐富。許多醫家注意到早期診斷治療可有一定療效,認為乳巖的形成與七情傷及肝脾關系密切,首先注重情志調養;其次可與疏肝理氣、益氣活血、健脾養血補腎等方劑治療。而在攻補的問題上有不同看法,多數醫家倡導補益,反對攻伐。古代文獻在乳巖治療上的另一特點是外治法應用較普遍。
3.1 清心滌慮為首要,疏氣行血方見效
清·馮兆張云:“惟于始生便須消釋病根,心清神安,然后施之治法。”朱丹溪也強調早期情志治療,并輔“以本草單方青皮湯,間以加減四物湯,行以經絡之劑。”明·趙宜真曰:“若能清心遠慮,薄滋味,戒暴怒,仍服內托活血順氣之藥,庶幾有可生之理也。”龔廷賢[18]提出,“初宜多服疏氣行血之藥,須情思如意則可愈。”
3.2 疏肝健脾初病驗,益氣養血歲月延
清代王旭高、高錦庭、傅山均認為,初起應以逍遙散、歸脾湯、益氣養營湯治之。陳自明指出:“乳巖初起,用益氣養榮湯、加味逍遙、加味歸脾,可以內消;若用行氣破血之劑,則速其亡。”余聽鴻[19]強調,“若治乳從一氣字,無論虛實新久,溫涼攻補,各方之中,挾理氣疏絡之品,使乳絡舒通,氣行則血行”。清·竹林寺僧人曰:“初起……用加味逍遙散、神效栝樓散、加味歸脾湯多服自消。”
《醫宗金鑒》[20]中主張初起宜速服十六味流氣飲,外以木香、生地搗餅,以熱器熨之,且不時以青皮、甘草各一錢為末,煎濃姜湯調服。若潰后久不愈,惟宜培補其氣血,或十全大補湯、八珍湯、歸脾湯選用之。
《女科經綸》[21]引“薛立齋曰:故初起小核結于乳內,肉色如故,五心發熱,肢體倦瘦,月經不調,加味歸脾湯、加味逍遙散、神效栝樓散,多服自消。若遷延日久漸大……用歸脾湯等藥可延歲月。若誤攻伐,則危殆矣。”祁坤認為,乳巖晚期“五大俱衰,百無一救,若自能清心滌慮以靜養.兼服神效栝蔞散、益氣養榮湯,只可茍延歲月而已。”
3.3 陰陽攻補孰是非,醫家經驗細體味
乳巖是陰疽還是火毒,在從陰從陽治療上有不同看法。馬培之曰:“非癰疽可用攻補諸法。奈醫以乳癰為實,乳巖為虛,泥用參、術以滯其氣,氣盛而火愈熾,焉得不潰?”馬氏治療倡導養陰清肝,反對應用補劑或陽和湯。王維德也強調“治宜解郁疏肝,不可照陰疽例治”,認為乳巖“非陰寒結痰,陽和湯斷不可服,服之是速其潰也,潰則百無一生。惟逍遙散最為穩妥,且犀黃丸內有乳香、沒藥、麝香,辛苦溫燥,更當忌投”。
清·林佩琴指出:“若用攻堅解毒,必致潰敗不救。凡潰后,最忌乳沒等藥。”林氏列舉方藥:“初起小核,用生蟹殼爪數十枚,砂鍋內焙,研末酒下,再用歸、陳、枳、貝、翹、姜、白芷、甘草節,煎服數十劑,勿間,可消。若未消,內服益氣養榮湯,外以木香餅熨之。陰虛熱,加味逍遙丸去焦術,加熟地。寒熱抽痛,歸脾湯。元氣削弱,大劑人參煎服可消。”張璐也指出:“氣血虧損,益氣養營湯、加味逍遙散,多服漸散。氣虛必大劑人參。專心久服,其核漸消。”反對攻堅解毒以傷正氣。
清·許克昌對治療則有不同看法,強調“須于初起時用犀黃丸……或用陽和湯加土貝母五錢,煎服數劑,即可消散。如誤服寒劑,誤貼膏藥,定致日漸腫大,內作一抽之痛,已覺遲冶。再著皮色變紫,難以挽回,勉以陽和湯日服,或犀黃丸日服,或二藥早晚兼服,服至自潰而痛,則外用大蟾六只……內服千金托毒散,三日后,接服犀黃丸,十全大補湯,可教十中三、四。”
汪機對醫家動輒應用流氣飲提出質疑:“夫氣血凝滯,多因營衛之氣弱不能運散,豈可復用流氣飲以益其虛。況各經氣血多少不同……人年四十以上,陰血日衰,若于血少經分而病癰腫,或脈癥不足,當以補接為主。”
祁坤《外科大成》中指出,乳巖初起服用六君子湯后仍疼痛惡寒者為氣血虛也,宜用調補氣血,補益肝腎,“宜十全大補湯加柴、梔、丹皮,兼六味地黃丸”。陳士鐸《洞天奧旨》中載化巖湯治療乳癰因房事變成乳巖,藥用人參、白術、黃芪、當歸、忍冬藤、茜根、白芥子、茯苓。方以益氣養血,兼以清熱解毒散結為立意。
顧世澄在《瘍醫大全》廣集各家之方,例如引用錢青掄消乳巖丸,以清熱解毒、化痰軟堅為主,藥用夏枯草、蒲公英、金銀花、漏蘆、山茨菇、川貝母、連翹、金橘葉、白芷、乳沒、栝樓仁、茜草根等,上為細末,煉蜜為丸,每早晚食后送下二三錢,戒氣惱。并載有錢氏乳巖初起方“青皮、甘草各等分共研細末,每服二錢,用人參湯入生姜汁調,細細呷之,一日夜五六次至消乃已,神驗。年壯者不必用人參。”
《青囊秘訣》也載有較豐富的治則和方藥分析,提出“不必治陽明之胃,但治肝經之郁,自然毒消腫解矣”。方用逍遙散加栝樓、半夏、陳皮。或用歸芍二通湯亦效:“歸芍二通治乳巖,當歸一兩芍五錢,柴粉三錢二通一,枳殼山甲楂桃全。”這里二通指木通、通草,柴粉指柴胡和花粉。此外,還載有延仁湯、化巖湯等。
3.4 外治內養雙管下,攻克頑癥有方法
內治加外治療法也為各醫家所喜用。引用比較廣泛的是木香餅外熨。《醫學入門》記載乳巖初起“急用蔥白寸許、生半夏一枚,搗爛,為丸芡實大,以綿裹之,如患左塞右鼻,患右塞左鼻,一宿而消……或急用十六味流氣飲,及單青皮湯兼服”。吳謙強調乳巖初期“速宜外用灸法,內服養血之劑,以免內攻……初宜服神效栝樓散,次宜清肝解郁湯,外貼季芝鯽魚膏。”
《壽世保元》記載:“治婦人乳巖久不愈者,樺皮、油核桃各等分,燒灰存性,枯礬、輕粉2味加些共為末,香油調敷。”龔氏還提及“如成瘡之后則如巖……用五灰膏去其蠹肉,生新肉。”馬培之治療乳癌欲火內動、抽掣作痛外貼清化膏。
祁坤《外科大成》中倡用內外兼治,載方多首。如乳巖初起時“宜艾灸核頂……至十余日,其核自落,用絳珠膏斂口”。又載乳巖方:“玄胡索、薏苡仁各五錢,黃酒二鐘,煎一鐘,空心服,出汗即驗。灸肩禺、足三里穴,各二七壯。”并載致和散:“治乳巖潰爛,膿水不干者。”祁坤推崇神效栝樓散曰:“治乳巖,久服可絕病根……服將愈,加參、芪、芎、術,以培其元。”
從古代文獻中可以看出,我國古代醫家對本病的認識已經相當深刻。反思現代乳腺癌治療,手術、放化療及內分泌治療應用廣泛,雖然治愈率有所提高,但治療過程中病人經受的肉體創傷和精神打擊以及后續的毒副反應是不言而喻的。文獻中記載的患者自然病程少則3、5年,多則14年,試想如能在早期采用中藥治療或許可減少痛苦。當然文獻所載方藥的療效還有待驗證,當代環境、生活方式等諸多因素對人體的影響需加以考慮。從現代醫學的角度出發,本病早期診斷仍是關鍵,手術、化療、放療相結合是較為常規的正確治療方法,結合中醫藥治療對減輕放化療毒副作用、增強免疫、提高生活質量和減少復發轉移會有一定的療效。目前,我國約有200萬乳腺癌患者,每年有20萬女性患病,其中至少有4萬人死亡,乳腺癌的防治工作任重而道遠,希望中醫藥治療能對本病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1]宋·陳自明.校注婦人良方.注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10:450.
[2]明·陳實功.外科正宗.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5:160.
[3]明·申斗垣.外科啟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8:37.
[4]清·王旭高.外科證治秘要.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1.12:45-46.
[5]清·吳謙.醫宗金鑒.吉林: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8:632.
[6]唐·王燾.外臺秘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9:944.
[7]明·王肯堂.證治準繩·女科.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2:893.
[8]明·王肯堂.證治準繩·瘍科.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57.12:213.
[9]清·馬培之.馬培之外科醫案.北京:中醫書局,1955.6:34.
[18]清·高秉鈞撰.瘍科心得集.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9.68.
[10]元·朱震亨.丹溪治法心要.濟南: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12:166.
[11]清·馮兆張.馮氏錦囊秘錄(卷十九).上海千頃堂石印本.
[12]清·竹林寺僧人.竹林寺女科.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3.2:241.
[13]清·傅山.青囊秘訣.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10:23.
[14]明·李梴.醫學入門.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12:474.
[15]宋·竇漢卿.瘡瘍經驗全書(卷三.影印本).續修四庫全書·1012·子部·醫家類.上海古籍出版社,505.
[16]清·林珮琴.類治證裁.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7.2:565.
[17]清·王維德.外科證治全生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10:13.
[18]明·龔廷賢.壽世保元.吉林: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8:213-214.
[19]清·余聽鴻.外科醫案匯編.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63.3:67.
[20]清·吳謙.醫宗金鑒(上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1:1244.
[21]清·蕭塤.女科經綸.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8: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