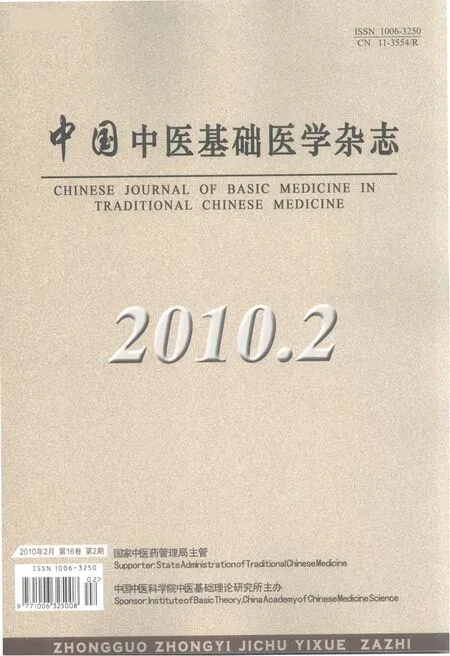張節《傷燥論》研究
萬四妹,戴 慎
(1.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蘇,南京 210046;2.南京中醫藥大學 基礎醫學院,江蘇,南京 210000)
張節,字心在,號夢畹,清·安徽歙縣人,著《張氏醫參七種》[1],即《醫學一得》、《持脈大法》、《本草分經》、《瘟疫論》、《痘源論》、《傷燥論》、《附經》,現存清宣統元年己酉(1909年)張氏家刻本和抄本。而《傷燥論》系張節以《內經》五運六氣理論為指導,闡述燥癥的病原、病證、病脈、病忌、病辨和雜論燥氣之精詳,是中醫文獻中少有的一部闡述燥氣為病的專著,其中有不少獨特見解,給人以啟發。
1 成書背景
自《傷寒論》問世后,廣大醫藥學家都研究和運用。隨著中醫學的發展,外感熱性病也積累了大量臨床經驗。有沿用《傷寒論》的經驗,也有新的法與方的經驗,從而出現了側重經方運用和側重時方運用的兩種情況。明末至清代中期是溫病學派的形成時期,也是傷寒學說與溫病學說論爭最激烈的時代。爭論的主要問題有《傷寒論》是否包括溫熱病,傷寒方能否治溫病及外感熱性病的病因等。
喻昌《醫學法律·秋燥論》初刊后,“秋傷于燥”逐漸被醫學界所公認,并成為外感溫熱的范疇。但張節認為,“燥氣為病,古人未之詳言”,“司天在泉,主客之氣,皆有燥金,平則為利,亢則為害,與風寒暑濕熱原無殊。古人以風熱目之,混二氣為一氣……即有別燥病為一門者,又多言內傷而不及外感”,且“近人于秋三月病初起……醫者從太陽表散不效,作暑治利小水亦不效,作癉虐治亦不效。遷延日久,近數十日遠百日,或死或愈,莫知其由”。加之喻昌提出“仲景書詳于傷寒,略于治溫”。而張節堅持認為,傷寒法能治秋燥等外感溫熱病,故在《傷燥論·自序》指出:“喻西昌嘗言燥病,而不合時行。心在讀經有會通,以傷寒法開治燥一門,實有心悟。”
2 學術淵源
張節在《傷燥論·病原》、《傷燥論·病癥》等多次節錄《內經》運氣七篇中有關燥氣的經文。如《內經·天元紀大論》“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內經·氣交變大論》“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歲木不及,燥氣乃行”;《內經·六元政紀大論》“陽明司天,燥氣下臨,肝氣上逆”;《內經·至真要大論》“陽明司天,其化以燥”。強調燥邪的形成和特點與歲運及時令密切相關,并依據五運六氣理論,反復強調人與天地相應的指導思想,突出中醫學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從天之六氣的變化和人體臟腑氣化功能動態平衡的角度認識人體的生理病理現象,指出天地萬物之間是一個不斷運動和變化著的整體。人體五臟之間也是在不斷運動和變化著,人與天地之間也是在不斷運動和變化的,所以一切都必須從整體恒動的觀點出發,分析人體的健康和疾病。
3 學術內容
3.1 易感人群和發病季節
鑒于歷代醫家對燥癥認識不一,如外燥內燥之分。張節對自己《傷燥論》的研究對象做了明確界定,只論外感六淫之燥導致的燥癥,對于“人有憂愁幽思勞役過甚,或溺酒色,致金水二臟無以相生,水涸不能潤土,胃火熏肺,咳嗽發熱,聲嘶色脫,漸漸肺萎,以成損癥著,此乃內傷為病,非六氣之應也,不以傷燥論”,且“嘈雜、膈噎、熱中、消中諸癥亦如之”,不作為《傷燥論》的研究范疇。并仿照《傷寒論》書名內涵,取名為“傷燥”,以區別于五志之火耗傷陰液的內燥。對于素體內傷血燥之人易傷外燥,張節總結為內燥的易感人群:“陽盛陰虛之人,多病傷燥……渾身作癢亦是血燥,手腳心不甚有汗者亦是血燥,鼻干唇揭亦是血燥,大便常硬亦是血燥,指爪枯而不澤亦是血燥,如此類人易病傷燥。”
張節反復推敲《內經》五運六氣理論的整體恒動思想,認為燥氣雖作為秋之主氣,但天之六氣有常有變,四時皆有不正之氣,有變是永恒存在的,又有“時行”等因素,故得出“思燥氣雖病于秋,而《素問》所言有不專病于秋者”,“不獨秋時,然方秋居多”,“天氣清肅,久晴而地干,燥病將發之候也。”
3.2 燥邪傳入途徑的認識
張節依據《易》同氣相求理論和《內經·天元紀大論》“陽明之上,燥氣主之”等經文,對“燥氣為病……醫者多從太陽表散不效”作出解釋。認為人體三陰三陽之氣,與在天之風寒暑濕燥火六氣一一相應。一旦感受邪氣,氣氣相感,便入于相應之經。如寒邪作用于太陽經,燥邪作用于陽明經。“《易》曰同氣相求。六淫之燥氣,陽明受之,其病不從太陽入,故表散無功”。“其(燥)病始在陽明經,既而入府,繼病肝膽,終病腎或兼病肺,或結諸腸胃”。
3.3 明示辨燥要領。
對于燥邪屬性問題,向有爭議。張節反對以涼燥溫燥來區分,認為“燥傷氣則寒,傷血則熱”,且“火熱燥三氣相似而不同,熱如滾湯,尚有水也。燥如干土,并無水也。火雖烈焰沸騰,其氣猶能蒸而為水,故治燥必保全津液”,客觀地揭示了燥邪為干的特點。
燥邪病脈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初起浮大而短,既而兼長,既而里實大而長或兼數,既而氣血皆傷細濇而短。
對燥邪的發病表現,張節依據五運六氣理論,綜合司天在泉的差異及歲金太過、歲木不及等因素,有六氣自病陽明經病、胃受病、腎受病、肝膽受病等多臟腑受病的多種臨床表現。但“傷燥不必悉見如上病,亦不必專是如上病”。燥癥又具“燥病偏病者多,全身病者少”的特點,“喻嘉言以為秋傷于燥,冬生咳嗽。亦有傷燥而即咳嗽者,不特歷時始發,未之或詳也”。“燥初起何以微微發熱?土本惡濕而喜燥,胃又為水谷之海,多氣多血,故輕傷不甚覺其苦。至天人交感,燥金之氣自動,則身熱不可耐亦。”鑒于燥癥與暑、虐、瘟疫、風熱、濕、癉虐都有發熱表現,暑“初起即體若燔炭而自汗”,瘟疫“憎寒壯熱以后但熱而不憎寒”,風熱“惡寒惡風,頭痛身痛而大熱”,濕“首如裹而身重以發熱”,癉虐“專熱而后作有時”,但仔細辨證還是能分清的。傷燥發熱“惟微微發熱,從肌肉熱起,初若不甚重,既而渾身大熱,烙受不能耐,津液干枯,晝夜皆熱。”
3.4 傷燥的治則、選方用藥
“寒勝燥,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 ”,故以 “燥者濡之”、“燥者潤之”、“治燥必保全津液”為總體治療原則,治療方法采用“始則直表陽明經,不治太陽少陽,病輕者即愈,重者清之下之而亦愈,用地黃湯收功”。用藥經驗上主張側重經方的運用,推舉加味升麻葛根湯用于“病初起,專治陽明微微發熱”;加味白虎湯用于“肌肉烙不能耐,津液干枯,晝夜皆熱或日哺潮熱”;三一承氣湯用于“病入胃府不定,定結大腸,火來就燥,大熱不退,大渴引飲……諸癥皆至危候”;六味地黃湯用于“津液久傷,纏綿不愈”;補中益氣湯用于“遷延不已,燥氣累久自退,精神倦怠,時熱時不熱……中氣大傷,非陽生不能陰長也”。雖“前五方予所常用有驗者,然病不盡似古方,有可參用”,又推選了小柴胡湯、生脈飲、四物湯、活血潤燥生津飲、通幽湯、當歸潤腸湯、竹葉石膏方、犀角地黃湯八方。這些方劑,雖不專為治燥所設,然均有直接增液或間接保津的功效。張氏指出:“火熱燥三氣相似而不同,熱如滾湯,尚有水也。燥如干土,無如水也。水雖烈沸騰,其氣猶能蒸而為水,故治燥必保全津液。”還特別提示,“初起忌發太陽汗利小便,忌引吐,忌和解少陽,始終不可用燥藥熱藥。”
選藥方面,張氏以《素問》六淫特點及藥物性味相關的理論,出“燥者潤之”“燥者濡之”“寒勝燥”“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以苦下之,或佐以甘辛,或佐以酸平;治以辛寒,佐以苦甘。總之,須選濡潤辛苦性寒的藥物。
4 學術評議
4.1 何廉臣《全國名醫驗案類編》曰:“六氣之中,惟燥氣難明,蓋燥有涼燥、溫燥、上燥、下燥之分”,難以明辨,故傳世的論燥文獻和專著較少。張節身處寒溫論爭最激烈和“秋傷于燥”學說漸被學界接受的時代,堅持深研《易》、《內經》、《傷寒論》等經典,依據天人相應的整體恒動觀創“傷燥論”,補充了喻昌依據《內經》六氣配四時理論而提的“秋燥論”的不足,豐富了中醫學對外感燥癥的論述。
4.2 燥邪作為六淫之一既是客觀存在的,就不應局限于季節發病來認識,僅言“秋燥”是不夠的。張氏《傷燥論》指出,陰虛陽盛之人,或遇某年、某季、某月、某時燥氣流行,多患燥病。呼吁醫者當重視天時、地域、人體質等各異,不能僅憑一年季節變化僵死對待,強調中醫學整體恒動和辨證論治,既發展了學術,又為臨床辨治燥病拓展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