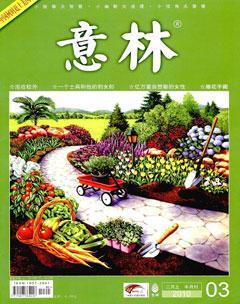泡在校外
蔣方舟
我認(rèn)識(shí)的一個(gè)頗有點(diǎn)搖滾精神的小學(xué)妹給我寫信,用一種大抒情的亢奮語氣,向我描述她的羨慕之情:“學(xué)校外難以計(jì)數(shù)的打口碟唱片鋪是否茂盛如富有營養(yǎng)的野草?南門外的搖滾酒吧是否還嘶吼著最后的龐克吶喊?如果我來北京,能否在咖啡館放映歐洲紀(jì)錄片的夜晚與你相遇?”
收到這封信,我窘迫羞愧得無以復(fù)加,硬著頭皮回信道:“你說的這些我也不知道耶!不過我知道學(xué)校外面有個(gè)“我愛炸醬面”異常好吃,你來了我可以請你吃一大盆。”因此,又打上了一個(gè)諂媚的笑臉符號(hào),它仍然掩飾不了我校外生活的貧瘠與干癟。
平心而論,我在班里同學(xué)中算是在外游蕩積累里程數(shù)比較多的人。就算是只買一袋酸奶,我也會(huì)哼著小曲騎車到校外去買。在我的自我描述里,這被形容成“熱愛擺脫象牙塔的束縛,感受社會(huì)的千姿百態(tài)”。事實(shí)上,我自知這只是出于我貨比三家的邏輯。
我也想泡在校外,在宿舍之外為自己找一個(gè)可以歸屬的家。
寒冬的夜晚,我和同學(xué)吃完好大一盆“我愛炸醬面”,我突然又想到文章開頭小學(xué)妹給我寫的那封信,肚中飽脹,心中凄涼———去他的,我也可以搖可以滾。我對我的同學(xué)忐忑又堅(jiān)毅地說:“走!我們?nèi)ヅ輷u滾酒吧。”
步行幾百米,就有一家外國人開的搖滾音樂酒吧,會(huì)請世界各地的獨(dú)立音樂人來演唱,號(hào)稱“地下?lián)u滾”的搖籃。晚上六點(diǎn)的酒吧除了兩個(gè)酒保外空無一人,滿屋的大沙發(fā)有種殘破的紅,陳舊的木質(zhì)地板走起來嘎嘎作響,在寂靜的房子里聽得格外清楚。我們兩個(gè)小心翼翼地一邊走一邊偷瞄擦酒杯的服務(wù)生,猜測他有沒有發(fā)現(xiàn)我們,像極了《阿凡提》動(dòng)畫片里的笨小偷。
我們窩在二樓最不起眼的角落,看著墻上龐克嚎叫的夸張涂鴉,無話可說,只是討論了一下剛吃的“我愛炸醬面”。一個(gè)小時(shí)之后,仍是一個(gè)客人都沒有,但是樓下響起了巨大的鼓聲和電吉他聲,聲音如此之大而又難聽,讓我只有張著嘴大口呼吸才能緩解耳膜的壓力。我努力克制捂住耳朵的欲望,內(nèi)心贊嘆道:“這才是搖滾啊!”我還隨著樂鼓沒有節(jié)奏的節(jié)奏,上下劇烈地?cái)[動(dòng)著頭,如同猛鬼上身,還在忙亂的搖擺中對同學(xué)吼道:“你也來!你也來!”
馬上,音樂戛然而止,傳來一個(gè)中年男子的聲音:“音響修好了,一百二。”這個(gè)樂器修理工就是我以為的搖滾之神。我的同學(xué)被我蒙受的尷尬激怒了,憤然說:“走走走,我們快出去。”我哀求道:“至少喝杯雞尾酒再走吧。”天知道雞尾酒是什么東西,我們在一樓的吧臺(tái)坐了半個(gè)小時(shí),兩個(gè)頭埋在一起研究那張黑色的酒單,像兩個(gè)刻苦的差生窩在一起考試作弊。酒保大概也覺得我們十分可笑,始終站在吧臺(tái)遙遠(yuǎn)的另一端,自始至終沒有抬眼看酒吧里唯一來的兩個(gè)客人。
故事的結(jié)局,是我們兩個(gè)自己把自己掃地出門,臨走之前,我憤恨又沮喪地在吧臺(tái)抓了一大把花生米。冬天的北京天黑得很早,那天的風(fēng)格外大,走過的商店、餐廳、咖啡館莫不用力地關(guān)堵住門,掛上“暫停營業(yè)”的招牌。我明知道關(guān)店是因?yàn)榇箫L(fēng),但總有種委屈,覺得校園以外偌大的世界,竟沒有一個(gè)親切而喧雜的地方容得下我,讓我能消磨一天半時(shí)。
理查德?桑內(nèi)特寫過一本書叫做《公共人的衰落》,里面有一章專門是講“公共空間之死”,說現(xiàn)代社會(huì)大部分的公共空間的用途只剩下“通過”而已,許多可以交流和消磨的場所都被拆毀。這樣看,許多人緬懷母校外的“墮落街”被拆,如同被摧毀了第二故鄉(xiāng),也的確可悲可嘆。
直至今日,當(dāng)初和我一起從搖滾酒吧落荒而逃的同學(xué),已經(jīng)能輕松自然地逗留在酒吧,這多少給我樹立了一點(diǎn)信心。也許將來,我也可以在校外找到一個(gè)可以泡去時(shí)間的地方。首先,我得更新一下心里的那本“辭源”———校外的那條街不叫“墮落”,它叫“生活”。
(水云間摘自《女友?校園》
2010年第1期圖/韓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