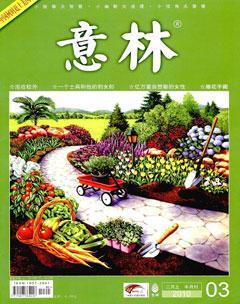武將教出弱書生
王艷鵬
子承父業,往往不能發揚光大。否定之后,常常別有洞天。而在那否定之中,隱著一脈相承。
如果是通過昆曲《牡丹亭》知道了白先勇,你怎么也不會想到他是白崇禧的兒子。白崇禧是戰場上的名將,在軍事指揮上有“小諸葛”之稱;白先勇則是一介書生,文文弱弱,在文學上,人們拿他和張愛玲比,可見其風格與白崇禧有多大的差異。
同唱《滿江紅》
白崇禧共有10個孩子,第8個孩子白先勇出生的時候,他已經四十多歲。當時正是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所以在白先勇幼年,父子倆的相處機會極少。
雖然飽讀“四書五經”,接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白崇禧打起仗來卻不受那套規矩的制約。白崇禧一生和蔣介石對著干,即使在一致抗戰的時候,他在蔣介石面前也犯顏直諫。自家是回民,回民的叛逆因子在他們的血液里流淌。另外,廣西民風彪悍,在戰爭中,桂系軍隊是最難啃的硬骨頭。這種民風在白崇禧父子的身上留下了痕跡。
雖說叛逆,但白崇禧受儒家的家國思想影響很深。抗戰期間,白崇禧從戰場回到家里,帶著孩子們去看他們的奶奶。在路上,白崇禧就教孩子們唱歌,是哪首歌?其實白崇禧只會唱一首歌,就是岳飛的《滿江紅》。“怒發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小孩子們唱得高興,他們哪里懂得詞中之意。
白先勇后來說:“那首歌是應著我父親的心境,面對外族入侵,戰火連天,抗日艱難。教自己的孩子唱《滿江紅》,那是一種悲壯啊。”他和父親一樣有深深的家國之思,盡管已入美國籍,但他從來沒說過自己“既是美國人也是中國人”,而總是說“我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我住在美國,但我的想法和關切都是中國的”。他訂有中國報紙,時刻關注國內的情況,對于“文革”,他痛心疾首;對于改革,他拍手稱快;下崗問題出現后,他憂心忡忡:“中國可不能亂呀!”
解放戰爭時,南京被攻陷,蔣介石迫退臺灣。白崇禧有機會到國外,甚至在香港居住也可能。當時馬步芳就到了沙特阿拉伯,白崇禧和他關系很好,又是穆斯林,到沙特阿拉伯非常便利。但他還是聽了蔣介石的話,去到了臺灣,白先勇在寫《白崇禧將軍傳》時,說父親選擇到臺灣是“要向歷史交代”。
言出必行
身為武將,白崇禧對中國古典文學卻情有獨鐘。在進入保定軍校前,白崇禧就讀了很多古書,像《史記》《漢書》都能整段整段地背誦。他不僅熟讀《孫子兵法》,而且通讀世界戰役戰史、拿破侖侵俄史、俾斯麥的戰爭策略等。
從小,白崇禧讀書就很用功,再難背的古文,晚上寧可不睡,都要背下來。在學校,先生布置的古文,背不下來就要受處罰,但白崇禧從來都沒有受到過先生的責罰。對自己的孩子,白崇禧也這樣嚴格要求,一切都以考試成績說話,誰的考試成績好,誰在家里地位就高。打仗的間隙,白崇禧打電話回家,寒暄過后就要問孩子們的成績。白先勇的成績最好,每次都考第一名,很得父親器重。白先勇學習也非常刻苦,用他的話說是“拼命念書”,這和白崇禧小時候很像。
吃飯前,白崇禧會搞突然襲擊,讓孩子背“九九乘法表”,因為這事,白先勇的大姐幾十歲了還做噩夢。但是白崇禧尊重兒女,白先勇非常感謝父親的尊重,覺得這對中國父母來說“非常難得”。
白先勇講過這樣一個故事,父親讓他去寄一封信,但是他忘得一干二凈,兩天后,父親看到信還在桌子上,有些不悅,但也只說了一句“與人謀而不忠,不行”。這是白崇禧責備白先勇最重的一次,白先勇說:“我很感念他培養了我一份很強的自尊自信。”
父子倆有很多的不同,白先勇沉迷昆曲,白崇禧在廣西也只是偶爾看看桂戲。白崇禧希望白先勇學工程,所以白先勇考上了臺灣成功大學水利專業。但讀了一年后,白先勇發現自己的志向不在工程,而是文學,于是退了學,去報考了臺大外文系。這是項地下工作,考中后,他才告訴父親。白崇禧雖然很有些失望,但也沒有太責備兒子。
“我父親有個優點,雖然他很強勢,但是講理,以理說服他就可以。”白先勇說。白崇禧理解兒子的選擇。后來,白先勇和朋友一起創辦了《現代文學》雜志,白崇禧還在經濟上給他以支持。“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理解父親,也發現他對我的影響越來越大。他認真而不輕言放棄的做事態度,言出必行,軍令如山。我這點很像他。”白崇禧愛才,重視教育,曾把林海峰送到日本學圍棋,讓林海峰最終成為圍棋名將。白先勇惜才,在美國教了29年書,極愛自己的學生。
花語即心語,父子倆都愛養花弄草,白崇禧喜蘭花,白先勇愛茶花。蘭花高潔,“惠質不堪逐流水,露華何妨潤愁腸”。茶花謙遜,“唯有山茶偏耐久,綠叢又放數枝紅”。
白崇禧的墓碑上,寫著4個大字:仰不愧天。頂天立地的鐵漢形象,令人肅然起敬。白先勇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述說人世間的纏綿,“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也正是他對父親的深深眷戀。
(丁香摘自《樂齡時尚》
2009年第9期圖/孫紅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