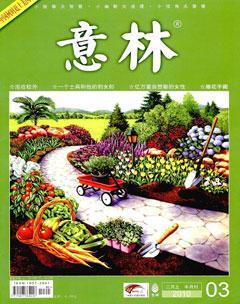麻木的草食性集體主義
王溢嘉
北京奧運的開幕式,讓布魯克斯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說:“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像一個人一樣擊鼓,一樣起舞,按照精確的編隊疾走而不會絆倒或沖撞。……這是目前的集體主義———和諧社會的高科技版本,而背景是中國奇跡般的成長。”
中國的崛起讓很多外國人感到好奇,而紛紛探討其原因,布魯克斯想說的是在這一輪競賽中,中國的集體主義已勝過西方的個人主義,而且還是一個頗具吸引力的和諧理想模式。奧運開幕式的“萬眾一心”只是表演,集體主義對中國崛起的貢獻,恐怕也是一相情愿。說到中國的集體主義,我想到的不是大伙在公園打拳、圍桌共食、集體貪污這類事情,而是魯迅在《吶喊》自序里所描述的一個畫面:他就讀仙臺醫專時,在一部描述日俄戰爭的紀錄片里看到一個被指為俄國間諜的中國人,被日本人斬首示眾,而一大群中國人就在旁默默圍觀。套用布魯克斯的話:“成百上千的中國人像一個人一樣麻木、一樣呆看,執刑的日本人雖只寥寥數人,但完全不必擔心會受到沖撞或反抗。”
中國集體主義的基調是草食性的。在自然界,像羊、斑馬、麋鹿等草食性動物,都喜歡過群體生活,一起覓食、遷徙;但在同類受到獅、豹或狼群的攻擊時,他們卻也都“萬眾一心”、事不關己地站在一旁呆看。這種集體的冷漠和奴性,正是當年讓魯迅“深感恥辱”的。時過境遷,中國崛起了,但草食性集體主義的根性依然健在,為什么到現在還有那么多人搭車公然不排隊?為什么有人會在大庭廣眾下活活被打死?個人的私欲與暴力固然是原因,但大多數人只是站在一旁袖手“呆看”,這種集體的“無為”、麻木,無異于默許、縱容,而使得違法亂紀者更加猖狂。
西方社會雖有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但搭車購物人人排隊,小區住戶也沒有人會任意在住宅窗前加個鐵欄、屋后搭個架子,因為他們普遍認為身為公民就必須具備公德,遵守集體生活的規范;如果有人違反規范,就會立刻受到譴責,并以集體的力量嚴加制裁。這也是一種集體主義,但比較像鬣狗、狼等肉食性動物的模式:當大家必須集體營生時,那么在分工和食物分配等方面就必須嚴格遵守規范,違者決不寬貸。這種肉食性集體主義是積極的,使得他們在自然界能和獅、虎等大型貓科動物分庭抗禮,甚至更具生存優勢。
人類社會沒有完全的個人主義或集體主義,也少有純粹的草食性或肉食性,差別只是色彩濃淡。我的一個觀察是,中國社會過去偏向草食性集體主義,但現在想吃肉的人愈多,肉食性個人主義正急速冒泡,違法、脫序的亂象相當嚴重。這使我想起馬丁·路德·金的話:“歷史將會記錄在這個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喧鬧,而是好人的過度沉默。”為什么有人能如此張牙舞爪?因為多數人對此依然采取集體無為、呆看、麻木、默許、縱容的態度。如果你也想吃肉,如果想讓大家都有肉吃,那大家就必須遵守集體規范,特別是對破壞規范者必須有更多的公民出面譴責、更強的公權力嚴加制裁,這才是中國目前最需要的集體主義。
(吳順國摘自《南方周末》
2009年12月24日圖/宋德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