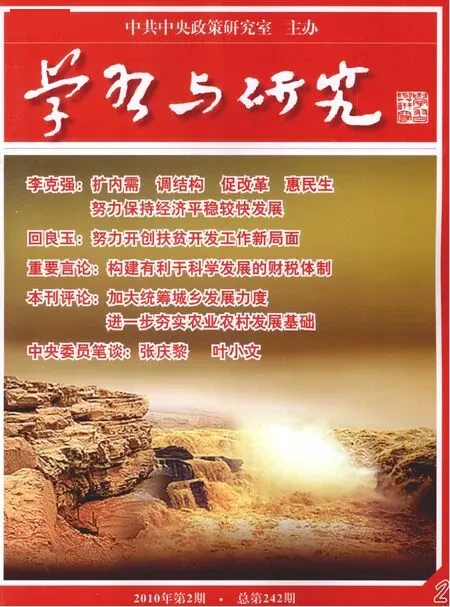生產力發展視角下的五四運動研究
黃亞玲
(華東師范大學,上海 200241)
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和進步的歷史,生產力發展是貫穿人類社會歷史的主線。“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須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1]彭明曾精辟地指出,作為歷史科學的整體來看,經濟是歷史的骨骼,政治是歷史的血肉,文化思想是歷史的靈魂。[2]因此,當我們在分析任何一種政治現象或思想文化運動時,應當首先把握其“骨骼”,即這一時代的生產力發展狀況。研究五四運動也應當如此。
五四運動包含著兩個內容: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既是指1919年5月4日的學生愛國運動,又是指1915-1920年這一時期的新文化思想運動。它既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愛國主義運動,又是一場意義深遠的思想啟蒙運動。本文正是從五四運動所包含兩個內容進行研究,一方面從生產力發展的視角來探討五四愛國運動發生、發展的起源,另一方面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對社會生產力發展所起的作用。
一、生產力發展與五四愛國運動
對于五四愛國運動來說,近代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現狀是這場運動爆發的原因、背景之一。當時生產力發展極其落后,激起了以愛國學生為主體的廣大人民要求推翻舊軍閥統治的愿望;生產力發展也促使中國的工人階級迅速成長強大起來,足以以嶄新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成為五四愛國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生產力發展也使民族資本發展壯大,使民族資產階級有相當的力量與北洋軍閥政府對抗,成為五四愛國運動的推動力量之一。與此同時,五四愛國運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近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1.五四愛國運動前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
五四運動前的中國,正處于北洋軍閥統治的黑暗時期,陷入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和軍閥混戰的局面。在不同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下,北洋軍閥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據一方,為了鞏固和擴大地盤,并爭奪對北京政府的控制權,各派軍閥之間進行著頻繁的爭奪以至戰爭,使國家陷于長期的分裂和動亂中,嚴重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
與此同時,從袁世凱到段祺瑞的歷屆北京政府,都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操縱。北京政府的財政,主要依賴外國政府的借款來維持。截止1919年5月,各派軍閥公開或秘密舉借外債180多次,數額達銀元8億元以上。為了借到外債,他們將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權益,包括鐵路修筑權、礦山開采權、銀行投資權、內河船運權,以及關稅、鹽稅、煙酒茶稅、米捐等大宗財政收入,都作為借款的抵押品。帝國主義國家則通過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的政治性貸款,操縱中國的內政和外交。[3]總之,這一時期,北洋政府經濟上的橫征暴斂,政治上的黑暗統治,加上軍閥戰爭造成的破壞,都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給整個社會帶來無窮的災難,也使廣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以愛國學生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要求改變現狀的愿望越來越強烈,這正是五四愛國運動在經濟層面的爆發根源。
2.五四愛國運動前后的工人階級
中國無產階級產生在19世紀中葉的的外國在華企業中,隨后又出現在19世紀60年代清朝官辦的企業和70年代興起的民族資本企業中。甲午戰前中國工人階級就已產生,大約有10萬產業工人。甲午戰后,隨著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和帝國主義在中國企業的進一步擴張,工人階級隊伍也迅速成長壯大。1913年,近代產業工人達60-70萬,五四運動前更增到200萬人左右。城市手工業工人和店員工人還有一個相當大的數目,約計1,000萬左右。[4]掌握著先進生產方式的無產階級成為一支新興的產業大軍。
五四運動期間,日益成為近代一支重要社會力量的工人階級以巨大的聲勢參加了反帝愛國斗爭。雖然工人的罷工是自發的,但工人階級以自己特有的組織性和斗爭的堅定性,在運動中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
五四運動后,工人階級更加壯大,不僅表現在人數的增加上,而且表現在力量的集中上。從地區看,由于中國工業發展的殖民地性,近代工業多集中于沿海少數大城市。上海、天津、武漢、青島、廣州五個城市工人就占全國工人總數的70%,其中,上海一地就占25%。1924年,上海計有產業工人29萬,相當于當時居民人口160萬人的六分之一。1927年,全國有近代紡織工人23萬,上海就集中了9萬,占37%。從部門看,工人集中最多的是紡織、礦山、鐵路、航運等業。1920年日資的本溪煤礦有48,000人,撫順煤礦40,000人,開灤煤礦也近20,000人。在紡織業中,外資紗廠有的多到6,000-7,000人,中國紗廠也有5,000-6,000人的。在鐵路部門,1927年,京漢、京浦、京綏三線各有工人20,000人,京奉、隴海、南滿三線亦超過10,000人。1919年民族資本工廠335家中,工人在500人以上的有144家,1,000人以上的有29家。[5]工人階級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為后期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五四運動前后的民族資本經濟
中國的民族資本經濟是在外國侵略勢力與本國封建主義經濟共同壓迫的夾縫中艱難產生與生存的,自身比較弱小的民族資本主義,在有限的市場空間中,難以憑借自身的經濟實力在競爭中獲勝。在政治領域中也沒有足夠的力量為自己爭取應有的權力與政治地位,進而憑借政治力量來推進自身經濟的發展。因此,中國的民族資本經濟的發展是艱難曲折的。
五四運動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曾因帝國主義國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無暇東顧時,有過“短暫的春天”。 這一時期,民族工業無論從設廠數目、投資規模看,還是從增長速度方面看,都是其產生以來發展最快的一個時期。從1914年到1919年,民族資本共新設廠礦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資本8580萬元,平均每年1430萬元,年平均設廠數和投資額均比此前19年間增長一倍以上。從1913年到1920年,民族產業資本的年平均增長率為10.54%。民族資本在全國產業資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民族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的發展,引起了社會階級關系的新變動,促進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長。
五四運動時,各地民族資本的工商業正面臨著帝國主義勢力在一戰后卷土重來的威脅。五四學生運動提出了抵制日本貨,勸用國貨的口號,對工商業者來說是有利的。北京的商會立即表示贊助學生的行動,接著,天津、上海和全國許多城市的商會也紛紛響應。同時,不斷高漲的反帝愛國革命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著外國資本對華的侵略,為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個相對較好的機會,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帝國主義國家開始向中國大量輸入商品,尤其以日本為最。當時日本輸華的商品主要為棉紗,再加上日商在華投資設廠,從而對中國民族資本企業形成巨大壓力。但五四運動爆發后,全國人民愛國熱情高漲,掀起抵制日貨運動,成效顯著。日紗輸華數量,1918年為746000擔,1919年下降為 531000擔。日紗在1918年占中國棉紗進口總量的66%,在1919年只占38%。[6]
五四運動后,就中國的經濟情況來看,近代工業的發展水平還是很低的。但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并未因一戰后帝國主義的卷土重來,立即就陷入蕭條破產的境地,而是繼續發展的。據北洋政府農商部不完全的統計,全國資本較大的廠礦公司,1914年共計146家,資本總額4,100萬元。1922年,廠礦公司增加到了379家,資本總額16,000萬元。公司增加了1.5倍,資本增長了近3倍,平均資本由28萬元增至43萬元。這說明了廠礦數和投資規模都比以前增加和擴大。據估計1933年全國工廠數已在2,000家以上,資本額達4億元。[7]
資料表明,就工廠數目而論,棉紡織業、絲紡織行業、卷煙工業、面粉鉻鎳鋼業等四大行業,1919年共有工廠102家,到1927年增為315家,即1919-1927年8年中,就增加213家;1927年后工廠的數量有一定下降,但棉紡織業的設備和產量仍不斷增加。所以說,1919至1927年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是繼續發展的,1927年后發展速度放慢,但較之一次大戰期間及戰后幾年,發展速度仍較快。可見,五四愛國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資本經濟的發展,為其提供了良好的機會,也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二、生產力發展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20世紀的舊中國存在兩大問題,一是社會制度的落后,一是科學技術的不發達。這兩大問題互為因果,共同制約著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阻礙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五四新文化運動為解決這兩大問題提出了新思維、新方法。一是馬列主義的傳播,為中國指出了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是“賽先生”——科學的提出,科學救國思想的深入發展,為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它們都為當時及此后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必要和充分的條件。
1.生產力發展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
五四新文化運動極大促進了思想解放,猛烈地沖擊和蕩滌著幾千年來的封建舊禮教、舊道德、舊思想、舊文化,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開辟了道路。
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經過歷史的比較和實踐的選擇,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并積極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并不只是無產階級革命學說,對于中國的發展受益最大的,是中國人民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跨越了生產關系的“卡夫丁峽谷”,實現了社會制度的突破,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必不可缺少的條件。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新文化運動的陣營內部逐漸發生分化。馬克思主義者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之間出現了要不要馬克思主義、以什么主義改造中國社會的激烈論爭。其中有三場論爭在中國思想領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一場是關于“問題”與“主義”的論爭,它實際上是一次中國需要不需要馬克思主義、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論爭;一場是關于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于中國國情的論爭,它實際上是一次關于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實行社會革命還是實行社會改良以及需要不需要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論爭;還有一場是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爭,它實際上無產階級要不要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斗爭,用暴力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論爭。經過這三場論爭,一批進步青年初步感受到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的科學性和真理性,認清了科學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之間的本質區別,認識到只有科學社會主義才能達到救國救民和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的目標。
總之,五四新文化運動使人們認識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逐步明確了“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放與發展生產力”;中國要迅速改變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慘命運,從根本上改變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就必須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社會生產力要充分而徹底地發展,必須通過革命的手段從根本上推翻舊有的落后的封建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然后建立先進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同時,在隨后的實踐中,人們逐步認識到從舊中國的國情出發,最能有效地推動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生產關系與社會制度,并不是在較封建主義生產關系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應當是充分反映現代社會大生產發展要求的、更先進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近代中國要想建立充分適應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發展要求的先進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首先必須對傳統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進行變革,尤其要對由帝國主義入侵而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社會結構進行一次徹底的革命。這樣,就需要把原本要在生產力比較發達基礎上才可能發生的徹底的社會革命提前進行,以保證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
2.生產力發展與“賽先生”的提出
中日甲午戰爭失敗以后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社會的科技意識有了真正的提高。1915年創刊的《科學》雜志曾經指出:“世界強國,其民權國力之發展,必與其學術思想之進步為平行線,而學術荒蕪之國無幸焉。”“百年以來,歐美兩洲聲明文物之盛,震櫟前古,翔厥來原,受科學之賜為多。”[8]這兩句話充分概括了科學對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在東西方文明空前劇烈地碰撞和融合時,思想解放更加深刻與廣泛,知識分子對科學的認知與理解較之以前更全面更深刻。
五四新文化運動孕育著科學的偉大精神。以陳獨秀、魯迅、李大釗、胡適等人為代表的五四先進知識分子,以求實態度宣傳新科學新思想,激勵人們沖破舊的思想樊籬,尋求科學救國的道路。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為科學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科學者何?吾人對于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9]他提出要從客觀事物中尋求其規律,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包括在科學之中。他還突出強調了科學的重要性,把其與民主并重。“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再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9],“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9]“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它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論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黑暗。”[10]胡適則提出了“科學”的懷疑精神與探索方式,使“實驗主義”以工具理性的方式進入救國實踐。當然,科學的方法并不限于實驗主義,辯證法的唯物論也有同樣的重要。所以還有一部分新文化運動者,提倡辯證法的唯物論。可以說,五四新文化時期,人們對于科學的關注,既包括科學技術本身,也包括科學精神、科學方法。“賽恩斯”——科學——的重要,不是只限于機器的一方面;科學的精神,科學的方法比其他一切的科學的結果更為有價值。所以介紹科學的方法,是新文化運動者的責任。[11]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下,科學救國思想達到了高潮階段。對科學重要性的強調使整個社會的科學氛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為科學的普及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條件,促進了現代自然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也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作了充分的準備。不可否認,“科學救國”思想一定的局限性,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科學救國”并不能根本解決中國貧窮落后的狀況。而且,時人所理解的科學與當下的科學有一定的差距,但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必然會促進社會的變革與發展。由此可見,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選擇“科學救國”的艱途,實為難得。當然,更為難能可貴的,五四時期“賽先生”提出并頗受社會重視的重大意義,并不在乎當時的知識分子提供了多少具體的科學知識,而在于提出了新思維、新方法來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綜合以上的分析,對于五四運動的研究不能僅局限于思想文化層面,從生產力發展的視角來考察五四運動也是必要的。在生產力發展的視角下可以看出,生產力發展之于五四愛國運動來說,其作用是顯性的,當時生產力發展的落后狀況是導致愛國運動爆發的經濟根源,而五四愛國運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于生產力發展來說,其作用則是隱性的,卻又是極其重要的。無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還是科學技術認識的提升,都是社會生產力得以快速發展不可缺少的因素。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2.
[2]彭明.五四運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2).
[3]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23-24.
[4][5]凌耀倫、熊甫、裴倜.中國近代經濟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2:361,362.
[6]榮家企業史料:上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64-65.
[7]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M].上海:三聯書店1961:21.
[8]科學[J].發刊詞,1915年:1.
[9]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志[J].1914:1.
[10]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J].第6卷第1號.
[11]伍啟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況[M].黃山:黃山書社,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