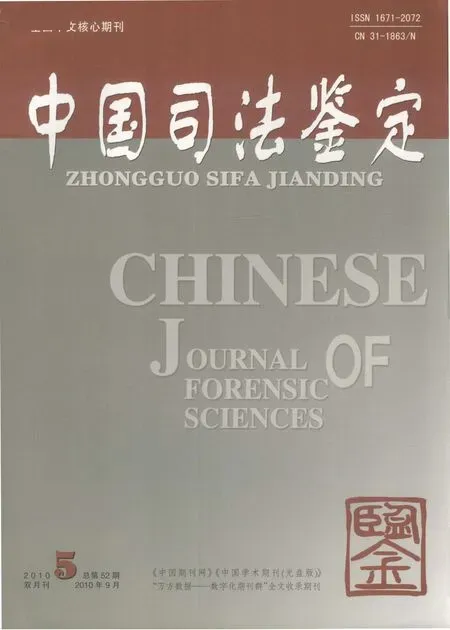論我國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完善
劉建偉
(中國政法大學 證據科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北京100088)
論我國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完善
劉建偉
(中國政法大學 證據科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北京100088)
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對法官采信正確鑒定意見、消除當事人對鑒定意見的懷疑、提高鑒定質量都有重要作用。但目前由于種種原因,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率極低,需要我們認真分析其原因,完善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
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
Abstract:Court Testimony of Forensic Appraiser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judges’ accepting correct expert opinions and eliminating litigant suspicions regarding expert opinions and improving the appraisal quality.However,in China’s legal practice,it’s seldom for forensic appraisers to be testimonied in court,the reason of which needs to be analyzed carefully,so as to improve this system.
Key words:forensic appraiser;appear in court;court testimony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法制的完善,司法鑒定在司法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而帶有科學性光環的鑒定意見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成為公正裁判唯一可以選擇的依據。但是,要想讓鑒定意見真正造福于司法審判,必須保證它的真實性。而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又是保證司法鑒定意見真實性的一根保險絲。
西方有句法諺,“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讓人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即是這樣一種讓人看得見的實現正義的途徑。作為法定證據之一,鑒定意見只有經過充分質證方可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而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就是認定鑒定意見證明力的核心問題,這已成為業界的共識。
1 我國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現狀
1.1 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率極低
據不完全統計,在2000年前刑事案件的審理中,鑒定人的平均出庭率不足5%[1]。民事訴訟中,鑒定人出庭作證的比率更低。據2002年12月21日在廈門民事訴訟證據研討會上的統計資料顯示,鑒定人出庭參加庭審的比例不到2%[2]另據有關部門統計,2003年吉林省的高級和中級法院進行司法鑒定的案件共有2 153件,其中鑒定人出庭參與質證的僅為17件,出庭率僅為0.8%。在江蘇省蘇南某基層法院,2007年審結刑事案件320件,涉及司法鑒定的268件,占案件總數的83.75%,無一件案件的鑒定人出庭作證[3]。2008年度,以江蘇省蘇州市為例,在蘇州市兩級法院審理經過司法鑒定的6 009起案件中,通知鑒定人出庭的案件86件,實際出庭33件,不足0.6%[4]。面對如此之低的出庭率,不能不使我們對我國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問題進行冷靜地思考。
1.2 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誠然,從理論上來講,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設立對法官采信正確的鑒定意見,對雙方當事人消除對鑒定的懷疑而有效地減少纏訴,對鑒定人提高鑒定質量、保證鑒定意見真實合法而防止錯鑒的發生等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但在實踐中,那些極少數有鑒定人出庭作證的案件實際效果又如何呢?筆者幾次出庭的親身經歷使筆者感到在我國目前的司法環境中,即使鑒定人出庭,由于我國對司法鑒定人的質證程序、內容規定有所欠缺,使得鑒定意見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也不能在法庭質證過程中得到充分辨認,對鑒定人的質證很難起到預期的效果。出庭作證要么流于形式,無任何實質意義;要么成為法官保證在規定期限內結案的“道具”;更有甚者可能淪為當事人玩弄訴訟技巧的工具。
1.3 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法律法規尚不完善
近些年通過我國法律工作者的不斷努力,我國現有關于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法律法規漸成體系,如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下簡稱 《決定》)、《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司法部《司法鑒定人管理辦法》等有關法律、法規中都明確規定司法鑒定人須出庭作證。而2007年4月1日開始實施的國務院關于 《訴訟費用交納方法》又對司法鑒定人因出庭而受損的經濟利益進行補償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可見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保證社會化的司法鑒定機構中的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的。但仍然不夠完善,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我國現有的一些法律法規多是從宏觀上規范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的,可操作性不強。在一些有關出庭作證的程序細節上缺少統一規定,比如如何保證隸屬于偵查機關的司法鑒定人也能出庭接受質證;在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的通知時間期限、鑒定人出庭是在法庭上座位的安排等方面上沒有統一規定,造成每次出庭因案因主審法官不同而要求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現有的法律法規對鑒定人的出庭工作義務要求有余,權利保障不足。如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十三條又對“經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拒絕出庭作證的”司法鑒定人制定了處罰規定。這作為法定義務來規定的鑒定人出庭作證行為的,而很少能從制度上保障鑒定人的權利。對鑒定人來說,出庭作證需要花費時間、精力,甚至還冒一定的危險,在審判實踐中,司法鑒定的出庭鑒定費用的收取相當有難度,雖然現有法規原則上規定了鑒定人出庭可收取費用,但沒有明確規定這筆費用的補償標準,該項費用的核算尚處于“空白”狀態,從而常常因交納該費用的義務人拒絕交納而導致費用收取不能。對鑒定人來說,人身方面的保護更為重要。鑒定人從事的是事關當事人利益的鑒定活動,鑒定意見往往對一方當事人不利。而且目前的訴訟活動中,鑒定意見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雙方當事人都想獲得對自己有利的鑒定意見。因此,當事人可能用各種方法對鑒定人施加壓力,甚至是暴力手段。鑒定人在作出鑒定結論后,也可能遭到一方當事人的報復,危及自己、家人的安全。2007年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統計,全國每年發生的證人、舉報人致殘、致死案件從20世紀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現在每年1 200多件[5],這里的證人包括鑒定人。因此,法律對鑒定人人身方面的保護極為重要。目前我國法律沒有規定相應措施保障他們出庭作證時的經濟損失和人身安全,進而導致權利和義務的失衡。
綜上所述,由于我國相關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不完善,司法鑒定人出庭率極低,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很難起到制度設置之初的預期效果,因而使得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大有雞肋之痛的感覺,這不由地促使我們對產生這一現狀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
2 我國司法鑒定人出庭率低的原因分析
關于我國司法鑒定人出庭率低的原因,近年來很多專家學者進行了大量的論述,這里不一一列數。大家普遍認為制約鑒定人出庭作證的因素有很多,然而在這些因素中幾乎一致的觀點均將司法鑒定的主體——司法鑒定人有意回避甚至逃避出庭作證看成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情況果真如此嗎?筆者作為有著十余年工作經驗的司法鑒定人,以自身為例,自從事司法鑒定工作以來出具的3 000余份司法鑒定結論中,出過庭的案件僅有12件,出庭率不足0.4%;去年筆者所在鑒定機構共出具司法鑒定結論3 000余份,參加出庭作證的也僅有20多件,出庭率不足1%(其他鑒定機構的情況與此類似)。這似乎進一步驗證了我國司法鑒定人出庭率低這一事實。但我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只要是法院要求出庭的案件我們均出庭參加了質證。也就是說在這些進行了司法鑒定的案件中,只有為數很少的案件法院要求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所以我們應該這樣描述:在我國進行了司法鑒定的訴訟案件中,要求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的案件比例極低。所以相應的,我國司法鑒定人出庭率低的問題也就轉化成為要求司法鑒定人出庭的案件比例低的問題。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法院在案件審理中很少要求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呢?筆者認為大體有以下幾個原因:
2.1 雙方當事人對鑒定意見不存異議
《決定》第11條明確規定:“在訴訟中,當事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的,經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根據這一規定,在訴訟中,鑒定人出庭作證取決于兩個條件:其一,當事人對已形成的鑒定意見有異議;其二,經人民法院依法通知。具備這兩個條件,鑒定人就應當出庭作證,反之,鑒定人則不需要出庭作證或可以不出庭作證[6]。在一些訴訟案件中,當事人對司法鑒定機構出具的司法鑒定結論并不持有異議。例如在一些筆跡鑒定的案件中,筆跡為誰所寫當事人雙方心知肚明。筆跡書寫者往往抱著僥幸的心態拒絕承認,從而啟動司法鑒定。當鑒定人做出認定其書寫的正確結論后,僥幸的心態被戳破,往往也就“不再狡辯”了。這種情況下,鑒定人可以不出庭作證,從而彰顯了提高訴訟效率,節約訴訟資源的價值追求,于國于民都是有好處的。
2.2 法官認識上的偏差
我國訴訟雖然采用了控辯式的模式,但法官仍然以書面筆錄作為審理、判決的主要基礎,對刑事被告人的供述筆錄以及民事訴訟的書證情有獨鐘,實質上未樹立起以庭審中經過當事人(控辯)雙方質證的證據作為定案根據的觀念。鑒定人出庭與否對法官認定案件事實、對鑒定意見的采信與否,幾乎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法官對鑒定人不出庭現象熟視無睹,并認為在沒有鑒定人出庭作證的情況下靠宣讀鑒定意見可以查明案件的事實與真相;同時,可以避免因鑒定人出庭導致鑒定意見再次出現爭議,使法官采納鑒定意見出現困難。因此,對于法官來說,鑒定人出庭不如不出庭[7]。筆者曾受理一起重新鑒定案件,一方當事人對初次鑒定的結論有異議,要求鑒定人出庭,而主審法官認為該鑒定機構隸屬于偵查機關,即使通知鑒定人出庭,鑒定人也不會出庭,所以干脆不通知,而直接到我處進行重新鑒定。
2.3 一些案件高昂的出庭費用的影響
從法理上說,權利和義務是相輔相成的,只享受權利而不承擔義務,或者只承擔義務而不能享受權利,都不是法律生活的常態。作為與案件沒有利害關系的訴訟參與人,鑒定人出庭作證是一種承擔法律義務的行為,必然需要一定的權利為保障。鑒定人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做出鑒定,并且需要花費時間和精力為出庭進行準備,而出庭作證目的是讓法院能更準確地采信證據,從而做出正確的裁判,法院應該考慮鑒定人的個人權益,經濟補償是在情理之中[8]。根據2007年4月1日實施的國務院關于 《訴訟費用交納方法》(以下簡稱《方法》)第11條之規定:“證人、鑒定人、翻譯人員和理算人員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發生的交通費、住宿費、生活費和誤工補貼,由人民法院按照國家標準代為收取。”應該說,雖然《方法》中規定的標準并不很高,卻對保障鑒定人的經濟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據。然而,盡管按此方法計算,一般案件的出庭費用并不很多,但實踐中有一些異地委托的案件由于鑒定人與傳喚其到庭的法院地理位置相距太遠,造成交通費用相對較貴,使鑒定人實際出庭的可能很小,甚至成為不能。試想,一個西藏的基層法院通知北京一名作傷殘鑒定的鑒定人到法庭作證,勢必會產生高昂的交通費分擔問題,這筆費用對當事人來講必然造成沉重負擔,這位鑒定人出庭作證的可能性有多大?而隨著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第8條“各鑒定機構接受委托從事司法鑒定業務,不受地域范圍的限制”之規定,異地委托司法鑒定的案件正大量增加,這勢必給日后的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增加了很大的阻力。
2.4 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流于形式
從筆者和所在單位同事的幾次親身經歷出庭作證的案件來看,目前在我國,即使鑒定人出庭了,由于我國對司法鑒定人的質證程序、內容規定還有欠缺,對鑒定人的質證也常常只是一種形式,無法保障當事人的權益,無任何實質意義。原因在于,當事人在庭上對司法鑒定人所提的問題無怪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鑒定委托程序上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具體鑒定過程、方法等技術層面上的問題。對于前者,由于目前受理的鑒定案件多為由法院的法官直接委托進入到訴訟程序中的案件,所以從委托程序上提問題,無疑是在挑法官的毛病,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往往都不需要鑒定人多說,法官就加以解釋或予以制止了;而對于后者,由于當事人及其代理人缺少專業上的知識,根本提不出多少有用的問題,鑒定人只要運用專業知識稍加解釋,他們也就無法繼續深入發問了。雖然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有關專家輔助人制度的引入,有些案件當事人會聘請專家輔助人對鑒定人提一些專業性的問題。但當雙方專家對深奧的專業問題進行爭辯時,坐在審判席上的法官由于缺乏專業知識而無法分辨,往往也起不到多大作用,比如在某省高院法庭的一件關于確定文件制成時間鑒定人出庭作證的案件,當鑒定人與當事人聘請的專家輔助人就專業問題在法庭上大擺科學數據時,主審法官終止了他們的辯論,理由是他們根本聽不懂。可見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要想在我國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有很長的路要走。
2.5 依職權要求鑒定人出庭作證被濫用
有些法官由于案件即將超審限,為了在期限內將案子審理完畢,在鑒定機構出具鑒定結論后沒有按規定送交雙方當事人,而直接要求鑒定人出庭作證。此時當然也不存在當事人對鑒定結論有異議的可能。例如2007年12月中旬,筆者所作的鑒定案件突然有兩件委托法官緊急通知需要出庭作證。其中一個案子在筆者調整了日程按時出庭作證時,才發現雙方當事人開庭前并未見到鑒定書,而只是在庭上才知道鑒定結論的。法官向雙方當事人宣布本案鑒定人已經到庭,當事人對鑒定結論有何異議,請鑒定人當場予以解答。在這種情況下,鑒定結論對其不利的一方當事人勉強地提出一個程序上的問題。整個出庭僅僅用時5分鐘,鑒定人就被告知出庭結束,可以離開了。而由于是異地出庭,為了這5分鐘,鑒定人花費了兩天時間,并錯過了一場重要的學術會議,而當事人為此則支付了高昂的出庭費用。原因只為法官要趕在年底前將案件審結,如果這次開庭鑒定人不出庭,一旦當事人對鑒定結論有異議而提出鑒定人出庭申請,法官勢必需要通知鑒定人,需要再安排時間開一次庭,而這樣年底就結不了案了。所以就讓鑒定人在庭上候著,隨時答復可能出現的異議。可見,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在此種情況下已被濫用的無以復加。
2.6 一方訴訟代理人請求鑒定人出庭作證
有些案件當事人申請鑒定人出庭作證并不是因為其對不利于己的鑒定結論真的有異議,而是其訴訟代理人基于庭審技巧而慫恿當事人提出申請。他們往往用這樣的話來說服其委托人,“鑒定人一般不會出庭的,你盡管要求他出庭。一旦他不來,我們就可以要求法官不采信這個鑒定結論了”。這種情況下,只要鑒定人按時出庭,他的陰謀就不能得逞了。例如近期筆者出庭的一個案件,當事人對鑒定結論有異議,向法官提出申請要求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證,并且明確要求參與該案鑒定的三名鑒定人均要到庭,否則就說明鑒定程序有問題。法官跟我們協商說當事人比較難纏,希望我們三位鑒定人都能到庭。我們為了讓當事人的伎倆不能得逞,同時也是配合法官的工作,決定三位鑒定人一起出庭。當事人的代理人看到我們鑒定人都到庭后有點出乎意料,草草地提了幾個無關緊要的問題就結束了,最終法官采信了我們的鑒定意見。
3 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相關制度不完善
3.1 單一追求司法鑒定人出庭率來評價司法鑒定人出庭制度的優劣
長期以來,法律學者一直陷入“司法鑒定人應該每個案子都出庭作證”的誤區,甚至以出庭率100%作為制度設計的終極目標。這與司法鑒定這門行業的特點及其規律是不相符的。一方面,司法鑒定意見因其具有科學性、客觀性等特點,絕大多數情況下是能夠真實地反映事物的本來面目的。而大多數情況下雙方當事人對鑒定意見是不存在異議的,或即使鑒定文書中存在瑕疵細節,但因其不影響鑒定結論的準確性,當事人考慮到訴訟成本一般也不會申請鑒定人出庭。這種情況下再一味要求鑒定人出庭,顯然造成訴訟資源的極大浪費;另一方面,現有司法鑒定機構的鑒定人員編制配置狀況也不能承受所有案件都支持出庭的壓力。鑒定人出庭所耗費的時間精力往往并不低于鑒定本身,每案都出庭勢必大大增加了鑒定人的負擔。這不僅在實踐中做不到,也是沒有必要的。在大陸法系國家如法國、德國等國,雖然原則上均規定鑒定人需要出庭,但實踐中“法官對鑒定事項的認定主要還是依據鑒定人所提交的書面鑒定報告進行的,而一般不要求鑒定人出庭作證”[9]。一般來說,在大陸法系國家,如果法官認為鑒定人不需要出庭時,鑒定人可以向法庭提交書面意見即可[10]。即使是質證程序以典型的當事人主義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國家,也沒有做到“每案必出”。由于專家證言涉及較強的技術性和復雜的專業性,使得庭審質證活動常常引起專家之間的 “科學大戰”,不僅造成了庭審的拖延、時間和費用支出的昂貴,而且使得當事人在訴訟中不堪重負。近年來,英美法系國家已著手對專家制度進行一定的改革:專家證言通過庭前開示,對當事人沒有異議的,專家證人可以提供書面報告而不出庭作證[11]。值得一提的是,在近年來,在英美國家所進行的專家證人制度改革過程中,出于訴訟效率和訴訟經濟的考慮,越來越多的鼓勵專家書面證言的使用[12]。據來華交流的英國蘇格蘭場法庭科學服務部(FSS)的專家介紹,2006年該機構的出庭率為40%,而且他們只有經過出庭培訓的高級鑒定人員才有資格出庭作證,一般的鑒定人員不能出庭。可見,我們不應僅以司法鑒定人出庭率的高低來衡量一個國家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優劣。對我國現有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現狀的也不應過度“悲觀”。
3.2 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配套細則的滯后
我國現有的一些法律法規雖然對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的義務進行了規定,但大多是從對宏觀上規范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的,往往比較原則性,可操作性不強。我國現有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過分泛化,對一些程序上的操作細節缺少統一明確規定。自從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出臺,至今已五年有余,有關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配套細則仍未出臺,不能不說是與相關主管部門的懈怠作為有關。由于缺少配套的統一規定,造成每次出庭因案因主審法官不同而要求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混亂。鑒定人出庭作證程序細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的內容:例如何時通知司法鑒定人出庭,在實踐中,在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的通知時間期限上沒有統一規定。各地方法規有的規定開庭前3日向司法鑒定人送達出庭通知,有的地方規定5日。其實司法鑒定人能否有充足時間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做好出庭準備對保證按時出庭至關重要;開庭時司法鑒定人應攜帶哪些證明材料,除了自己的執業證明之外,鑒定機構的《司法鑒定許可證》原件是否一定需要攜帶,因為按規定該原件應該懸掛在鑒定機構辦公場所的顯著位置,所以鑒定人在出庭時往往只能出具復印件,況且鑒定機構的信息也可以在當地司法行政管理機關的辦公網站上查詢到。在一起異地出庭的案件中,某鑒定機構鑒定人就曾有因未帶所在司法鑒定機構的《司法鑒定許可證》原件而被法庭要求補來原件后再另行開庭的遭遇;庭審時,應對司法鑒定人就哪些方面進行質證,如需對鑒定人的資格、鑒定方法、依據、過程、檢材以及結論等在法庭上進行公開的質證,而那些與鑒定無關、內容重復、有損司法鑒定人的人格尊嚴及涉及案件以外第三人的利益或國家利益等問題,鑒定人在庭上可以向法官申請拒絕回答。
3.3 忽視司法鑒定人權力的保障
我國司法鑒定人的訴訟地位在法律上是沒有明確規定的。學術界對鑒定人的地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是“具有專門知識的人”,有的認為是“專業技術人員”,也有人認為是“科學技術專家”。從我國法律的規定看,《刑事訴訟法》第119條規定,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決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的時候,應當指派、聘請具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鑒定。第82條將司法鑒定人規定為與證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并列的訴訟參與人。可見,我國的鑒定人既不同于大陸法系的法官的科學助手,也有別于英美法系的雙方當事人的專家證人,它既是幫助司法機關解決訴訟有關專門性問題的專家,又是訴訟參與人之一。可以說我國司法鑒定人的地位比英美法系的高,比大陸法系的低。
應該看到,我國現行的主體鑒定模式接近于大陸法系的司法鑒定制度,由法官依職權或經當事人申請啟動鑒定程序并選任適格鑒定人。在這種模式下,鑒定人與當事人之間無直接經濟聯系,而是為法官解決專門性問題的。但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對于鑒定人的地位往往參照英美法系專家證人的地位,更多地將鑒定人視為當事人(尤其是鑒定意見對其有利的一方當事人)的顧問,而忽視了鑒定人為法庭訴訟解決專門性問題的職能,從而過于強調鑒定人證人性質的一面,以致一味強調鑒定人出庭作證的義務,而忽視了對其權力的保障,沒有明確規定鑒定人享有的相應權利。司法鑒定人的權利除了前述提到的鑒定人出庭有獲得經濟補償和人身保護的權利外,司法鑒定人還應享有隱私權,在開庭時,鑒定人的一些個人信息,如家庭住址、身份證號碼,不應在庭上公開給當事人。否則勢必會對鑒定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構成威脅;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時,還應享有專門座位的權利,筆者一次出庭就差點被安排在被告人的位置。在提出異議后,才在旁聽席上被安置下來;此外,司法鑒定人因出庭進入法院時,應該享有同律師一樣的安檢免檢權,……凡此種種,均缺少明確的規定。
4 完善我國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思考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我國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是鑒定人出庭率低的問題,而是如何保證那些因當事人對鑒定結論存在異議而需要出庭的案件司法鑒定人到庭作證的問題。因此我們有必要圍繞這一問題來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4.1 應規定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例外的情形
鑒定意見往往對案件事實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其本身是否科學、可靠,普通人通過閱讀鑒定書一般難以判斷,需要鑒定人出庭予以說明,并接受當事人(控辯)雙方的質疑。然而,鑒定人對所鑒定的案件一律出庭雖然能滿足法庭審理證據的需要,但不經濟,在實踐中往往也沒有必要。鑒定人出庭接受當事人的質詢是原則性的規定,但在特定的情況下,如果符合法定的條件,鑒定人也應享有不出庭的權利。法制發達國家和地區對此也作出了相應的規定①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51條規定了鑒定人不到庭的四種例外情形。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區法院《關于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的若干規定(試行)》第8條規定:“下列情形,司法鑒定人可以不出庭:(一)所作鑒定結論經過法庭質證,控辯雙方均無異議,僅是標點、校對或語言不當方面的失誤;(二)鑒定結論由兩人以上共同作出,且鑒定意見無分歧的,已有一鑒定人出庭;(三)鑒定結論已被新的鑒定結論所取代,且該鑒定結論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法律適用不起決定作用;(四)司法鑒定人因重病、死亡、失蹤或其他客觀條件限制無法出庭的。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8年7月1日實施的《有關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的規定》第十三條也規定:“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鑒定人經人民法院同意可以不出庭:(一)該鑒定意見對案件的審判不起決定作用;(二)兩名以上司法鑒定人共同做出的鑒定意見,已有一名鑒定人出庭,并向法院提交了其他鑒定人的書面授權;(三)司法鑒定人因突發疾病、重病或者行動極為不便的;(四)司法鑒定人因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無法出庭的;(五)因其他特殊客觀原因確實無法出庭的。”。筆者認為,根據案件的審判需要及鑒定人出庭作證的條件,為降低不必要的訴訟成本,適當規定鑒定人可以不出庭作證的例外情況,符合我國的國情。要求那些存在爭議的和對重大案件提供意見的鑒定人——既包括面向社會服務的司法鑒定機構的鑒定人,也應該包括隸屬于偵查機關的鑒定機構的鑒定人出庭則具有可行性,符合法律規定的意圖,也符合實踐中的一貫做法。這樣做有助于將有限的司法資源用在那些需要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的案件上,提高了訴訟效率,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司法公正。
4.2 制定對偵查機關的司法鑒定人拒絕出庭作證的制約措施
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對面向社會服務的司法鑒定機構中的司法鑒定人不出庭的制裁是比較嚴格的:一經投訴,鑒定人資格就會被司法行政管理部門吊銷。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保證這些鑒定人的出庭作證。然而,在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著少數需要出庭而司法鑒定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作證的情形,這些鑒定人員大多都是隸屬于公安、檢察及國家安全機關的鑒定機構。這種情況的產生是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雖然將司法鑒定機構的管理工作授權給司法行政機關,但它只能對那些面向社會服務的、在其省級機構登記的社會上的鑒定機構中的鑒定人員進行處罰,而對隸屬于公安、檢察及國家安全機關的鑒定人員它是無權進行處罰的。因而對隸屬于偵查機關的司法鑒定人拒絕出庭作證的制約措施的制定是保證那些需要出庭作證的案件出庭率的一個重要因素。
4.3 設置鑒定人出庭前書面異議答復制度和網絡視頻出庭制度
對于那些因當事人對鑒定意見存在爭議而需要鑒定人出庭作證的案件,在出庭前先由鑒定人對當事人存在的主要爭議給予書面答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當事人的異議,而減少鑒定人出庭的需求。這種做法在現實司法實踐中是可取的。一般情況下,當事人對鑒定意見的爭議往往存在于委托鑒定的程序合法性,用于鑒定的材料來源的真實性、鑒定文書的格式與表述等方面,鑒定人通過書面解答的方式就可消除當事人的疑慮。如此一來,就可減少一些爭議不是很大的案件的出庭,從而有助于節約訴訟資源,提高訴訟效率。對那些異地委托的案件,如果鑒定人必須出庭而當事人因高昂的出庭費用無法支付時,還可利用發達的網絡技術開展網絡視頻出庭。這樣既節約了當事人的費用,又保證鑒定人可以在庭上接受法官及雙方當事人的質詢。如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檢察院、四川省公安廳、四川省司法廳《關于死刑第二審案件證人、鑒定人出庭二審案件作證的若干意見》第7條規定:“……不出庭的證人,可以提交書面證言或者視聽資料或者通過雙向視聽傳輸技術手段作證。不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對相關質詢問題作出書面答復。”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為鑒定人通過網絡視頻的方式出庭作證提供了現實的技術上的可能。如果運用了這些現代科學成果,我們可以設想:在北京進行傷殘鑒定的專家,就可以借助可視電話,走進西藏一個基層法院的審判法庭,接受法官、控辯雙方的質疑和詢問,釋卻當事人心中的疑慮。
4.4 設立鑒定人出庭作證基金制度
在刑事訴訟中,司法鑒定人的出庭費用往往要由負責審理案件的法院承擔。目前我國多數基層法院的辦案經費有限,與公正司法對經費保障的要求還相差甚遠。受辦案經費所限,那些應該支付給出庭作證的鑒定人的合理費用包括差旅費、誤工費,就不得不被“節約”掉了,由此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鑒定人出庭作證的機會。為此,國家應當設立鑒定人出庭作證專項基金,用于對鑒定人出庭作證的經濟補償,并對補償對象、范圍、條件以及補償標準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以便于操作。鑒定人補償項目應包括誤工費、交通費、食宿費和其他經濟損失。對鑒定人因作證而遭受的經濟損失以及本人或其近親屬受到的人身傷害,致殘或死亡的,可按國家賠償法的賠償標準進行賠償。
4.5 應設立專家陪審員制度
由于鑒定意見涉及專門性問題,對其證據價值的評估與判斷往往離不開專門知識與經驗,因此,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法官在審判中對鑒定意見的認識大多仍然停留在對其證據能力 (如鑒定人是否有資格、是否有回避的情形等問題)的審查認證上。對于法官與當事人對鑒定意見判斷和質證所產生的困惑、專家輔助人與鑒定人就專門性問題進行辯論所引發的尷尬,只有聘請具有中立地位的技術顧問為專家陪審員,才可能將具有專門知識的人所解答的專門性問題轉換成事實領域中的社會性問題,并通過專家陪審員、專家輔助人和司法鑒定人三維構造的庭審質證模式來提高或者保證鑒定意見的質量。聘請專家陪審員協助法官對鑒定結論的證據力進行審查認證,不失為一種避免鑒定結論失當的有效途徑,尤其在所需鑒定之問題復雜、各方對鑒定結論意見分歧嚴重時[13]。
4.6 完善我國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制度的操作細則
我國現有的一些法律法規多是從對宏觀上規范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的,往往比較原則性,可操作性不強,且多是規范鑒定人的作證義務的,對權力保障方面的確存在不完善之處。偶有規定或措施,也多為籠統表述,實踐中很少有可遵循的依據,應盡快完善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細則,在強調司法鑒定人具有出庭作證的法律義務的同時,應切實保證其應享有的權力。如人身安全保障、收取出庭相關費用權,進入法庭安檢免檢權、法庭專用席位的設置等等,從而切實保證司法鑒定人的權力,利用制度鼓勵鑒定人出庭作證,為公正的判決提供有力支持。
[1]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2]余漢春.影響鑒定人出庭質證的因素與對策[J].中國司法鑒定,2006,(4):59.
[3]寧紅.刑事鑒定人出庭率為何低[N].江蘇法制報,2008-3-20(7).
[4]施曉玲.鑒定人出庭質證的相關法律問題[J].中國司法鑒定,2010,(3):87-89.
[5]李曉光.最高人民檢察院:舉報人年受害案1200多件,將推保護新措[EB/OL].(2007-09-24)[2010-04-01].http://www.hnse.com.cn/news/2007/09/24/219162.html.
[6]顧永忠.略論鑒定人出庭作證[J].中國司法鑒定,2007,(1):10.
[7]郭華.鑒定意見證明論——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規則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
[8]吳丹紅.我國鑒定人出庭制度探析[J].中國司法鑒定,2003,(2):
[9]周湘雄.英美專家證人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27.
[10]汪建成,孫遠.刑事鑒定結論研究[M]//司法部法規教育司.司法鑒定立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1]郭華.鑒定意見證明論——司法鑒定人出庭作證規則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
[12]徐昕.英國民事訴訟與民事司法改革[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353-356.
[13]許為安.論鑒定結論的質證[J].中國司法鑒定,2008,(1):8.
(本文編輯:胡錫慶)
Several Thoughts on Improving the Court Testimony of Forensic Appraisers in China
LIU Jian-wei
(Key Laboratory of Evidence Science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DF794
A
10.3969/j.issn.1671-2072.2010.05.004
1671-2072-(2010)05-0022-06
2010-07-11
劉建偉(1974-),男,副教授,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