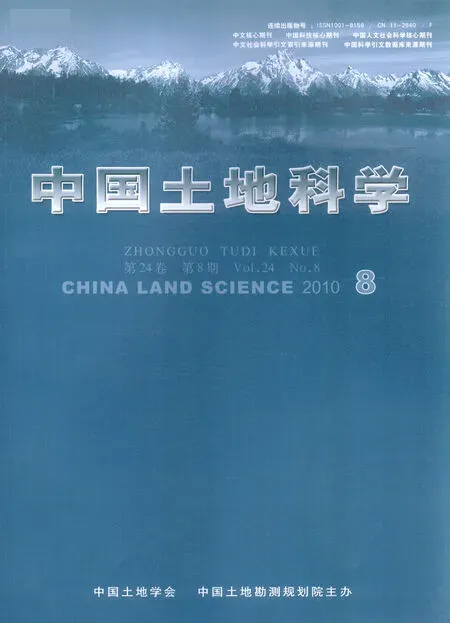論集體土地所有權行使程序的缺失與完善——以法教義學的分析為視角
祝之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湖北 武 漢430223)
“集體所有權是指一定的團體或社區在其成員平等、民主的基礎上形成集體共同意志,對其財產進行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1]集體共同意志的形成過程以及實施該意志的過程即集體所有權的行使程序。集體所有權的行使程序是將抽象的集體所有權法律概念轉化為現實法律制度的關鍵點。作為一種最重要的集體所有權,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程序建設實乃完善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一項重大課題。但是,“長期以來,中國民事實體法忽視了權利行使的程序的規定,沒有給予程序應有的重視。……因此造成這些權利在實踐中無法落到實處,出現了大量的權利被虛置的情況,集體所有權就是典型的例證[2]。”不僅如此,大多數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也呈現著“重實體而輕程序”的學術傾向。程序立法的缺失與學術研究的失衡互為表里,亟待糾正。
1 集體土地所有權行使程序研究述評
集體土地所有權行使程序是集體土地所有權制度的一部分。目前,學術界針對行使程序的專題研究尚屬空白,但若放大到集體土地所有權制度的宏大視域,亦可將相關研究大致分為兩種觀點。一種觀點主張完善現行集體土地所有權代行制度,即“通過一定制度安排,由某種組織(能成為民事主體之法律地位的法人組織)或者特殊機構來代表‘農民集體’充當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行使主體,以便達到所有權人的終極目的之實現”[3]。另一種觀點則主張“建立健全農民集體法人的組織機構和治理結構,按照法人的治理結構規則行使集體土地所有權”[4]。兩種觀點實質上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傾向,前者維護現行代表行使制度,后者致力于農民集體的“法人化”,意圖通過重構主體制度解決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行使問題;前者保守,后者激進。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和傾向均不是完善中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行使制度的現實選擇。
1.1 集體土地所有權代表行使制度割裂集體成員共同意志與代表者的意志,違背所有權法理
現代法學研究揭示了權利的本質不是單純的利益,也不是單純的意志,而“總是由‘特定利益’與‘法律上之力’兩個要素構成”[5],是利益與意志的結合,兩者缺一不可。但是,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代表行使制度卻以代表者的意志代替農民集體的意志,使得作為權利主體的農民集體喪失應有的話語權。而話語權的喪失勢必造成其利益實現的障礙。現實生活中大量出現的村委會濫用職權任意調整承包地的現象便是明證。因此,完善集體土地所有權代表行使制度的方案違背所有權的基本法理,并不可行。
1.2 農民集體“法人化”的觀點不符合法人組織自身發展的歷史邏輯和中國農村的社會現實
“制度的起源并不在于構設或設計,而在于成功且存續下來的實踐[6]。”法人是具有獨立的名稱、機構、場所并能獨立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的組織體。一種組織是否應該被構造成法人的形式,取決于其自身發展的程度,不是立法者所能決定的。因為任何組織的形成和發展都是一個歷史過程,如果將不成熟的組織規定為法人,不僅浪費立法資源,而且有違法人組織自身發展的歷史邏輯。將農民集體塑造成一種法人組織的觀點正是如此。另外,相對于學者們對制度構建的偏好,農民的發言權和選擇才是最重要的。農民集體的法人化依賴于集體內部成員的共同選擇,而不能依賴于國家的強制性政策或命令。就全國而言,目前還沒有普遍出現對農民集體法人化的需求。
1.3 建立集體土地所有權行使程序是完善中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制度的現實選擇
相對于保守的現狀維持派以及激進的農民集體法人化觀點,筆者認為,建立健全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行使程序是一項科學可行的制度選擇。建立集體土地所有權行使程序的實質是為廣大農民群眾參與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行使創造一個受法律保護的制度平臺以形成集體意志,進而維護其所有權主體地位。這符合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物權法原理,與目前農民集體較低的組織化程度相適應。再者,改革開放以來村民自治的實踐也為建立集體土地所有權行使程序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因而,從程序建設的角度完善集體土地所有權制度具有較強的可行性。
2 現行集體土地所有權行使制度中的程序缺失
《民法通則》是中國第一部對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行使問題作出規定的基本法律。此后的《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農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物權法》都不同程度地對《民法通則》規定的集體土地所有權行使制度進行了補充。這些法律規范初步建立了中國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代表行使制度和集體行使制度,但也存在如下問題。
2.1 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行使程序與村委會的村民會議議事程序混合在一起
集體土地所有權是一種私法權利,而村委會的權力則屬于公共權力。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行使依附于村委會的公共權力,致使村、組(特別是村民小組)的集體土地所有權沒有獨立的行使程序。這勢必混淆性質完全不同的私法權利和公共權力,從而使集體土地所有權在改革開放30年后依然具有濃重的政治色彩,而不能獨立和自治,并使其因政治權力和農民個體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雙重擠壓而虛置。
2.2 沒有科學地區分鄉鎮、村、村民小組三種彼此獨立的集體土地所有權
特別是對村民小組集體土地所有權——這一在人民公社時期已經具有基礎地位從而也是存在范圍最廣的集體土地所有權,現行法律則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由1986年《土地管理法》建立并被2007年《物權法》完全照搬的村民小組集體土地所有權行使制度更是不倫不類。因為村委會由村民選舉若干委員組成,可以代表村集體行使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而村民小組則不同,它本身就是由全體集體成員組成,村民小組即為村民小組集體,因此“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內各該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代表集體行使所有權”的法律規定完全不符合邏輯。
2.3 在具體程序方面的條文設置凌亂雜陳,極不統一
2001年《農村土地承包法》對土地承包程序做出相對完整的規定和程序設置。但是,對土地調整方案、土地補償費使用分配方案等則缺乏具體可操作的規定。因此,中國現行法律對集體土地所有權行使中的諸多事項,缺乏系統考量和統一規劃。另外,對于集體土地所有權代表行使制度,現行法律沒有設置任何制約所有權行使主體的程序。
上述問題歸結為一句話,就是程序缺失。集體土地所有權缺乏獨立的行使程序,已經規定的程序也因缺乏科學合理的配置而無法有效運作,進而造成中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完全成了一種被虛置的所有權。
3 完善中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行使程序的若干建議
3.1 強化團體觀念,確定農民集體的成員范圍
村民小組范圍內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是中國農村最為普遍的集體土地所有權類型,絕大多數的農村集體土地均屬此類。但是,很多該部分土地的發包和調整之權卻不屬于村民小組,而操于村委會之手,形成事實上的集體土地“組有村管”模式[7]。該模式不符合基本的物權法原理。為此應加強村民小組的團體觀念,從法律上明確設立村民小組會議或村民小組代表會議以及村民小組組長。同時明確規定在村內土地分別屬于各農民集體的村莊必須以集體土地所有權為基礎設立村民小組,而不得打亂集體土地歸屬再以其他因素(如居住狀況等)為基礎設立村民小組。另外,應尊重集體土地所有權行使主體的獨立性,三類主體在行使各自的土地所有權時彼此獨立,不存在隸屬關系,也不得相互干涉。
3.2 堅持成員自治,重塑土地所有權行使程序
所有權是“對物的最一般的實際主宰或潛在主宰”[8]。對集體土地所有權而言,最能體現集體意志支配的形式莫過于由集體成員組成的成員會議。因此,從權利與意志相統一的角度分析,作為土地所有權人的各農民集體通過成員會議以民主的方式形成集體意志并將該意志貫徹于集體土地之上的土地所有權集體行使制度是中國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較理想的制度,應作為一般的標準程序予以完善。當然,鑒于鄉鎮集體土地數量有限以及鄉鎮集體成員會議召集的諸多不便等,可以將鄉鎮集體土地所有權交由鄉鎮政府或人大行使。但在村、村民小組集體土地所有權之上完善集體行使程序則是可行的。因此建議廢除村、村民小組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代表行使制度而代之以集體行使制度,彰顯成員自治的價值取向。
3.3 完善具體程序,增強集體行使程序的適用性、統一性和可操作性
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其行使程序進行完善:(1)成員會議召集程序。召集成員會議的權利可依法賦予村民小組組長或村委會和一定比例的集體成員;(2)成員會議表決程序。成員會議對一般事項可經半數以上與會成員通過,重大事項則必須經2/3以上與會成員通過;(3)決議執行程序。村民小組組長、村委會或其他經成員會議授權的組織或個人可作為成員會議決議的執行者,其執行行為須依據一定的程序和要求,如不得越權、向相關成員進行說明和解釋、及時向成員會議匯報執行情況等;(4)通知、公告程序。召集成員會議必須通知所有成員或農戶,告知其時間、地點和事項等;成員會議表決內容和決議執行情況應及時公告。(5)不當行為救濟程序。對成員會議的非法決議、侵權決議或違反內部章程的決議以及決議執行者的類似執行行為,集體成員有權通過一定的程序予以糾正或通過人民法院進行救濟。(6)明確規定違反上述程序規定的法律責任,以增加其強制性和權威性。
(References):
[1]史際春.集體所有權研究[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97.
[2]王利明.中國民法典學者建議稿及立法理由·物權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64.
[3]丁關良.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多元行使主體研究[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320-326.
[4]張安毅.論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行使——評我國《物權法》草案第62條之規定[J].法學雜志,2006,(5):149-152.
[5]梁慧星.民法總論(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0.
[6]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北京:三聯書店,1997:61.
[7]嚴金泉.組、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博弈理論與經驗解釋——以福建、江西兩省31村為例[J].中國土地科學,2000,14(5):10-14.
[8]彼德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