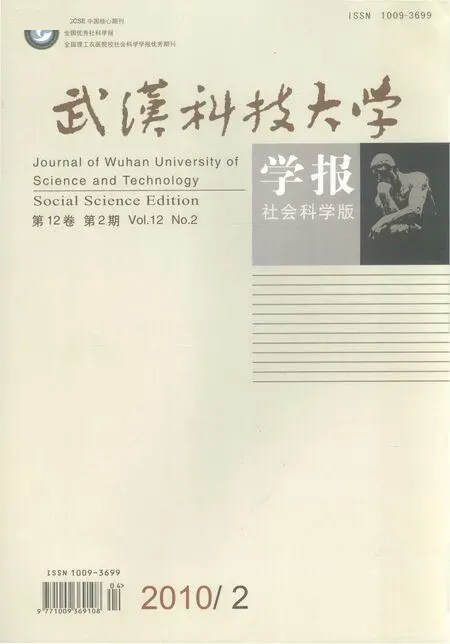重審《精神現象學》的開端——共相能否在“辨證”中吞沒感性?
劉貴祥
(1.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甘肅蘭州 730000;2.中山大學哲學系,廣東廣州510275)
《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哲學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馬克思曾指出《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從“感性確定性:這一個和意謂”的辯證分析入手開始哲學的精神之旅,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黑格爾對“感性確定性”的辯證分析構成黑格爾哲學體系“開端的開端”和“秘密的秘密”。可見,重新考查《精神現象學》的開端,辨明黑格爾對“感性確定性”的辯證分析,探求黑格爾哲學的隱性立場和基本傾向,并呈現黑格爾哲學在他的批判者和現代哲學參照下的得失意義重大。
一、《邏輯學》開端與《精神現象學》開端的比較
黑格爾哲學體系以《邏輯學》為開端。《邏輯學》則以“純有”為開端。“有”、“無”、“變”構成黑格爾《邏輯學》中的第一個三段式,也構成黑格爾哲學大廈的第一塊磚。關于黑格爾哲學的“純有”是什么,為什么要以“純有”為開端,哲學史上有各種各樣的觀點和爭論,但是不管這些觀點差別多大,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就是《邏輯學》必須從最純粹和最普遍的東西開始。在《邏輯學》中,“純有”即是純思維,哲學必須以純思維為對象和開端,并且必須要擺脫一切歷史的外在性和偶然性。“在哲學歷史上所表述的思維進展的過程,也同樣是在哲學本身里所表述的思維進展的過程,不過在哲學本身里,它是擺脫了那歷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純粹從思維的本質去發揮思維進展的邏輯過程罷了”[1]。可見,“純有”作為《邏輯學》的開端,它同時也是《邏輯學》中所出現的第一個絕對知識,它必須要上升到純粹思維的層次并擺脫一切“歷史的外在性和偶然性”,才能夠探討“存在”這樣的哲學問題。
和邏輯學不同,《精神現象學》以“感性確定性”為開端。關于這一點,黑格爾說得很明白:“那最初或者直接是我們的對象的知識,不外那本身是直接的知識,亦即對于直接的或者現存著的東西的知識。我們對待它也同樣必須采取直接的或者接納的態度,因此對于這種知識,必須只像它所呈現給我們的那樣,不加改變,并且不讓在這種認識中夾雜有概念的把握。”[2]63這種不夾雜概念把握的認識就是感性確定性。感性確定性的德文表達是“ die sinnliche Gewissheit”,英文的表達是“sense-certainty”,漢語的翻譯是“感性確定性”。需要指出的是,感性確定性的表達在漢語中極容易引起誤解,讓人以為黑格爾要肯定的是感性本身的“確定性”,但是黑格爾的意圖恰好相反,他認為感性雖然是無可懷疑的,但是知識的真理不在感性的易變性本身,而在如何用共相把它固定下來這一點上。正因為如此,有人主張“die sinnli-che Gewissheit”應譯為“感性的確知”,而不是感性確定性[3],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再以英文的表達為例,黑格爾要表達的這層意思同樣也是很明顯的。如Donald Phillip Verene在《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導言》一文中就指出,黑格爾“sense-certainty”的含義“不僅是指有一個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個世界如何被確知”[4]。英語對“die sinnliche Gewissheit”的翻譯在這里雖然也是二手語言,但是它表達“感性如何被確知”這一點上比漢語貼近得多。當然,本文仍然僅限于突出這一含義,這一術語的使用仍然沿用“感性確定性”。
黑格爾對《邏輯學》的基本定位是“純粹從思維的本質去發揮思維進展的邏輯過程”,而對《精神現象學》的基本定位則是“意識的經驗科學”。意識的經驗科學目的是探討真正的知識,“這部《精神現象學》所描述的,就是一般的科學或知識的這個形成過程。最初的知識或直接的精神,是沒有精神的東西,是感性的意識。為了成為真正的知識,或者說,為了產生科學的因素,產生科學的純粹概念,最初的知識必須經歷一段艱苦而漫長的道路”[2]17。從這句話可以看出,黑格爾探求的真正目的是概念的認識,因為只有概念的認識才算得上真正的知識。但要達到概念認識,不經歷艱苦而漫長的道路是不可能的。當然,《邏輯學》沒有這段艱苦而漫長的道路的探索,也無法真正開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才說《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精神現象學》是以偉大的歷史感為基礎的。
概而言之,《精神現象學》的末端構成《邏輯學》的起點。但遺憾的是,在《邏輯學》中,黑格爾認為,為了討論純存在,《邏輯學》的這個前提是應該忘記的。至少應該忘記精神現象的這種意識的經驗形式,而讓它里面孕育出來這種絕對知識以純粹的方式不受束縛地發展起來。“彷佛一切過去的東西對于它來說都已經喪失凈盡,而且視乎它從以前各個精神的經驗中什么也都沒學習到”[5]。顯然,在知識論的傳統中,從追求思維的純粹性這一點上來說,黑格爾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問題是黑格爾為了“產生科學的純粹概念”想要完全忘記純粹概念粗糙的出生地,這一做法究竟是不是可能的?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哲學的抽象意識雖然和最初的感性意識不同,但是感性意識作為抽象意識的真正發源地,抽象意識不可能完全脫離感性意識獨立存在,而且感性意識的豐富性和多樣性還具有各種發展的多重向度,不能完全被抽象的理性思維所吞沒。但是,眾所周知,黑格爾卻在隨后對“感性確定性”的辯證分析中,最終用“純粹思維”把感性意識完全清洗和吞沒了。黑格爾怎么做到這一點的呢?總體上說,這正是黑格爾思維辯證法的秘密。
所以,若把《邏輯學》的開端與《精神現象學》的開端作一比較,前者從“純有”開始,后者從“感性確定性”開始只是表面的不同,實質上二者在思維方式的運用上是一樣的。差別只是《邏輯學》的開端更純粹,而《精神現象學》不得不從“感性確定性”開始。這樣一來,黑格爾對“感性確定性”的辯證分析就成為黑格爾哲學的真正秘密。
二、黑格爾對“感性確定性”的辯證分析及其隱性立場
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通過對感性確定性的辯證分析,描述出了個體意識由感性確定性到絕對知識的發展過程,最終把意謂完全納入了共相。黑格爾對感性確定性的辯證分析方法蘊含著黑格爾哲學方法論一以貫之的基本原則。黑格爾正是在思維的“辯證”中用共相把意謂最終吞沒。可以說《精神現象學》的開端運用的方法是黑格爾哲學體系的“最小公分母”。黑格爾完成這一點通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讓考察對象和考察尺度合一
現象學以意識發展史為考察對象,但考察尺度本身又是意識發展史完成了的結果,即絕對精神(實質上還是意識本身)。這樣考察對象即是考察尺度,差別只是這個考察對象有待展開自身而已。“感性確定性的這種具體內容使得它立刻顯得好像是最豐富的知識,甚至是一種無限豐富的知識……此外感性確定性又好像是最真實的知識;因為它對于對象還沒有省略掉任何東西,而讓對象整個地、完整地呈現在它面前。但是,事實上,這種確定性所提供的也可以說是最抽象、最貧乏的真理。它對于它所知道的僅僅說出了這么多:它存在著。而它的真理性僅僅包含著事情的存在”[2]63。站在知識論的立場上,黑格爾可以把“感性確定性”當成“純存在”,但這個“純存在”并不具有什么獨立自存的意義,它一定會被更高層次的知識所代替。所以,感性的確定性最終要被理性的確定性所代替,直到感性確定性發展出絕對知識為止,就此而言,感性確定性是確證意識發展的一個環節。因此,總觀《精神現象學》的目的,表面上看,黑格爾對人類意識發展史在作完全客觀的描述,實質上黑格爾的描述已經先以人類普遍意識的發展程度為前提了。
在這里,我們似乎看到了黑格爾《邏輯學》中開端的影子。事實上正像前面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精神現象學》中以萌芽和潛能的方式,包含了他后來整個體系抽象思維的原型。“感性確定性”正是《邏輯學》中“純有”的影子和原型。這是黑格爾將哲學的開端理解為圓圈的必然結果。《邏輯學》的機制本質上是一種在思維內部“永不停息的循環”,它本質上是由近代意識哲學這個隱性立場提供的。差別只在于,《精神現象學》走的是上升的道路,用的是分析的辦法;《邏輯學》走的是下降的道路,用的是綜合的辦法。“在這個意義上,《精神現象學》一方面被看作一條達到真正科學的道路,一個‘純粹知識’的形成過程;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已經完成的‘絕對知識’在回憶它自身走過的歷程”[6]175,這個歷程本質上就是感性確定性被完全納入認識共相的過程。
(二)用抽象思維冒充感性,然后用共相吞沒意謂
黑格爾實現這一點通過兩個步驟。第一,把《精神現象學》的走完全程后人類思維的普遍性實體化,即變為絕對精神。這一點用黑格爾的話說就是,共相是感性確定性的真理。只不過感性確定性作為思維的萌芽,它作為最直接、最抽象的真理性還有待展開自身為共相。“被宣稱為感性確定性的真理性的這種純有,如果我們試仔細看一下,就可以看出在這種純有中還包含著更多的別的東西……即在這種直接感性確定性里純有立刻就分裂為前面已提到的兩個‘這一個’:作為自我的這一個和作為對象的這一個”[2]64。這句話中的“我們”相當重要。黑格爾考察的對象是意識的發展史,尤其是個人意識的發展史,那么,考察尺度只有在意識發展走完它的全程時才能出現。但是,現在在這里意識發展史尚待展開,卻已經先行出現了“我們”這個先在的思想尺度。那么這個先在的思想尺度是什么呢?其實就是無人身的抽象思維本身,即馬克思所言:“舉止如此奇妙而怪誕、使黑格爾分子傷透了腦筋,這整個觀念,無非始終是抽象,即抽象思維者。”[7]334這個“無臉、無牙、無耳、無一切的抽象思維”,可見正是黑格爾哲學的秘密所在。第二,絕對精神在反觀自己的來歷中,把感性和感性的對象分割開來,讓主體和思維分離。這樣,最初作為實實在在的感性確定性就失去了對象,只有脫去對象這一雜質的束縛,感性才可能上升到絕對精神。黑格爾正是借助這個抽象的普遍意識,他才能把感性確定性看作是“自我”這一個和“對象”這一個的對立。可見這個冒名為“我們”的普遍思維其實正是黑格爾的“絕對觀念”。這個絕對觀念作為思維著的精神,“匯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也就是說:“意識——作為知識的知識——作為思維的思維——直接地冒充為它自身的他物,冒充為感性、現實、生命。”[7]328這樣一來,感性、意謂就被完全納入共相。感性和意謂一旦被納入共相本身,黑格爾就可以任他的理性思維之馬自由馳騁。本來,感性確定性作為意謂,是人和世界上手時的源初狀態,它是“前邏輯的”。但是,當感性確定性被看作是還有待上升和展開的抽象性和直接性時,感性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及意謂的不可表達性被狹窄化。它的豐富性和不確定性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從感性確定性上升為共相和普遍性。這樣,當感性確定性走完全程反觀自身時,意謂乃是被完全納入認識的共相本身。這是一條從笛卡爾開始一直到黑格爾為止求“我思”的道路。
(三)利用語言對實在的顛倒功能
在感性確定性內部,作為對象的這一個和作為自我的這一個還是抽象的相互獨立。當我們用語言說出意謂是“這一個”時,我們同時是把“這一個”當作普遍的東西來說的。這樣一來,意謂的“這一個”已經變成了“另一個”,而保存下來的是作為抽象共相的“這一個”。這樣一來,認識和對象、語言與實在原先的關系就顛倒過來了。“語言是較真實的東西:在語言中我們自己直接否定了我們的意謂;并且既然共相是感性確定性的真理,而語言僅僅表達這種真理,所以要我們把我們所意謂的一個感性存在用語言說出來是完全不可能的”[2]66。正因為如此,感性確定性的真理性轉變為共相和語言的真理性。“因為那感性的‘這一個’是語言所不能到達的,而語言是屬于意識范圍,亦即屬于本身是共相或普遍性的范圍”[2]72。語言和實在本身存在著一種矛盾,語言不可能完全窮盡實在。但是,黑格爾理性主義的哲學立場則把語言作為概念和共相的本性泛化和神圣化了:“語言具有這樣的神圣性質,即它能夠直接地把意謂顛倒過來,使它變成某種別的東西(即共相),因而使意謂根本不能用語言來表達。”[2]73意謂真的根本不能用語言來表達嗎?不是。原則上,意謂并不是“不可言說的”,而只是語言是“不可窮盡”的。事實上,語言除了有普遍的規范作用以外,它本身就是人們情感和生存狀態的原初表達。但是,在黑格爾看來,語言的最主要功能在于它的普遍的規范性和可傳達性,至于語言的模糊性和對情感的表達性,語言的這些“雜質”對概念思維來說恰恰是要清洗掉的。這樣一來,黑格爾就不給概念思維以外通達世界的方式留下任何余地,感性確定性最終失去了一切合法性。黑格爾“將感性活動所獲得的豐富意謂揚棄和消融在抽象意識的概念、共相之中,將一切不可說的東西(或不如說:不可規范、不可窮盡的東西)在科學和理性的蒸餾器中蒸發掉——這就是思辨哲學的秘密”[6]160。
概而言之,《精神現象學》雖然以感性確定性為開端,但是由于黑格爾仍處在近代哲學知識論的傳統中,以意識哲學為其隱性立場,所以抽象思維的運動最終在概念的辯證法中用共相吞沒了感性。海德格爾后來對近代意識哲學的這種內在運行機制有著深刻的揭示:“只要人們從Ego cogito(我思)出發,便根本無法再來貫穿對象領域;因為根據我思的基本建制,它根本沒有某物得以進出的窗戶。就此而言,我思是一個封閉的區域。‘從’該封閉的區域‘出來’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必須從某種與我思不同的東西出發。”[8]由此可見,從理性思辨專制下拯救出人的感性,重新確立感性本身的合法地位,就成為黑格爾哲學以后的主要任務。
三、從兩個不同路向看感性的重新確立
馬克思在1841年的博士論文中曾稱黑格爾哲學是“普照的太陽”,但是,隨著黑格爾的逝世,這一“普照的太陽落山了”。卡爾·洛維特后來在回顧和總結黑格爾逝世12年以后新哲學的發展狀況時說:“恰好是1843年這一年決定了以后一百年哲學的命運,這一命運現在才又變得可見了。在這同一年里發表了費爾巴哈的《未來哲學原理》,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克爾凱郭爾的《非此即彼》。這些19世紀的最后一批亦或是第一批哲學家們想理解從現實得出的共同原則,不再是一種純粹的‘意識’或一種純粹的‘理性’或一種絕對‘精神’,而是處在赤裸裸的存在當中的人本身。”[9]29洛維特的這一概括非常準確。黑格爾哲學以后,對感性的肯定重新沿著兩個基本路向展開。一個是在非理性主義哲學那里得到肯定;另一個是在馬克思所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那里得到肯定。在前一種路向上,克爾凱郭爾、叔本華和尼采是典型代表;在后一種路向上,費爾巴哈和馬克思是典型代表。
首先,看以克爾凱郭爾為首所代表的非理性趨向。克爾凱郭爾對黑格爾哲學的反抗主要是兩方面,一是批判黑格爾哲學體系的思辨化傾向,譴責他把哲學和宗教結合的泛神論做法;二是突出個人面對虛無的絕望和生存狀態,用生活的辯證法對抗黑格爾思維的辯證法。就克爾凱郭爾哲學來說,他的焦點始終是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選擇。所以,在此意義上,他通常被看作是第一個存在主義哲學家。
至于叔本華,眾所周知他是第一個在黑格爾活著時公開和黑格爾對抗的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認為,作為世界本體的是意志。世界根本不是什么絕對精神的外化和展開,而是意志盲目沖突的結果。至于人的認識,叔本華認同康德的批判哲學,認為直觀是世界的真理,表象不過是意志的客體化。那種認為認識是第一性的,意志是第二性的觀點是把事情搞反了。“從我全部的基本觀點看來,這一切說法都是把實際的關系弄顛倒了。意志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認識是后來附加的,是作為意志現象的工具而隸屬于意志現象的”[10]。這樣被黑格爾哲學忽視和打發掉的感性又作為人的生命活動被肯定下來。
叔本華的悲意志論哲學深深地影響了尼采,尼采從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中走出來后形成了自己的“強力意志”學說。尼采明確肯定生命意志的積極方面和對理性認識的基礎地位。尼采認為酒神精神和悲劇哲學就是對生命意志的最大張揚,理性認識只不過是強力意志更好地實現的手段而已。“對痛苦本身的肯定,對生命本身一切疑問和陌生東西的肯定……這種最后的、最歡樂的、熱情洋溢的生命肯定,不僅是至上的認識,同時也是為真理和科學所嚴格證實的認識,并且成了科學和真理的基礎”[11]。
其次,再看以費爾巴哈和馬克思為代表的歷史唯物主義。正如上文洛維特所說,費爾巴哈哲學的貢獻就在于用“感性直觀”取代黑格爾的“理性思辨”。由于費爾巴哈重新把感性和感性意識理解為人的實在性及其最后確證,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費爾巴哈在哲學上是一種感覺論和經驗論的唯物主義的恢復。在費爾巴哈那里,所謂的感性,首先是指對象在感覺之外存在,同時也是在語言和思維之外存在。費爾巴哈說:“這種感性的、個別的存在的實在性,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用我們的鮮血來打圖章擔保的真理。”[12]68這就是說,在費爾巴哈那里,感性意識表明的就是感性存在,這幾乎是一個自明的真理。費爾巴哈認為,黑格爾以語言為共相對感性意識的吞沒應該重新被顛倒過來:對于感性意識來說,一切語詞都不過是專名(Nomina proria),是意識的符號,因此,“對于感性意識來說,語言正是不實在的東西,虛無的東西”[12]68。黑格爾之所以根據語言否定感性確定性,那是因為黑格爾并沒有深入地考察過感性意識本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評價費爾巴哈的哲學貢獻主要在于“直截了當地使唯物主義重新登上了王座”[13]。
但是,由于費爾巴哈哲學過分注重直觀和自然,因此他的哲學缺陷不但不能從根本上克服黑格爾哲學缺陷,而且還從根本上放棄了黑格爾哲學能動的方面,尤其是黑格爾“實體即主體”的思想和否定性的辯證法。這樣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和缺陷克服之路就只走了一半。費爾巴哈哲學的缺陷被馬克思所克服,馬克思說:“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14]54后來,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更進一步指出:“費爾巴哈比‘純粹的‘唯物主義者有很大的優點:他承認人也是‘感性對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對象’,而不是‘感性活動’。”[14]78費爾巴哈的直觀唯物主義最終被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所代替。這樣,費爾巴哈構成了黑格爾和馬克思之間過渡的中介。馬克思最終用“感性活動”取代了費爾巴哈的“感性直觀”。
總之,黑格爾哲學以后,理性的至上性和絕對性的地位被動搖了。正如洛維特所說,以上兩種反對黑格爾哲學的路向雖然不同,但他們都開始從“處在赤裸裸的存在當中的人本身”出發。這是黑格爾以后這些學說具有的一個“統一的基本特征”,即“這個基本特征也因此貫穿在他們對黑格爾的純粹‘思維’的三重批判中,這種批判是在給‘激情’(克爾凱郭爾)、‘感性直觀’和‘感覺’(費爾巴哈)、‘感性活動’或者‘實踐’(馬克思)恢復名譽的旗號下進行的”[9]29。這就是說,黑格爾以后,哲學雖然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發展路向,但共同點都已和近代意識哲學的知識論的傳統不同。具體說,以上這兩種新路向已經共同代表了一種“生存哲學”的新路向。
[1] 黑格爾.小邏輯[M].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55.
[2]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上卷[M].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3] 羅伯中.論黑格爾的感性確知概念[J].學術研究,2006(3).
[4] Donald Phillip Verene.Hegel’s absolute :an introduction to reading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44.
[5]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M].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274.
[6] 鄧曉芒.思辨的張力[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7]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晚期海德格爾的三天討論班紀要[C].丁耘,譯.哲學譯叢,2001(3):55.
[9] 卡爾·洛維特.克爾凱郭爾與尼采[C].李理,譯.哲學譯叢,2001(1).
[10] 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沖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401.
[11] 尼采.看哪這人:尼采自述[M].張念東,凌素心,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69.
[12] 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上卷[M].榮震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13]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2.
[14]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