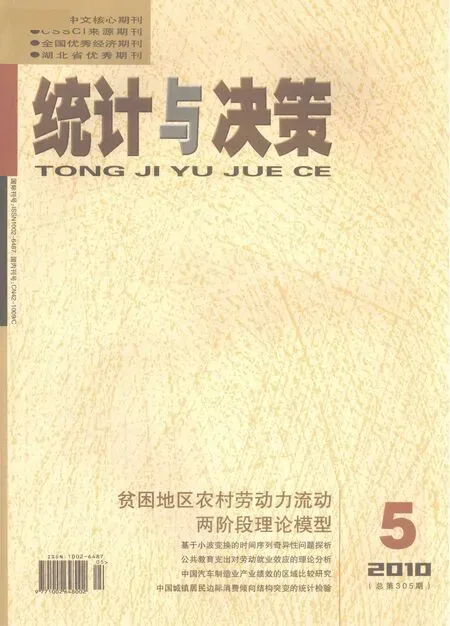西部地區民間資本投資差異分析
楊天榮,陸 遷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楊凌 712100)
1 西部各省(市、自治區)民間資本投資總額差異比較
我國西部地區特指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四川、重慶、云南、貴州、西藏、廣西、內蒙古12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本文民間資本是指集體、個體、聯營、其他經濟、以及聯營經濟和股份制經濟中非國有控股經濟成份的投資總和。鑒于民間資本指標并不是一個標準的統計分類,只是在分析民間投資問題時使用,其投資數據不能從統計年鑒中直接獲得,因此可采用全社會投資減國有及國有控股投資,再減去外商及港澳臺投資的方法以獲得民間資本投資數據[1][2]。受數據收集約束,民間資本僅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構成部分,原始數據分別來自1997~2007年間的中國統計年鑒。
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后,其投資增長幅度很大。相比較而言,四川民間資本投資額一直遙遙領先,投資規模最大,且歷年來均保持首位。1997年,其民間資本投資額為376.31億元,2007年則達到3451億元,是1997年的9倍。民間資本投資額增長最顯著的是內蒙古,1997年為78.65億元,名列西部地區第7位,1998年、1999年上升為第六位,2003年又升到第三位,2004~2007年則一直保持第二位,2007年其民間資本投資額達到2555億元,是1997年的32.4倍。民間資本投資的迅猛增長有力地推動了內蒙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2004年其生產總值增長率為20.9%,2005年為23.8%,不僅是西部第一,而且是全國第一,2007年雖為19.1%,但仍是全國第一。民間資本投資總額排在西部地區后面的是甘肅、寧夏、青海、西藏,但上述地區民間資本投資額也同樣出現大幅增長,2007年其民間資本投資總額分別是1997年的9.7、18.1、22.7、34.5倍,西藏地區因為基數太小,所以在西部增長倍數最大。
2 西部各省(市、自治區)民間資本投資增速比較
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對西部民間資本投資推動力很大,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云南、陜西、寧夏等七個地區在2001~2003年間民間資本投資均表現出連續高速增長,2003年內蒙古增長率達到66%,寧夏達到70%,重慶達到44%。貴州則在2004~2006年間表現出連續增長,2006年其投資增長率為43%。然而,西部各地區民間資本增長率均呈現出波動性特點,內蒙古自2005年開始下滑,2007年跌落到26%,其他地區則呈現出一年低、一年高態勢。西藏民間資本投資增長率則表現出一定的極端性,最高增長率為117%、最低增長率為-40%,極值幅最大。
1997~2007年間,西部各地區民間資本投資平均增速從高到低依次為西藏42.5%、內蒙古41.6%、寧夏36.1%、青海33.6%、新疆30.3%、重慶28.4%、貴州 27.8%、陜西 27.8%、甘肅25.6%、四川24.8%、廣西23.4%、云南23.3%。西藏、內蒙古、寧夏、青海、新疆平均增速高是因為其民間資本基數小,四川、廣西偏低是因為其民間資本基數大,因此平均增速并不能完全反映各地區民間資本發展優劣。
西部各地區民間資本投資增長率總體上呈現不規則性,各地區增長速度基本上均為波浪式發展態勢,增速表現出不穩定性,尤其是西藏。西部尚處在大開發戰略第一階段,民間投資的不穩定性及2008年經濟危機對民間資本投資影響的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對西部經濟發展構成了威脅,西部各地區需采取應對措施以保持經濟健康發展。
3 西部各省(市、自治區)民間資本投資比重比較
3.1 各省(市、自治區)民間資本所占西部民間資本比重
西部地區中,四川對民間資本投資具有較強吸引力,歷年來民間資本投資額占西部總民間資本比例最大,平均值達到26%,集中了1/4以上的西部民間資本。其次民間資本所占比重平均較大的是重慶12%、廣西11%、云南10%、陜西10%、內蒙古9%。民間資本比重排在后六位的是新疆8%、貴州5%、甘肅4%、寧夏2.3%、青海1.7%、西藏0.2%,這六地區的民間資本投資比重之和為21.6%,還不及四川一個省的民間資本投資所占比重。
從比重發展趨勢看,四川、重慶、陜西所占比重較穩定,廣西、云南呈現一定波動性,內蒙古雖然平均比重排在第六位,但自2002年后其比重連續上升,2007年民間資本已占西部民間投資額的16%,是1997年的2.7倍,為西部增長最快地區。西藏民間資本所占比重非常小,平均比重僅為0.2%,這與其偏遠地理位置、特殊氣候環境、不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有較大關系,但自2004年以來,其比重連續上升,2007年已達到0.62%,這與青藏鐵路開通后運輸條件得到改善有直接關系。
西部大開發以來,西部地區間民間資本投資規模差距已經拉開,其一方面與各省(市、自治區)經濟體大小有關,另一方面也說明各地區投資環境有較大差別,民間資本比重較小的各地區應充分發揮地區比較優勢,進行特色產業開發,拓展民間資本進入領域,使經濟發展充滿活力。
3.2 各省(市、自治區)民間資本所占其總投資額比重
民間資本所占比重的地區間橫向比較不能完全反映某地區民間資本發展狀況,一個地區人口多少,區域地理位置等因素影響著民間資本吸納總量,但是一個地區民間資本占其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自身縱向比較卻能反映出該地區在吸引民間資本方面所做的努力,及該地區未來吸引民間資本的潛力。西部12省、直轄市、自治區自西部大開發以來,民間資本得到了長足發展,其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比重均呈上升趨勢。2001年四川民間資本投資額占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比例首次過半,2003年重慶、寧夏兩地區民間資本投資比重也逾半。2004年共有四川、重慶、廣西、云南、內蒙古、寧夏、新疆等七個地區民間資本投資比重超過50%,尤其是寧夏,其比重達到了62.7%,2007年又上升到67.3%,而1997年其比重僅為22%,說明寧夏在西部大開發過程中,思想解放,改革力度大,民間資本投資活躍,使民營經濟充滿活力。2004年西部區域民間資本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也到達54%,標志著西部地區以民間資本為投資主導格局的形成。2007年西部只有甘肅、西藏兩地區的民間資本投資比重未達到50%,不過,兩地區同樣取得了較大進步,1997年,西藏民間資本占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比重僅為8%,2007年已達到37.2%。
4 西部各省(市、自治區)民間資本投資效率比較
4.1 民間資本對總投資的貢獻率
民間資本對總投資貢獻率[3]=(當年民間投資增長率/當年總投資增長率)×(上年民間投資總額/上年投資總額)=△民間投資/△總投資×100%
根據1997~2007年西部各地區民間資本投資額和總投資額計算的民間資本對總投資貢獻率分析,民間資本對總投資增長貢獻率波動較大,1998~2007年間,各地區均呈現不平穩發展態勢,一些地區甚至出現大起大落。其中重慶在1999年出現峰值103%后開始下滑,并在小幅度范圍內保持波動,到2006年又一次出現峰值105%。四川于1999年達到峰值110%,其后便呈現遞減態勢,而新疆在1999、2000年達到高峰值198%、193%后也開始下滑。寧夏2004年達到高峰值132%,2005年僅為5%,2006年又猛然回升到115%。民間資本對總投資增長貢獻的波動性,使得對其投資效率預測變得困難。不過,從發展趨勢看,2004年以后各地區民間資本投資貢獻率均為正值,且2007年均達到50%以上,說明民間資本已經成為推動地區總投資增長的主要力量。
4.2 民間資本對GDP的貢獻率
民間資本對 GDP貢獻率=△民間資本投資/△GDP×100%
根據1997~2007年西部各地區民間資本投資額和GDP計算的民間資本對GDP貢獻率結果分析,西部各地區民間資本對GDP貢獻率在各年間同樣呈現波動性,內蒙古在2002~2006年間連續增長后,2007年開始回落;四川2004年之后的貢獻率明顯減小;重慶2000~2005年間處于小幅波動中,2006年則突然上揚到129%,2007年又跌落下來;寧夏民間資本對GDP貢獻率1999年為120%、青海2000年為119%,但之后兩地區又處于低位波動中,且2005年寧夏僅為5%。同一年度,各地區間民間資本對GDP貢獻率差異也非常顯著,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極值差很大,但自2004年之后,差異開始縮小,2007年,重慶貢獻率稍微偏高,為71%,其他地區基本在40%~60%范圍內,這說明各地區民間資本對GDP貢獻率差異呈收斂趨勢。
5 結語
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后,中國區域政策已有過去的注重效率和增長目標逐步轉移到注重公平目標,然而由于這種戰略轉變時間不長,加之西部各地區地理區位、基礎設施、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等自身因素制約,西部各地區間民間資本投資存在較大差距,并呈現出梯隊發展狀態。從規模上看四川、內蒙、重慶、廣西民間資本投資額最多,尤其是內蒙,投資額增加幅度、投資增長速度非常顯著。陜西、云南、新疆、貴州處于第二梯隊,民間資本發展基本穩定,其中新疆相對增速較快。甘肅、青海、寧夏、西藏屬于民間資本規模利用最小地區,其中寧夏民間資本投資占總投資額比重較高、增速也非常快,呈現出良好健康發展態勢。但是,西部各地區民間資本對總投資及GDP的貢獻率均呈現較大波動性,表明西部地區民間資本投資效率不穩定,其長期發展趨勢難以預測,使得地區經濟增長充滿著不確定性。
西部各地區不僅要和東部、中部展開競爭,其區域內部同樣需要展開競爭,各地區應改善投資環境、充分利用地區優勢資源進行特色產業生產,以吸引民間資本投入、提高民間資本投資效率、促進地區經濟增長。內蒙古利用草原資源、重點發展畜牧業、奶業使民間資本投資規模迅速壯大就是一個成功發展的典范。
[1]汲鳳翔.民間投資的概念和統計方法[J].北京統計,2002,(15).
[2]邱元直.對我國民間投資增長的實證分析[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3)1.
[3]應雄.中國民間投資問題研究[D].廈門: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