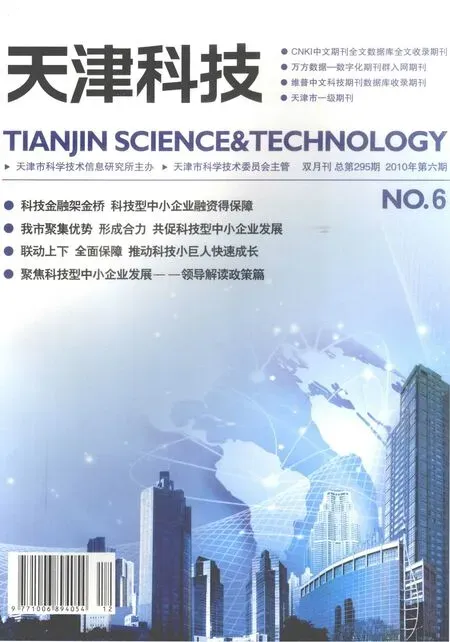對水利水電工程環保驗收調查中若干問題的探討
王臨清 (環境保護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 北京100012)
付鵬 (松遼水利委員會水文局信息中心 長春130021)
對水利水電工程環保驗收調查中若干問題的探討
王臨清 (環境保護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 北京100012)
付鵬 (松遼水利委員會水文局信息中心 長春130021)
總結在水利水電工程竣工環保驗收調查中發現的工程環保措施落實不到位、措施缺失或不明確、措施受制于權限,以及施工期環保措施落實不足等一系列環保問題;從“三同時”制度的執行、流域統一規劃的實施以及跟蹤監控機制的有效執行等方面,分析了水利水電工程竣工環保驗收調查過程中上述環保措施落實不到位等問題的原因;從流域開發整體高度和政策制度層面提出制定河流生態用水配套法律法規,強化“三同時”全過程管理,嚴格執行流域規劃環評,盡快實行環境監理制度以及開展環境影響后評價等對策建議。
水利水電 環保驗收 對策建議
水電是我國第一大清潔能源,其開發利用已有百余年歷史。與其他能源相比,水電具有可循環利用、長期成本低、綜合效益大等優勢,對改善能源結構、減排溫室氣體、保障能源安全和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然而,隨著水利水電工程的大規模開發建設,一系列生態問題開始陸續顯現。對此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給予了高度重視,并在環評階段從流域開發整體高度和項目建設可能存在的環境影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生態保護、減緩和補償措施及污染防治措施。工程竣工環保驗收調查結果表明,絕大多數環評及其批復要求得以落實,取得了預期的環境保護效果。但調查中也發現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工程實際建設、運行中由于種種原因未落實或落實不到位,帶來了不利的環境影響。本文結合近幾年水利水電工程竣工環保驗收調查工作中常見的幾類問題進行探討。
1 驗收中發現的問題
1.1 環保措施明確但落實不到位
環評及批復提出了明確的環保措施但落實不到位,影響較明顯的尤以生態基流保障措施最為突出。水利水電工程的建設會造成壩下部分河段減水甚至脫水,尤其是引水式電站。為減緩工程建設對壩下生態環境的影響,環評階段一般均提出最小下泄生態流量(生態基流)保障措施,以滿足下游生態等用水的基本要求。原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發改委聯合下發的《關于加強水電建設環境保護工作的通知》(環發[2005]13號)中也明確指出:“要根據用電、用水和生態環境等方面的要求,研究制定電站優化運行方式,最大限度地減輕對水環境的影響。對于引水式等水電開發方式,應避免電站運行造成局部河段脫水,落實泄水建筑物建設和運行,確保下泄一定的生態流量。”然而實際驗收調查中發現,許多工程存在無法保障持續下泄生態流量的情況。
例如:某引水式水利樞紐在工程環評階段提出最小下泄生態流量要求,并通過壩體灌溉洞予以保證放流。驗收調查時發現,由于下游無灌溉需求,工程實施中進行了設計變更,取消了灌溉洞只留泄洪洞,根本無法按要求下泄生態基流。工程運行后造成壩下近12 km長的河段減脫水,其中約4 km河段處于完全脫水狀態,致使該河段內水量僅靠2條小支流匯入及電站尾水上溯補充,對水生生態造成了嚴重的影響。類似這樣的情形,驗收調查時已很難提出切實可行的補救措施。再如河床式電站,河床式電站在持續發電狀態下一般不會引起壩下脫水,但水文情勢的改變依然會對下游生態環境帶來不利影響。驗收調查中多數工程屬于調峰電站,壩下間斷放流,實際中極少在不發電時根據環評要求持續下泄生態流量,因此造成河流部分時段的減脫水。這主要是由于電站的運行調度方案中缺少生態流量調度方案造成的。
1.2 環保措施缺失或不明確
部分環評較早的工程,由于當時認識的不足,個別環保措施缺失。某工程環評階段未提出下泄生態流量保障措施,造成壩下斷流。驗收調查單位為減緩對下游生態環境的影響,提出“從水庫提水下泄生態流量”的補救措施。該措施在理論上可行,然而在實踐中受運行調度方案和監管措施的限制,實施困難。
另外,環評階段措施不明確不具體,也是造成環保措施落實不到位的重要原因。例如對新疆特有的胡楊林等河谷林,洪水是其自然繁育、漂種的重要環境因素,水利水電工程的建設改變了下游河道天然的洪峰過程,會導致河谷林的衰敗。有的環評中只簡單提到“采用人造洪峰,減緩河谷林衰敗”,并未提出具體的洪峰流量和下泄過程等。
1.3 環保措施受制于權限
水利水電工程影響范圍廣,因此制定流域性保護措施非常必要。但若具體到某項工程,建設單位往往受制于管理權限,難以落實這些措施。例如:某水電工程在環評中提出“切實抓緊落實雅河上游細鱗鮭魚保護區、回龍山壩下魚(鰲花魚)保護區,以及制定恢復喇蛄資源的相關計劃”的流域性保護措施。[1]經驗收調查,環評中提到的以上兩個保護區均未建立,也未制定相關的資源恢復計劃。所以說,沒有流域管理部門的配合,很難通過單項工程的環保驗收落實流域性保護措施。
又如,面源污染是庫區的重要污染源,也是庫區水體富營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環評要求庫區一定范圍內退耕還草還林,是解決面源污染的重要措施,但該措施必須在整體流域污染控制中得以實施。建設運行單位管理范圍有限,這些措施的全面實施也受到制約。
1.4 施工期環保措施落實不足
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周期長,污染影響主要發生在施工期。所以,施工期環境保護和監測尤為重要。而驗收調查中發現,建設單位真正按環評要求落實環境監測計劃的少之又少。尤其在目前環境監理還處于試點階段的情況下,水利水電工程施工期缺乏有效監督,施工期環境影響調查缺乏有效的資料數據。
另外,水利水電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一個漸變、長期、累積的過程,驗收階段一般在工程試運行一年左右,一些生態影響還未顯現。僅通過驗收階段的監測和調查,難以反映工程對生態環境的長期累積影響和變化趨勢。
2 原因分析
2.1 “三同時”制度執行不完善
“三同時”制度是建設項目環境管理的一項基本制度,是我國以預防為主的環境保護政策的重要體現,是落實環評措施和要求的有力保障。但實際中“三同時”制度執行有時還不夠完善,尤其是“同時設計”階段缺乏有效的監管,致使個別重要的環保設施(措施)在設計階段就未能體現,如未按要求設計生態流量通道或電站運行調度方案中缺少生態流量調度方案等等,均會導致生態基流保障措施無法實施。
另外,對環境保護工作重視不夠也是造成部分環保措施落實不到位的重要原因,一些單位把項目環評僅作為上項目的一張通行證,取得批復后即束之高閣,至于如何落實往往不再問津。[2]
2.2 缺乏流域統一規劃
河流水能開發必須與流域綜合治理規劃相適應,與水資源保護、生態保護、水土保持等規劃相協調。流域性保護措施是流域規劃環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在流域規劃實施過程中落實的措施,而當時流域規劃環評工作還未開展或處于初期,一些流域性的保護措施依靠單個項目無法完成。近年來,環境保護主管部門重視規劃環評的開展和推廣,規劃環評試點工作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仍然存在不進行流域規劃環評,或為了上項目而補做規劃環評的現象,致使應該在流域規劃中實施的環保措施無法得以落實。
2.3 缺乏有效的跟蹤監控機制
驗收調查發現,目前已驗收的水利水電項目中,絕大多數未開展施工期環境監理工作。因此施工期缺乏有效的跟蹤監管機制,致使施工期環保措施和環境監測計劃落實不足;個別實施了環境監理的水利水電工程,也由于監理人員缺乏系統培訓、介入時間偏晚、環境監理制度不完善等原因,未能充分發揮環境監理的作用。
3 對策建議
3.1 制定河流生態用水配套法律法規
以法律手段強制執行生態用水措施。制定和完善與河流生態用水相配套的相關法律法規,將保障生態用水納入法制軌道,構建生態用水的法律保障體系,是引導社會和建設單位重視生態流量、預防和懲治侵占生態用水行為的必要手段。
3.2 強化“三同時”全過程管理
強化建設項目環境保護“三同時”全過程管理制度是落實環評措施和批復要求的有力保障。環境保護部也不斷加強建設項目竣工環保驗收工作,并開展了建設項目環境監理試點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設計階段的監管有待于進一步加強。建議環境管理部門參與設計、運行調度方案等的審查,或要求建設單位分階段(設計、施工、竣工、試生產和運營等)向環保部門匯報環保措施執行情況,建立報告-反饋機制,確保環評措施落實到位。[3]
3.3 嚴格執行流域規劃環評
流域規劃環評是流域性保護措施得以實施的前提和保證。流域性保護措施是流域規劃環評的重要支持內容之一,必須在水資源綜合規劃、專業規劃及其他國民經濟有關規劃中占有一席之地。流域性保護措施應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與河流主管部門聯合制定,并在流域開發規劃實施過程中進行。流域性保護措施與單項工程環保措施有機結合,才能發揮最大的環境效益。
3.4 盡快實行環境監理制度
水利水電工程施工期長、影響范圍廣,因此施工期環境監理尤為重要。驗收調查表明,實行環境監理的工程,施工期環保措施和監測計劃的落實情況總體較好,施工過程中出現的環境問題也能及時被發現并采取有效的補救措施。但現階段環境監理仍處于試點推廣階段,并沒有全面展開,環境監理制度也處于制定和完善中,這給環境監理工作的開展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因此,建議在現階段的工程建設中,應要求環境監理與工程監理聯合簽字以確保環境監理的監督力度,充分發揮其作用。同時,應盡快實行環境監理制度,開展并加強從業人員的系統專業培訓,使環境監理盡快步入正軌。
3.5 開展環境影響后評價
大型水利水電項目建設階段分明,其環境影響也各異。僅進行竣工環保驗收無法全面反映水利水電項目建設對環境的影響,階段性的環境影響也已無法彌補。為此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已開展了下閘蓄水等階段驗收工作,通過階段驗收可以及時發現存在的問題和環境影響,并盡快采取減緩和補救措施。而對項目的長期、累積影響,還應積極開展環境影響后評價工作。[4]工程運行數年后對其進行后評價(或跟蹤評價)可較準確地把握工程建設帶來的長期、累積、潛在的環境影響,檢驗環評的準確性和延緩措施的有效性,并尋求改進的途徑,反饋到今后的環評和環境管理之中。
4 結語
水利水電工程開發,尤其是流域梯級開發,其生態環境影響深遠,有些甚至不可逆。因此,更加需要在其竣工環境保護驗收中嚴加管理,嚴格執行“三同時”制度以及后續監督、管理程序。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建設機構、調查機構和審批機構在驗收及后續過程中共同配合和努力。■
[1]陳凱麒,曹曉紅,廖琦琛,等.水利水電建設中若干環境保護關鍵技術的考慮 [C]//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環境影響評價管理司.水利水電開發項目生態環境保護研究與實踐.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6.
[2]付鵬,張鍍光,胡強強,等.生態文明目標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發展方向[J].環境污染與防治,2008,30(6):85-89.
[3]陳慶偉,梁鵬.建設項目環評與“三同時”制度評析[J].環境保護,2006(12):42-45.
[4]毛文永.生態環境影響評價概論[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8.
201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