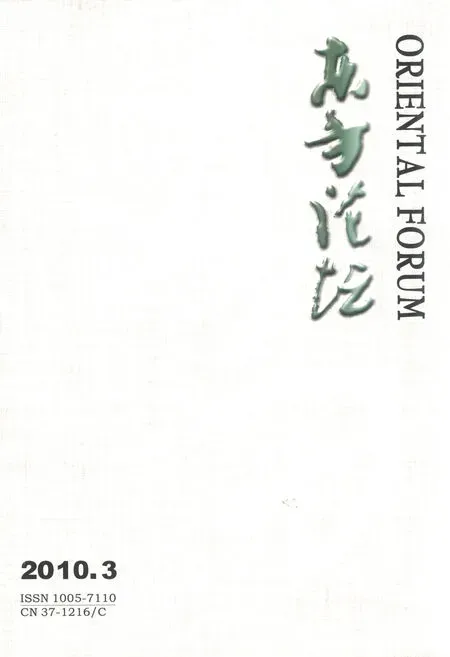新生代作家的影視生存與文化立場
周根紅
(南京體育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4)
新生代作家的影視生存與文化立場
周根紅
(南京體育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4)
1990年代以來與市場化浪潮同步成長的新生代作家表現出對城市生活想象性的寫實,使得他們的寫作與影視有了某種一致性,進而成為影視改編的一種基礎性資源。與此同時,他們全身心投入到影視浪潮之中,參與影視編劇,使他們的作家身份帶有明顯的影視特征。在這種強烈的影視文化和商業意志的滲透下,新生代作家的創作出現想象貧乏的狀態,自我重復現象比較嚴重,作品的原創性逐漸減弱。
新生代作家;影視文化;商業滲透
1990年代,文壇上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就是一批具有實力和鋒芒的青年作家日益活躍,最后成為一種具有代際色彩的作家群體,批評家將他們稱之為“新生代作家”。新生代作家登場的1990年代,市場經濟的變革和大眾傳媒的興起成為這一時期社會文化的重要推動力,商業話語成為影響1990年代各種文學藝術形態的主導性力量,它逐漸顛覆了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建立起來的價值觀念和文化模式。因此,1990年代成為一個中心價值觀和主流文化趨于消解式微的時代。與之前的先鋒作家相比,新生代作家幾乎與市場化浪潮同步成長,他們已經充分地適應甚至主動投身到市場經濟的發展洪流,商業化寫作成為新生代作家最為重要的創作特征。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新生代作家的創作總體上指向了物欲和性,“表現現實時采取便捷、近距離的審美視角,在貼近生活的體驗中,消解生活和藝術本身的雙重詩性特征,實現對生活欲望化、平面化、世俗化的存在性表達。并且,他們在寫作中竭力張揚自身對世界本能的、質感的生命沖動,外化為純粹的現實世界圖景,從而形成其小說文本的自足性個人性話語,以致構成對權利性主流話語的一種強力沖擊。”[1](P91)為尋求自身寫作的合法性,新生代作家甚至以“斷裂”的姿態告別傳統,然而,在商業的包圍和影視等大眾傳媒的聚攏下轉而形成了更為強烈的商業意志。新生代作家以一種徹底和決絕的姿態進入影視制作環節,成為影視的二傳手,逐漸被影視的商業化潮流所瓦解,模糊了文學的精英與通俗的邊界,日益染上了文化工業的品性,他們自身也完成了一個作家向影視人的轉型,進而遠離了文學創作的初衷。雖然新生代作家并不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他們在創作風格和題材上都表現出自己的特色,但是他們的創作“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90年代文化和其他文化(包括80年代文化)的雜糅,顯示了文化間對文學這一大眾媒介的爭奪。”[2](P247)
城市化想象
1990年代是一個社會急劇轉型的時代,一個以商業化和大眾傳媒為主導的多元話語模式開始形成,大眾文化以一種突飛猛漲的姿態進入我們的消費空間。“一方面執政集團通過機制修復和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強化,加固了政治的一體化體系;另一方面已經形成慣性運作的經濟的國際化和市場化,又使得市場經濟邏輯滲透和影響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層面。”[3]因此,在1990年代中后期,我國社會日益現代化甚至出現所謂的“后現代化”的生活場景,“進城”與城市化等成為1990年代一個比較突出的社會現象。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市民階層甚至鄉野村民,城市∕城市生活形成了一種新型的文化資源和特有的文化張力,影響著大眾的審美趣味和文化藝術形態,文學和影視藝術也在這一時期將目標轉向了城市生活。
1990年代,以張藝謀和陳凱歌為代表的一批導演,先后執導了《紅高粱》、《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黃土地》、《邊走邊唱》、《五魁》(黃建新導演)、《二嫫》(周曉文導演)等電影,展現了中國鄉村的生活和民俗,形成了1990年代新民俗電影的浪潮。這些新民俗電影的出現,“為中國的影視導演提供了一個填平電影的藝術性與商業性、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的鴻溝的有效手段。”[4](P22)這一類鄉土化電影的出現,可以說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城市與鄉村所形成的空隙所造成的,他們試圖縫合城市和鄉村、本土與國際等關系的裂縫,于是在這兩者之間徘徊,而又無法徹底指向某一方。然而,隨著1990年代中后期城市化的發展,我國影視的創作方向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以都市現代化為背景的生活表現日益增大比重。“由于現代生活方式迅速成為我們時代的生活主體,人們被現代思潮所感染,瞬息萬變的信息、蜂擁而至的各種物質誘惑、紛繁復雜的思想情感和快捷多變的節奏,使現代人處于張望、惶恐、焦慮不安的心態中,老邁緩慢的傳統生活情趣、與世無爭的閉鎖田園鄉村生活所帶來的情感需求被甩到時潮之后,都市影片應運而生。”[5](P298-299)風行一時的由王朔小說改編的《輪回》、《頑主》為先導,其后的《站直啰,別趴下》、《離婚了就別再來找我》、《沒事偷著樂》等電影,以及生活情節片《渴望》、農村少女闖都市的《姊妹行》、中國人在外國的《北京人在紐約》、反映社會改革生活的《編輯部的故事》、反映都市男女情感的《過把癮》等都市生活題材成為1990年代影視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的敘事資源,這些影視表現了現代人在身處嘈雜而混亂的現代生活漩渦中的種種情感困惑、心靈掙扎,從一個側面顯示出影視對日常生活的消費和對城市資源的借用。
當現代城市生活成為影視對當代人精神內核進行深刻挖掘的重要“場域”時,新生代作家也不約而同地將筆觸伸入城市生活的書寫、對日常生活的瑣屑敘事,表現出漂浮的成長經歷。面對日益城市化的進程所表現出的迷茫和慌亂時,“新生代作家以動蕩不居的城市生活作為主題,以第一人稱的獨白口吻表現主人公的‘漂泊’狀態。”[6](P202)畢飛宇的創作轉向就較好地說明了這一時期新生代作家的主題書寫策略。“(1994年之前,筆者注)我是一個比較看重歷史語義、過于著重小說修辭學的這樣一個作家。……(1994年之后,筆者注)我把觸角伸向了當代生活。”[7](P121)這之后,畢飛宇轉向了城市寫作,如《飛翔像自由落體》、《家里亂了》等,展示著城市的一種寧靜、凄涼、感傷的和絕望的情緒。張旻的《傷感而又狂歡的日子》、《遠方的客人》、《兩個汽槍手》則與以往的《情幻》、《審查》的不確定性有了很大的變化,小說的現實感進一步增強了,但也缺乏了深度而過于平面化。邱華棟的《城市戰車》、《哭泣游戲》、《都市新人類》等,以繁密的都市景觀和應接不暇的信息書寫了城市的誘惑。此外,丁天的《飼養在城市的我們》、何頓的《我們像葵花》等也專注于城市成長小說的寫作。新生代作家對城市生活和社會底層的瑣屑敘事,無一不表現出1990年代以來的文化特征。
當“城市生活”成為1990年代以來影視和文學共同的主題時,影視和文學便發生了密切的聯系,新生代作家的一些小說陸續被改編為影視作品。對城市生活想象性的寫實,使得他們的寫作與影視有了某種一致性,即影視所需要的基本上都是一種城市空間的想象和新型文化的體認,新生代“寫本能、寫欲望、寫生存的淺層次狀態”的寫作正好順應了這一文化潮流。新生代作家中接觸影視較早的應該是畢飛宇和述平。1995年,畢飛宇的長篇小說《上海往事》就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搖啊搖,搖到外婆橋》,1997年,述平的《晚報新聞》被張藝謀改編為電影《有話好好說》,這是張藝謀第一次真正涉足城市題材電影。《上海往事》、《晚報新聞》讓一些導演和作家逐漸認識到新生代作家的影視潛能,可以說,1990年代成為新生代作家和導演相互磨合和認識的時期。正是在這種影視和文學的文化合流背景下,張旻甚至還主動寫了電影劇本《向紅》,“《向紅》一開始是為電影寫的故事,后來沒有搞成電影,就當小說發表了。”[7](P165)新世紀以后,一批新生代作家的小說被大量地改編成影視作品。2000年,根據畢飛宇的小說《青衣》改編而成的同名電視劇長期“霸占”熒屏,許多人認識畢飛宇就是從這部電視劇開始的。隨后,著名導演楊亞洲和演員宋佳相中了畢飛宇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的短篇小說《哺乳期的女人》;2004年,著名導演葉大鷹則拍攝了根據短篇小說《地球上的王家莊》改編的同名電影,但是后來沒有發行。在文壇引起很大轟動的中篇小說《玉米》同時受到數位影視界重量級人士的青睞,說畢飛宇與影視特別有緣似乎并不過分。目前東西的小說被改編為影視應該算是最多的。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在獲得魯迅文學獎后,被改編為《天上的戀人》,由著名演員劉燁、董潔、陶虹主演,該片在2003年第十五屆東京國際電影節上大放異彩,作為唯一一般入圍的華語影片,被定位電影節的首映片。而真正使東西在影視圈站穩腳跟揚名的,大約要算長篇小說《耳光響亮》改編為二十集電視劇《響亮》和電影《姐姐詞典》。同樣取得巨大成功的是根據東西短篇小說《我們的父親》改編的二十集同名電視劇。除此之外,東西小說改編的影視劇還有:中篇小說《美麗金邊的衣裳》改編的電視劇《放愛一條生路》、《沒有語言的生活》改編的二十集同名電視劇以及《猜到盡頭》改編的電影《猜猜猜》。一時間,東西的小說成為影視改編的富礦。邱華棟更是以一個城市文學家的姿態書寫著城市的奢華和悲涼。2000年邱華棟的長篇小說《正午的供詞》被廣東巨星公司老板鄧建國買下其電影拍攝權后,由于作品將導演和演員的都市艷事作為主要內容,被認為影射張藝謀和鞏俐而一推再推。2001年再次被北京金英馬公司買下其電視劇改編權,邱華棟親自擔任26集同名電視劇的編劇。觸電較晚的何頓也在作品中展現出城市生活的想象甚至是浪漫,改編自同名小說的《我們像葵花》中一群文革中成長起來的文化人、小商人以及個體經濟階層,他們自以為“我們像葵花”,懷抱著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浪漫與夢幻,但在洶涌而來的商品大潮沖擊之下,他們的人格和命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為了生存,為了發財,為了女人,他們不惜鋌而走險,坑蒙拐騙,走私販假,背信棄義,打架殺人……此外,由陳染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與往事干杯》(夏剛,1995年),1995年被選為國際婦女大會參展電影。2007年鬼子的小說《一根水做的繩子》也進入了改編環節,這部小說不僅是鬼子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他從事創作以來惟一的一部寫愛情的小說。[8]
“隨著90年代初知識分子‘精英集團’的瓦解與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曾經彌漫在80年代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逐漸發生改變,圍繞著共名而尖銳對立的兩極意識形態也隨之逐漸淡化;隨著大眾文化市場的形成,傳統文學的審美趣味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群眾性多層次的審美趣味分化了原先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和知識分子各自所提倡的單一的藝術標準。”[9](P192)新生代作家的創作正是以個人的生活體驗和想象取代群體的意識形態和集體文化觀念的狂熱,進行著一種私語化、個人化的創作。他們在“個人化寫作”的名義下,展示著城市生活、青春成長的經驗和想象,這些無疑成為影視改編的一種基礎性資源。新生代作家與1990年代中后期的影視一起形成了商業意識勃興后的大眾文化浪潮,進而顛覆和消解著文學經典和精英文化。
身份的重塑
新生代作家是在1990年代的市場化浪潮中成長起來的,因此與這之前的作家所不同的是,新生代作家具有一種前所未有的體制外生存和自由寫作的意識,這種體制外的寫作,一方面使得新生代作家急于逃離政治意識形態話語的束縛,轉而面向社會生活∕城市生活的瑣屑敘事;另一方面,他們又被迫或自覺地以一種自由職業∕商業意志的身份進行寫作,他們的職業和文學創作沒有太大的關聯,他們不是專業作家,他們既選擇了文學創作,但又時刻面臨著巨大的經濟壓力,他們不可避免地受到商業意志的控制而使寫作成為一種謀生的工具。畢竟,“90年代的作家不能自恃清高埋頭寫作,他必須時時抬起眼來,因為他們已被置身市場。市場經濟鐵面無情,它使一部分作家緊張也讓一部分作家放松,或起始緊張繼而放松,使讀者快樂是適應市場的一條便捷通道。”[10](P11)因此,新生代作家比其他作家更懂得經濟利益在生活中的重要意義,為了“適應市場的一條便捷通道”,在這種經濟大潮中尋找自己的出路,新生代作家主動步入文學的商業化窠臼,與1990年代頗具影響的影視媒體一起,成為制造大眾文化產品的生產者。
雖然1980年代崛起的大多數先鋒作家面對影視并不拒絕,但是他們仍然堅持著自己的文學理想,仍然將影視和文學截然分開,仍然對文學充滿眷戀和激情,即使那些與影視結緣較深的作家北村、潘軍等人,仍然堅持文學的獨特性。而大多數新生代作家則全身心投入到影視浪潮之中,參與影視編劇,并逐漸脫離了文學創作的本真道路,甚至許多新生代作家徹底放棄了寫作,而成為一個職業的編劇,即便仍然堅持“編劇和創作兩不誤”的作家也大多只是面向影視的商業化寫作,比較典型的是李馮、東西、鬼子、王彪、述平等,他們中的有些人在編劇這一行當中已經成為知名的成功人士。述平在繼《晚報新聞》改編為《有話好好說》之后,參與了編劇《趙先生》(呂樂,1998年)、《鬼子來了》(姜文,1999年)、《太陽照常升起》(姜文,2007年)以及中國首部現實魔幻題材電影《走著瞧》(李大為,2008年);王彪參與了改編自軍旅作家吳強的經典名著《紅日》(蘇舟,2008年)的編劇工作和2009年國慶獻禮電視劇《東方紅》(蘇舟,2009年) ;丁天則編劇了《鐵血青春》(劉江,2003年)和《陳賡大將》(葉大鷹,2006年);張旻曾參與編劇池莉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水與火的纏綿》(李自人,2006年);東西直接參與了自己小說的影視改編過程,在其中擔任編劇,同時還參與了其他影視改編活動,如鐵凝的《永遠有多遠》(陳偉明,2001年)。遺憾的是,他們在影視編劇過程中并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也沒有借助影視成名。朱文更是走得比其他新生代作家更遠,在編劇了影視作品《巫山云雨》、《回家過年》、《海南,海南》之后,直接當起了導演,執導了《海鮮》、《云的南方》等作品。但是,朱文至今仍與早期第六代導演一樣,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體制外的生存,尚未完成自身的商業化、主流化轉型,限制了其發展的生存空間。參與影視編劇最為成功的當屬李馮、東西和鬼子,他們成為新生代作家群體中少數借助影視而聲名俱隆的作家,也是少數實現了從作家向編劇的完美轉型。李馮相繼編劇了《英雄》、《十面埋伏》后,成為張藝謀的御用編劇,也成為當前影視領域的金牌編劇。隨后他還編劇了《霍元甲》、《瘋狂白領》等影視劇。2008年由深圳市鳳凰星傳媒有限公司、中國孔子基金會和山東廣電總臺聯合打造的106集動畫片《孔子》的編劇就有李馮和葉兆言、張煒等,計劃于2009年9月28日孔子誕辰2560周年時在央視首映。鬼子曾經為張藝謀擔任電影《幸福時光》的編劇,2001年,陳凱歌想改編鬼子作品《上午打瞌睡的小女孩》時,鬼子親自參與到編劇中去,為陳凱歌寫出了劇本初稿,但因為題材較為敏感而被擱置。據說這個劇本之所以被陳凱歌擱置,“一是因為題材敏感,二是因為他在處理故事和人物上還沒有找到一個滿意的表現方式。”[11]2006年鬼子再次觸電,為成龍的《寶貝計劃》編劇。東西則主動參與了每一部自己小說改編的影視。可以看出,在面對影視的沖擊時,新生代作家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文化姿態,正如新生代作家東西對那些不愿觸電、而把精力放在寫小說的作家所說:“我覺得,我們的作家不要過分自戀,對影視劇也不要一棍子打死。你看很多歐洲電影,會認為電影比原著差?小說不一定比電影更高雅。讓讀書的人讀書,讓看電影的人去看電影吧。”[12]無論新生代作家介入影視后的生存空間如何變幻,新生代作家通過對影視的深度介入,很自然地就融入到影視大潮中,完成了從一個“作家”身份向一個“編劇”身份的轉變。
新生代作家對影視的深度介入,一個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影視所帶來的名利雙收的巨大回報。正如畢飛宇在面對影視改編時所說的,“就我來講因為影視劇使我的讀者群擴大了,一些本來不看我作品的人看了影視劇后又回過頭看我的作品,使我的作品擴大了影響。不能說光要求作家用自己的作品為其他藝術種類提供了幫助,而不允許作家占到一點便宜,我認為這就是作家占到的一點便宜而已。如果有人找到我想把我的作品改編成好的影視劇,又有公道的價錢和我喜歡的導演,我不會拒絕。”[13]其實,1990年代以來,大多數新生代作家的生活狀態并不理想,甚至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丁天沒有讀完高中就退學了,然后在南京一所英語專科學校上學,上了一年就去華藝出版社工作了,1994年辭職。[14](P291)韓東靠《他們》中的一個朋友的幫助生活,寫作的稿費很難生活,特別是出書較少,稿費低。此外,朱文也一樣,最困難的是吳晨駿。[14](P49-50)雖然韓東提及他和朱文、吳晨駿的狀態時說:“我們辭職,我們養活自己,然后我們拒絕寫那種副刊文章,拒絕寫暢銷書,拒絕很多東西。”[14](P48)但是,這僅僅是一種宣言,實際上,韓東也曾在各種報刊如《新周刊》(廣州,2001年)、《現代快報》(南京,2007年)等開設有一些七零八碎的隨筆專欄,這些稿費成為他生活的主要來源。可以說,在與影視接觸(小說被改編或參與編劇)之前,新生代作家的生活狀態總體上來說并不理想,尤其是那些辭職后的新生代作家。另一方面,新生代作家基本上都生活在城市,他們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與現代物質文化和城市文化有著不解之緣,也使得他們成為現代城市的親和者和批判者,他們也不能不對城市的物欲表現出影響,就像邱華棟所說:“我只管做好編劇,掙點‘小錢’買輛車開。電影電視請誰拍都行,拍得如何與我無關。”[15]由于1990年代特殊的經濟和社會狀態,各領風騷的1990年代,他們必須立足于1990年代的文化資本中表現出一種更加明確更加現實的寫作路徑。在這一現實路徑的尋找過程中,新生代作家作為1990年代文化的直接參與者,在早期表現出一種“斷裂”的姿態——與1980年代文化表示斷裂,與1990年代文化一起作為自身發展的文化起點。“斷裂”者們是“新生代”中的代表和極端,其實,整個“新生代”作家的心態與“斷裂”者只是程度上的區分而無實質上的差別,他們在寫作中普遍表現的迷茫和空洞,以及他們整體的言語大于行動的創作表現,都顯示了他們反叛的表層化和形式化。他們的反叛姿態,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一個姿態而已,沒有取得真正的實質性成果,也難以形成對時代文化的真正反叛。[2](P252)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當新生代作家急功近利地介入影視或進行商業化寫作時,1998年新生代作家的“斷裂”事件,不過是一場故作姿態的鬧劇,最終他們還是回到了1990年代以來的商業文化邏輯,投身影視文化所構建起的話語系統,完成了商業社會的身份重塑。
匱乏的寫作
1990年代以來,強烈的影視文化和商業意志的滲透,對作家的文學創作表現出一種改寫和潛在的影響。新生代作家的創作出現想象貧乏的狀態,自我重復現象比較嚴重,同一故事、細節、場景、元素和敘事方式在不同作品中反復出現,作品的原創性逐漸減弱。邱華棟的《把我捆住》、《偷口紅的人》、《紅木偶快餐店》和《蠅眼?遺忘者》對打胎細節的描寫;《闖入者》和《夜晚的諾言》對摸得大獎的奇遇的玩味;《眼睛的盛宴》和《公關人》對假面舞會的渲染大同小異;《城市戰車》中朱溫和《蠅眼》中的袁勁松相同的性病方式。張旻在《槍》、《叛徒》、《永遠的懷念》和《兩個汽槍手》中對“槍”和“彈弓”的反復渲染;小說《回身遙望》不斷引入散文《永遠的女孩》的故事,可以說《永遠的女孩》是小說《回身遙望》的故事生長點。何頓的作品在人物關系、故事情節、敘述語調和結構關系上都同出一源,《自我無我》中的李茁、《無所謂》中的李建國、《不談藝術》中的肖正和《生活無罪》中的湘潭人都是懷才不遇的落魄者;《告別自己》中的雷鐵、《喜馬拉雅山》中的“我”、《生活無罪》中的“我”和一系列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辭去中學教職后轉入商海的突圍者,《我不想事》中的袖子、《弟弟你好》中的丹丹和《生活無罪》中的狗子在暴死前都散發出“神秘的臭味”。丁天的《流》以《飼養在城市的我們》中的一個人物劉軍為主角,細節與情節的重復無可避免。①新生代作家小說中自我重復現象比較普遍,對此學者黃發有曾詳細地做過論述,本部分論述也參考了其部分資料,在此不再贅言,詳見黃發有:《媒體制造》,第280—281頁,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年出版。林白的小說很多是將幾個短篇組成中篇,幾個中篇組成長篇,里面的細節和故事重復較多,如其自傳體長篇《一個人的戰爭》和《瓶中之水》、《青苔或火車的敘事》、《守望空心的歲月》等小說里的不少細節都出現重復甚至雷同。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作家總體上過于關注身體欲望和金錢物欲,使得他們的敘事主題千篇一律,沒有任何突破。刁斗的《作為一種藝術的謀殺》和《延續》、張旻的《情幻》、林白的《致命的飛翔》、海男的《我們的情人們》、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守望空心歲月》、韓東的《障礙》、朱文的《我愛美元》、《五毛錢的旅程》等,大量對性細節、性體驗的描寫前后重復,話語模式和敘事方式大同小異。與此同時,新生代作家的敘事徹底投放在商業語境內,表現出強烈的實利主義原則。無論是何頓的《我們像葵花》、《生活無罪》,還是邱華棟的《城市戰車》等,其敘事的中心無非都是“世界上錢字最大,錢可以買人格買自尊買卑賤買笑臉,還可以殺人。”(《生活無罪》,曲剛語)邱華棟本人也承認:“我本人也想擁有這些東西,當然什么時候我才能得到就不好說了。”[16](P44)朱文小說引發的“《我愛美元》事件”無疑是新生代作家與傳統觀念之間最具有代表性的價值沖突。新生代作家這種迎合商業的寫作姿態,對現實物欲的沉迷與認同,已經脫離了一個作家應該追求的審美理想,最終損害的必將是文學的原創風格和藝術品味。
另一方面,新生代作家的小說表現出強烈的影視痕跡。東西的長篇小說《后悔錄》,就借用了一些影視劇的創作方法,比如觀察和描寫的視覺角度,場景的描寫和人物的對話。與東西過去的小說相比,《后悔錄》結構更為簡潔緊湊,描寫的角度和手法更豐富,人物的對話也更準確。小說的結構猶如一部影視劇的敘事方式,小說開始是一個男人的自述,敘述的對象是“你”,似乎是以讀者為傾訴對象。隨著閱讀的深入,讀者又察覺到他的傾訴對象是一個女性。但直到小說的結尾,讀者才會發現:這原來是一個性無能的老處男面對一個色情服務的“小姐”的自述。《后悔錄》通過這種敘事結構,一層層抽絲剝繭式的敘述逐漸揭開傾聽者的面紗。這種獨特的小說美學有似影視作品的表現手法:先將鏡頭近焦鎖定講述者,再隨著講述過程逐漸將鏡頭拉遠,最后展現全部背景。東西自己也承認,“寫了幾年劇本,我再寫長篇小說《后悔錄》,有讀者說這個小說比我過去的小說好讀,這和我寫劇本有關系。因為,我懂得考慮讀者的閱讀感受。”[17]林白也是一個深受電影影響的作家,她曾在廣西電影制片廠當文學編輯,可以說是一個與電影有著密切關系的作家。她的小說《子彈穿過蘋果》和《致命的飛翔》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受到電影影響的作品。《子彈穿過蘋果》的構思與希區柯克的《蝴蝶夢》有著非常相似之處:絕對的主人公在小說和電影中都沒有出現;小說中七葉和朱涼的關系與電影中女管家和女主人的那種主仆、情人、追隨者的關系極其相似;小說的懸念氛圍和電影的懸念氛圍也頗為雷同。《蝴蝶夢》這部電影在林白的多部小說里提到,也是林白最為喜歡的黑白電影之一,因此,這部電影對林白小說的潛在影響自然不足為怪。而《致命的飛翔》這一意象則來源于希區柯克的電影《鳥》。同時,林白小說的結構也深受電影的影響。她的小說結構打破了小說的線性敘事,呈現出交叉、平行和并置的敘事結構,如《同心愛者不分手》中的月白色綢衣女人和男教師以及“我”和嘟嚕這兩條平行線索、《致命的飛翔》里的北諾和禿頭男人以及李萵和登陸的平行結構。除此之外,林白的小說中還運用了大量特寫、主觀鏡頭等電影語言的表現方法。林白的一部虛構性自傳也打上了電影的烙印,《玻璃蟲:我的電影生涯——一部虛構的回憶》。可以說,電影對林白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我被電影徹底浸泡過,我無法擺脫這一點,我眼前總要出現銀幕,正如我筆下總要出現女人,我永遠只寫進入我視野里的東西。”[18](P91)
由于商業因素的影響和生存的需要,新生代作家對影視表現出急切的認同,影視在某種程度上逐漸成為相當一部分新生代作家的主要職業,許多新生代作家甚至放棄或半放棄了文學創作。影視培養了作家的市場意識,作家在影視的潮流中摸爬滾打,也漸漸熟悉了影視的生產工序,新生代作家隨著不斷滋長的市場意識而走向身份的消解。以朱文和李馮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徹底轉向了影視行業。李馮在擔任張藝謀的影片編劇之后,成為身價百倍的“金牌編劇”,然后徹底告別了文學創作。朱文轉行導演,執導了多部影片,并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東西、鬼子、何頓則熱衷于影視編劇,雖然還繼續小說的創作,但小說創作上鮮有建樹。這些新生代作家實際上已經從作家轉向了影視。當然,在經歷影視之后,有些新生代作家表示不再涉足影視編劇這一行當,要將精力放在小說創作上,但是當他們再次回歸文學時,卻很少能見到他們的作品有什么進步。當自己聲望俱隆時,邱華棟成為涉足影視之后退而守之的作家,“他不否認自己曾為了個人的經濟利益寫過一些劇本,而有些劇本是媚俗的。但是現在,他堅決不會去寫了,他信奉文字本身的魅力,盡量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不媚俗,不出賣文字。”[19]鬼子也在小說《一根水做的繩子》賣出電影改編權后表示,雖然影視公司希望他來當編劇,但是他現在已經不想再做影視了。“因為我前些年在影視圈里面晃蕩了一些時間,我覺得這耗費了我大量的時間。我現在從這部小說開始,將回歸到寫小說中去。”[8]但是,雖然他們再次轉向文學的時候,他們并沒有創作出相對優秀的作品。只有那些仍然堅持文學道路,較少參與到影視的新生代作家還仍然創作出了一些優秀的作品,如畢飛宇和李洱等。畢飛宇自覺地與影視保持著一段距離,即便自己的小說被改編為影視,也不介入編劇過程,而主要進行小說創作。李洱雖然也有一些作品被被改編為影視,如《石榴樹上結櫻桃》(陳力,2008),但是他對影視還是保持警惕,“我的小說現在也被改編成電影。改完以后我不看。制片人讓我看,我也不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人物關系變了?你盡管變。讓我署名,我說我不署名。如果放棄署名權給更多的錢,那我選擇要更多錢。”正是這種創作心態,近年來,畢飛宇的《平原》、《推拿》和李洱的《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等作品廣受好評。然而,這樣的新生代作家已經越來越少了,許多新生代作家仍將小說作為影視的一個過渡階段。這種狀態和理念所創作出的小說自然喪失了文學的基本品質,正如作家李洱說,“小說中不能被影像化的部分,就是小說性最強的部分。如果一部小說很容易改編成影視劇,它的小說性就值得懷疑,即使不能因此說這是部爛小說,起碼它不算是好小說。”[20]
結語
學者黃發有在考察1990年代以來影視與文學創作主體的分層現象時發現,第六代導演與新生代作家之間具有某種內在的精神紐帶,第六代導演的生存方式、審美觀念與新生代作家殊途同歸,“影視主體與文學主體的呼應共同地印證著當下中國的文化邏輯。但是,這種過度膨脹的代群化特征抑制了創作個體的文化獨創,同時也使影視與文學的交流缺少互補的良性循環,精神基調的過分一致使影視與文學難以相互激發,也使文化格局顯得相對單調而不夠豐富。”[21](P203)當一些新生代作家紛紛逃離文學,加入了影視編劇行列或商業化浪潮的時候,新生代作家的文學創作活動便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游離狀態。一方面,1990年代以來的影視文化和商業邏輯潛在地影響到了新生代作家的創作行為,使得他們的創作脫離了文學本身;另一方面,在這一文化氛圍中,許多新生代作家在影視、商業和文學之間不斷徘徊,表現出身份的漂泊不定。正是這種雙重的游離狀態,我們發現,在今天我們再次回望“新生代作家”這一群體時,除1990年代新生代作家初登文壇時創作了一些優秀作品以外,1990年代后期和新世紀以來,新生代作家的創作基本上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
[1] 張學昕.詩性的消解和精神的遁逸——九十年代年輕作家小說創作的精神走向[A].唯美的敘述[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
[2] 賀仲明.中國心像——20世紀末作家文化心態考察[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3] 尹鴻.世紀轉折時期的歷史見證——論90年代中國影視文化[J].天津社會科學,1998,(1).
[4] 尹鴻.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影視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5] 周星.中國電影藝術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6] 黃發有.媒體制造[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
[7] 張鈞.小說家的立場——新生代作家訪談錄[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8] 莫俊.鬼子新作即將改編成影視劇《一根水做的繩子》:生命永遠為了愛[N].南寧日報,2007-09-13.
[9] 陳思和.試論90年代文學的無名特征及其當代性[N].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10] 張巖泉.社會轉型與文學媚俗[J].中國文學研究,1997,(2).
[11] 石宇.愛上“瞌睡女孩”暫不“夢游桃源” 陳凱歌找新震撼[N].每日新報,2002-04-01.
[12] 曹雪萍.著名作家東西:我就喜歡新奇的野路子[J].新京報,2005-10-14.
[13] 肖煜.畢飛宇:小說改編成影視劇很正常[N].燕趙都市報,2005-12-02.
[14] 張鈞.小說家的立場——新生代作家訪談錄[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15] 陳蕙茹.邱華棟:鄧建國再不拍《正午的供詞》就收回版權[M].成都日報,2001-09-17.
[16] 洪治綱.無邊的遷徙[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
[17] 東西.小說與影視的跳接[N].文學報,2008-12-11.
[18] 林白.子彈穿過蘋果[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19] 趙慧.邱華棟:不斷超越自我[N].新疆經濟日報,2008-09-11.
[20] 周代紅.價值彷徨時代的文學堅守[N].大連日報,2004-11-30.
[21] 黃發有.媒體制造[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馮濟平
The Survival through Film & TV and the Cultural Posi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Writers
ZHOU Gen-hong
(Nanjing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njing 210014, China)
Since the 1990s, the new generation writers who grow with a wave of marketization begin to write realistically about urban life, which makes novels and films conform to each other to some degree, which becomes the basic resource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dedicate themselves to the wav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nd involve themselves in the writing of film and TV play scenarios. Because of the strong penetration of film and TV culture and the commercial will, those new generation writers lack imagination and suffer from serious self-duplication.
new generation writers; film and TV culture; penetration of commercial will
I207
A
1005-7110-(2010)03-0064-07
2009-12-07
周根紅(1981-),男,安徽安慶人,南京體育學院新聞學專業講師,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文學與傳媒、影視藝術與文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