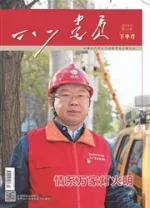鄧小平的語言風格

鄧小平的語言很有特色,簡潔有力,抓住要害,不冗長繁瑣,簡短的幾個字可以概括很多的內容。有人計算過,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時候,在武漢火車站的講話,總的意思是反對文山會海,只用了二百余字。著名作家劉白羽在《再道一聲小平您好》中寫道:“在一個大規模的會議上,我發現小平同志與旁人的不同之處,在整個過程中,他只講了兩次話,而且話講得精煉、簡短,會也就開得短,但他的每句話就像一顆子彈那樣有力,直中目標。”綜觀鄧小平的一生,他開會一般不作記錄,平時也很少記筆記,發言時最多一個紙條記幾個數字,大凡落筆都在文件上面。
鄧小平的語言簡潔,與長期的戰爭生活有關。那時不可能有時間去作長篇報告、寫長篇文章。比如,在談到長征時,他用了“跟著走”三個字;談抗戰時的感受,用“吃苦”兩個字;談解放戰爭,用“最舒暢”三個字;談“文革”之前的10年工作,用“最忙”兩個字;談“文革”,用“最大的災難”五個字;得知林彪摔死后,用“林彪不亡,天理不容”八個字;談到自己的三落三起時,用“忍耐”兩個字;談世界問題,用“東西、南北”四個字;談精簡軍隊的問題,用“腫、散、驕、奢、惰”五個字……
借用人人熟知的事物打比喻來說明深奧的道理,是鄧小平語言的一大特點。比如,將游擊隊脫離群眾的行為比喻為“裸體跳舞”;把觸及大的領導的問題比喻為“摸老虎屁股”;把照抄照搬上級文件的做法比喻為“當收發室”;把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與日本在一些技術領域的合作比作“學生與老師”的關系。談改革開放要膽子大一些,比喻為“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把精簡機構比喻為“拆廟搬菩薩”、“消腫”;在嚴厲打擊犯罪時,將大的問題比喻為“就是老虎里頭最大的東北虎也要管”;把價格改革比喻為“過關斬將”;談到在臺灣實施“一國兩制”時,比喻為“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
語言是一門藝術。在某些時候,用委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往往會收到特殊的效果。雙關語就是其中之一。比如,在一次登黃山時,鄧小平說“黃山這一課,證明我完全合格”,指自己不僅政治合格,身體也合格,可以為國家工作。“已經是春天了,冷不到哪里去。”這是鄧小平在1972年從江西回北京的路上,晚上散步后警衛讓他回房間時的回答,不僅是指自然氣候,也指政治氣候。1992年“南方談話”的時候,鄧小平說“我從來不走回頭路”,以此表明他對改革開放的堅定信心。
大部分時間,鄧小平是不需要用委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的,但在一些特殊場合、特殊情況下,他用語委婉:一、對上級。比如毛澤東要他對“文化大革命”作“三七開”的結論,鄧小平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委婉地表達了不作結論的答復。二、在外交場合。1978年鄧小平訪問日本,針對中國一些人不承認自己落后,他委婉地指出,“長得很丑,卻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樣,那是不行的”。三、其他情況。聶衛平得了“棋圣”的稱號,鄧小平委婉地指出,“圣人不好當,你還是當百姓好”。
運用幽默語言,鄧小平自然是行家里手。他的幽默不但通俗易懂,而且蘊含深意,不落俗套,許多幽默段子廣為流傳,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和長久的印象。在從重慶回北京的飛機上,子女問他:“在重慶大家叫你首長,到北京叫什么?”鄧小平用諧音回答:“在重慶叫首長(手掌),到北京叫腳掌。”在四川考察的時候,農民問:你們從哪來,到哪去?鄧小平回答:“我們從上頭來,到下頭去。”鄧小平聽說一個唱“樣板戲”的錢姓演員把自己的姓改了,于是戲稱為“連‘錢’也不要了”。他還把自己家鄉的干部稱為“父母官”;對陳香梅談廖承志,稱“你的舅父有‘氣管炎’,你可曉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勸吳晗,“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