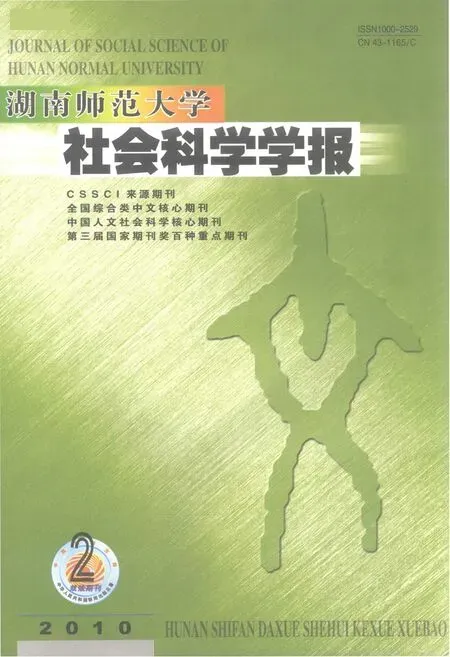浪漫主義:現代命運、經典解讀與啟示
張文初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浪漫主義:現代命運、經典解讀與啟示
張文初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20世紀主導性的社會心理在表層現象上排斥、對抗浪漫主義,但在深層結構上仍然強勁地推進著浪漫主義的發展。施勒格爾—海涅—施米特—羅素—伯林的浪漫主義研究構建了自浪漫主義運動出現以來的、近200年間的對浪漫主義的經典解讀。經典解讀的啟示是多方面的。它揭示出“作為概念語詞的浪漫主義”和“浪漫精神”的區別;它呼喚更為開放的對浪漫主義的理解:其中,超時空、跨學科、非理性、關注否定性意義等解讀維度在當代思考中尤為重要。
浪漫主義;情感;機緣
一
在表層社會心理的構成上,20世紀延續和深化著19世紀30年代以來的反浪漫主義訴求,對浪漫精神持抵制、漠視、對抗的姿態。整個20世紀的基本情調似乎都與“浪漫”無緣。兩次世界大戰、核災難、物化、生態危機、極權政治、理性囚牢、科技暴政:這些就是20世紀的人們殊深軫念的生存現實,它使這個世紀的人類感受到自我的生存完全陷落在非浪漫、反浪漫的深坑里。“只需在戰壕里呆上一周,就會滌除那些殘存的對戰爭的浪漫想法。”[1](P432)“戰爭是地獄,建造這所地獄的人是罪犯。”[1](P432)“像大詩人威爾弗雷德·歐文那樣幾乎挺過整個戰爭的人(歐文在即將停戰之際陣亡),對于戰爭的感受只有恐怖、遺憾、無聊。戰爭引發的浪漫情緒一去不返,戰后時期人們一想到戰爭就深惡痛絕。”[1](P433)這些是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生存敘說。戰爭不只是制造千萬人肉體的死亡,更是對整個人類精神生命的傷害。戰爭也并非只是災難的起因,更可怕的是它實際上是人類文明內在病灶的爆發。龐德說,西方文明是“一個老調了牙的婊子”。[1](P445)威爾斯說:“我們所在的文明正在倒塌,而且我想它倒塌的速度非常快。”[1](P445)諸如此類的對于人生、人性、文明、文化的非浪漫的、反浪漫的描述和揭露幾乎是整個20世紀前50年所有著名思想文本和文學著作的共同主題。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加塞特的《大眾的反叛》、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城堡》、海明威的《太陽照樣升起》、福克納的《喧囂與騷動》、雅斯貝斯的《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加謬的《鼠疫》,這些隨便列舉的書名呈現給我們的都是迷惘、破滅、絕望、荒誕、恐怖、惡心等等讓歡快的浪漫主義者們無法理解的情緒。
然而當我們穿越社會心理的表層,向其深處窺探時,我們發現的卻是另外的情景。初版于1955年的羅素的《西方哲學史》說:“從十八世紀后期到今天,藝術、文學和哲學,甚至于政治,都受到了廣義上所謂的浪漫主義運動特有的一種情感方式積極的或消極的影響。連那些對這種情感方式抱反感的人對它也不得不考慮,而且他們受它的影響常常超過自知的程度以上。”[2](P212)1919 年出版的施米特的《政治的浪漫派》談論的雖主要是20世紀以前的現象,但他對“浪漫趣味”的解讀,包含了對20世紀初社會現實的指認和對該書眼中的“未來”情景的預測。20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哲學家伯林說:歐洲歷史上由浪漫主義帶來的第三次大轉折全面改寫了西方世界的歷史,“我們稱為浪漫主義的運動使現代倫理學和政治學發生的轉型,遠比我們意識到的要深刻得多。”[3](P191)“浪漫主義者引進了一組新價值,與舊的價值毫不相容,而今天大多數歐洲人是這兩種相對立的傳統的繼承者。”[3](P198)伯林的這些敘述出現在《浪漫主義革命:現代思想史的一場危機》一文中。該文收入出版于1996年的《現實感》。盡管伯林的浪漫主義的“今天”并非就是20世紀行將謝幕的96年,但它代表了伯林對整個20世紀的生存現實的判斷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
羅素、施米特、伯林這些思想巨人的現實觀察確證了一個鐵的事實:浪漫主義依舊存在于20世紀西方人的生活和心靈之中。當然,他們的看法包含了他們對浪漫主義的不同理解。羅素關注的是“情感方式”,施米特重視的是“趣味類型”,伯林言說的是“價值范式”。從他們的立論依據和其現實觀察的對應來看,他們的判斷都是不可推翻的。施米特說,按照法國人對浪漫主義的理解,浪漫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事實。設想“有人正在城市街道上散步或在集市上閑逛,他看著農婦在兜售自己的貨物,家庭主婦在買東西。這些十分投入的交易著鮮果佳肴的人,令他十分感動;可愛的小孩、專注的母親、生龍活虎的年輕人、身板筆挺的男人和莊重的長者,都讓他著迷。此人就是個浪漫派。”[4](P3)感動于日常普通的無害于他人的真實生活情景就是浪漫:如果接受這樣的定義,可以說每一個人的生活里都有浪漫。說20世紀人類生存含有浪漫因此就不是空穴來風。中國當下流行歌曲把戀人攜手變老看作人間“最浪漫的事”而深情吟唱就是對浪漫主義真實存在的一種民間詮釋。伯林說,浪漫主義認定“要成為人不是要去理解或推理,而是去行動”;“因為個人被丟入他的社會的本源潮流里”,“于是這個美學模式就被移植到了社會和政治范疇里,后者注定要在現代歐洲歷史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成為“支持著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和任何依賴于道德的運動”[3](P214)的基本原則。這是對政治浪漫主義現代影響的描述。稍微熟悉20世紀政治社會歷史的人應該說都不會拒絕這樣的描述。在談到浪漫主義的美學觀念和價值觀念時,伯林說,存在主義是浪漫主義的后繼形式。在浪漫主義和存在主義看來,“價值不是事實,世界是‘價值中立的’”,“要想證明這種或那種道德秩序或政治成就更好、更值得追求或更理性是因為事物的普遍結構如此,這在這種類型的思想家看來純粹是自我欺騙——起源于在事物本質里尋找對自己觀點的支持的狂熱欲望”。[3](P217)如果相信此種論述,就同時可以認定:當今正在改寫西方文化的后現代主義實際上正是浪漫主義的新生兒子。人們說福科骨子里是浪漫主義者。實際上不止福科如此,德里達、利奧塔、德勒茲,同樣如此。
歷史常有邏輯的支撐。20世紀的浪漫主義可以在黑格爾思辯哲學的背景上解讀:20世紀浪漫主義的歷史性存在實際上隱含在20世紀反浪漫主義運動的邏輯之中。包括《存在與時間》等著述在內的整個20世紀對浪漫主義的蔑視和仇恨實質上正是因為浪漫主義頑強存在的緣故。排斥、反撥的原因是被排斥的東西在場,是因為它正在阻礙期待之物的出現。只要仍舊有排斥,被排斥之物就仍然在場。只有到排斥本身消失,被排斥之物才算是真正被排斥掉了。被排斥物的在場不僅是排斥行為誕生的依據,而且是排斥行為展開的基礎。被排斥物就包含在“排斥行為”之中。排斥的幅度、深度、方式、路徑、機制實際上都受制于被排斥物。20世紀的思想家之所以要顛覆浪漫主義恰是因為他們骨子里正活躍著浪漫主義的基因。顛覆的干勁越大,顛覆的程度越深,說明潛在的浪漫之魂越活躍,隱藏的層面越深刻。顛覆的路徑和機制、方式和手段也正是浪漫之魂活躍的路徑和機制、方式和手段。邏輯上的悖反不僅是從內在機制上映證了羅素、伯林諸人所描述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從理性上開辟了對20世紀反浪漫主義運動逆向解讀的合理空間。它從一個堅實的基礎上說明了浪漫主義在20世紀和當今社會中的存在是不容懷疑、不容輕視的事實。
二
浪漫主義在現代人心理和生活中的存在既決定了、同時也受制于思想家們對浪漫主義的解讀。
隨著18世紀末浪漫精神的井噴,浪漫主義的自我反思就跟著出現了。最早對浪漫主義進行學理審視的是著名的浪漫主義者施勒格爾和海涅。施勒格爾是浪漫主義的思想領袖,他的思考源自于創構浪漫主義的追求。表面看來,施勒格爾首先關注的是詩體形式的浪漫主義;是發展和繁榮“浪漫詩”的目標。但實際上,他的“浪漫詩”就是他對于詩的整體構想。他并不只是把“浪漫詩”作為“一種”詩體看待,他希望所有的詩都浪漫化。更關鍵的是,他的所謂詩的浪漫化,不是基于把詩僅僅作為人類生存方式之一的詩學理解,而是基于對人的整體生存的命運思考。在施勒格爾這里,詩的浪漫化,就是人的生命的詩化,就是人的生存的浪漫化。下面這一段施勒格爾的著名論述表達的正是這樣的意義網絡:
浪漫詩是漸進的總匯詩。它的使命不僅是要把詩的所有被割裂開的體裁重新統一起來,使詩同哲學和修辭學產生接觸。它想要、并且也應當把詩和散文、天賦和批評、藝術詩和自然詩時而混合在一起,時而融合起來,使詩變得生氣盎然、熱愛交際、賦予生活和社會以詩意……[5](P11)
浪漫詩等于詩的浪漫化、等于生活和社會的詩意化:這就是上述引語要表達的第一個思想。與之相關的第二個思想是,詩的浪漫化和生活的詩意化關鍵在于由“分”而“匯”,由“割裂”而“融合”。施勒格爾提出“總匯詩”的概念,強調詩的被割裂的體裁的融匯,詩同哲學、修辭學的融匯,詩和散文、天賦和批評、藝術詩和自然詩的融會,都是在闡釋他的“融匯哲學”。事實上,他要“融匯”的遠不只是上述條目,“融匯”有著更為廣闊深邃的內容。他說:浪漫詩和浪漫生活“包括了凡是有詩意的一切,最大的大到把許多其他體系囊括于自身中的那個藝術體系,小到吟唱著歌謠的孩童哼進質樸的歌曲里的嘆息和親吻”;它“能夠”“充當一面映照周圍整個世界的鏡子,一幅時代的畫卷”;它“不受任何現實和理想的興趣的約束”,“隨心所欲容不得任何限制自己的法則”。[5](P71)基于對整體主義和人性狂妄的不屑,當今的人們也許無法和施勒格爾的“融匯哲學”共鳴。但后現代對根深蒂固的理性分割主義的厭惡又可以讓我們進入施勒格爾的“浪漫”之中。維塞爾說:“席勒列出了一系列對立,不管從歷史來說,還是從邏輯上,都是不易克服的。它們預示了黑格爾式的那期待著一個更高的綜合的正題和反題。的確,德國浪漫派的源起恰恰基于這樣一種趨同的需求,而第一個為此而奮斗的就是 F·施勒格爾。”[6](P27)施勒格爾的時代,隨著理性主義哲學的興盛,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隨著個體主義思潮的噴發,隨著現代大工業生產的躍進,一切都分崩離析了,一切都在矛盾、沖突、分裂、對立之中。中國古人所說的“劃斷天人,失太極渾輪之數”、“九地黃流亂注”等等話語也許可以用來形容施勒格爾這一代人的生存感受。就是基于這種感受,施勒格爾呼喚“總匯”,呼喚那種“一切都應是詼諧,一切都應是嚴肅,一切都坦白公開、肝膽相照”的、“包含了并激勵著一種感情,一種無限和有限、一個完整的傳達既不可能而又必要的無休止的沖突的感情”。[6](P74)
出于對“總匯精神”的“浪漫”的理解,施勒格爾成了歷史上第一個狂熱推崇浪漫主義的思想家,與之尖銳對比的是同樣被歷史學家稱為卓越浪漫主義者的海涅卻成了歷史上第一個嚴厲痛斥浪漫主義的詩人。海涅的觀點集中表現于其名作《浪漫派》。該書撰寫于1836年。海涅鄙斥浪漫主義是因為他對基督神學的痛恨,也是因為施勒格爾等人對浪漫主義的推崇。海涅看出,在施勒格爾等人對浪漫主義的頌揚中,包含了對中世紀亡靈的呼喚:“在中世紀所有的這些詩歌作品中,都有一個鮮明的特點,由以和希臘人及羅馬人的詩歌區別開來,根據這種區別,我們稱前者為浪漫詩,后者為古典詩”;[7](P19)從浪漫主義的詩歌中,“我們看到它那痛苦大睜的眼睛深處,它用它那經院哲學的羅網突然把我們纏綁起來,一下把我們拖進中世紀神秘主義的愚妄深淵”;[7](P18)18 中世紀在德國復興了,成了一個新興的派別,“這個派別我們稱之為浪漫派,奧古斯特·威廉·施勒格爾和弗里德利希·施勒格爾兩位先生是這一派的總管”。[7](P38)施勒格爾的浪漫主義同中世紀神學關聯是歷史事實。但海涅由此而完全否定浪漫主義卻是今天的學者們無法接受的。今天我們讀海涅對浪漫主義的攻擊可接受的應該說正是這種攻擊中所包含的對浪漫精神的弘揚。海涅從推崇感性生命的角度來斥責中世紀神學和施勒格爾的浪漫主義。他說,“掙脫抽象空洞的基督教道德鎖鏈”之后,選擇的應是:“歡天喜地地沉湎于備加贊美的感性極樂世界”;應是象古希臘作家和歌德那樣的創作和生活:“熱忱地投向希臘歡快的大海”,[7](P26)“像兒童一樣純真無邪,像老人一樣充滿智慧”,“像綠色的海洋一樣清澈透明”,“像天空一樣奇異變幻莫測。”[7](P78)對感性生命的推崇:這就是海涅的浪漫主義。海涅在歷史上被稱為浪漫主義詩人,主要的原因應該說也就在這里:他是塵世的歌者。
三
施勒格爾-海涅的解讀是詩藝哲學的解讀。這一解讀以詩與生存的同一設定了詩藝在人類生活中的中心地位。進入20世紀,詩藝的中心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人們已不再期待通過詩魂的喚醒來改變社會、改變人生。與之對應的是,浪漫主義超越詩藝的、在廣闊深邃的人類生存領域中實際已發生的影響正在清晰地顯示出來。這兩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把浪漫主義的解讀引向了超越詩藝哲學的新的范式。
出現于20世紀初的施米特的《政治的浪漫派》代表了這一“新范式”時代的到來。施米特創建的是政治哲學的浪漫主義。在施米特看來,浪漫主義是一種政治哲學。“浪漫運動的擔綱者是新興市民階級。”[4](P11)浪漫運動“貫穿于 18世紀反對占支配地位的貴族教養的斗爭。”[4](P12)那么,何謂作為新興市民階級運動的浪漫主義的“浪漫”呢?施米特有明確的定義:浪漫即主體化的機緣。“浪漫派的態度可由一個概念即occasio得到清楚的說明。這個概念能夠譯成‘機緣’(Anlab)、‘機會’(Gelegenheit)、大概也能譯成‘機遇’(Zuffall)。然而真正的含義是通過一種對立而獲得的:它否定causa(原因、理由)的概念,換言之,否定可計算的因果性力量,所以也否定一切固有的規范。它是一個消融化的概念(ein auflosender Begriff注意:有打出的字母),因為,凡給生活和新事物帶來一致性和秩序的東西——不論它是初始原因的機械的可計算性,還是目的性或規范性的關系,都與純粹機緣的觀念不相容。”[7](P15)“機緣論”的主要意思是:世界和人生是由機遇和偶然構建的,不是由因果規律、必然性、既定原則決定的。機遇或機緣是主體的行為和遭遇;這一遭遇和行為是由主體自身決定的,不受客體的支配。因此,機緣論又是主體化的。“主體化的機緣論”意味著:“浪漫的主體把世界當作他從事浪漫創作的機緣和機遇”。[7](P15)施密特的主體化的機緣論無疑是經典性的。大到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小到張愛玲所欣賞的小男孩在人群稠密的鬧市騎自行車時雙手撒把輕捷閃過的身影,或者風華麗的年輕女孩奔放于林中路時“我幸福”的純情告白,所有在人類一切可用“浪漫”一詞加以描述的行為和心理中,可以說都能看到“主體化機緣”的作用:因為那里面都有源自主體特質的既不受束縛又高華美麗的率性和純真。
羅素的浪漫觀代表了20世紀中期歐美學界的浪漫觀念。羅素的解讀側重于心靈哲學的范圍。《西方哲學史》下卷第二篇以專章論浪漫主義運動。這種打破傳統哲學史敘事方式的安排足見羅素對浪漫主義的重視。第二篇的題目是“從盧梭到現代”。把盧梭視為浪漫主義的始作俑者,而且在此篇一開始就論浪漫主義,這表明:在羅素看來,浪漫主義是開啟現代西方歷史的運動。現代西方歷史的浪漫特征何在?羅素說,特征在于張揚審美的激情。“浪漫主義運動的特征總的說來是用審美的標準代替功利的標準。”[2](P216)浪漫主義“贊賞強烈的熾情”;“浪漫愛情,尤其在不如意的時候,其強烈足以博得他們的贊許”。[2](P221)因為強烈的情感大都有破壞性,因此,“為浪漫主義所鼓舞的、特別是為拜倫式變種的浪漫主義所鼓舞的那類人,都是猛烈而反社會的”。[2](P221)情感的強烈性,情感在心理上的恒定性,詩意和幸福情感的享受性,情感對自我和他人、對社會存在的巨大影響,包括痛苦在內的情感既反目的又讓自我無可奈何的特性等等,應該說是導致浪漫主義高揚情感的主要原因。除了情感的確認,羅素的心理學解讀還進入了本能和無意識的層面:“浪漫主義觀點所以打動人心的理由,隱伏在人性和人類環境的極深處”;“浪漫”的感覺即是在“推開”種種對自我的“約束”、以及“平息”“內心的沖突”之后所獲得的“新的元氣和權能感”,所獲得的“登仙般的自我生命的飛揚”體驗。[2](P221)
伯林對浪漫主義的解讀因其深刻性、也因其具有更加切近的當下性而特別具有意義。伯林反對羅素式的心理學范式。他斷言:“情感不是浪漫主義的核心”;把情感看作浪漫主義的核心“是許多歷史學家和批評家犯的一個大錯誤”。[3](P208)伯林反情感論不難理解,因為他選擇的是道德哲學的范式。伯林與羅素的另一區別是,他對浪漫主義有更多的肯定和同情。伯林把浪漫主義看作是西方18世紀末出現的新的價值選擇。“新的浪漫主義的價值再估用動機的道德觀取代了結果的道德觀”。[3](P218)“動機道德觀”的內涵是:“崇拜真誠和純潔而不是效率以及探索與知識的能力;崇拜自由而不是幸福;崇拜沖突、戰爭、自我犧牲而不是妥協、調整、寬容;崇拜野性的天才、流浪者、受難的英雄、拜倫筆下的邪教徒、家神和惡魔,而不是被作亂者們的宣言和綱領嚇呆了的順從的、文明的、值得尊敬的或市儈的社會。”[3](P213-214)價值選擇當然會表現在情感上,但更重要的是表現在意志上、行動上。在浪漫主義者看來,“個人性格、意志,行為,這就是一切。”[3](P207)“人的真正本質不是消極接受——休閑、沉思——而是能動性。”[3](P207)成為人即是去行動、去制造、去創造、去做自由的人。“浪漫”如此以及如此的“浪漫”顯然是伯林所欣賞的,這種欣賞導致他拒絕羅素,也導致他雖然完全20世紀化了,但有著同19世紀初年的浪漫英雄們更為相契的情緒。
四
在上述思想家們經典性的審視和檢閱中,浪漫現象或浪漫主義已經呈現出了多樣化的形態,它給我們理解浪漫主義提供了多種啟示。首先,應該把作為語詞的“浪漫主義”和“浪漫精神”區別開來。威廉斯說,“浪漫主義的”(romantic)一詞源于“兩個可區分的意義脈絡:romances(羅曼司的傳奇故事)的內容與特色,以及the Romantic Movement(浪漫主義運動)”。[8](P418)中世紀的romances是用韻文書寫的、表現冒險、愛情、騎士精神的故事。在表現方式上romances充滿情感的渲染和豐富的想象力。the Romantic Movement是出現于18世紀末期和19世紀初期的文化運動。威廉斯的話說出了浪漫主義一詞的多義性。可以補充的是,作為概念語詞,浪漫主義遠不止是威廉斯所說的兩種理解。浪漫主義有更多的“所指”:它可以被理解為發生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文學思潮;可以被認為是18世紀以來的政治、思想、文化運動;它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中世紀末期即已出現的一種文學范式(羅曼司);而有的思想史家則認為它是廣泛存在于漫長的人類歷史生活中的一種機制。承認作為概念語詞的“浪漫主義”在其實際使用中已有多種“所指”,卻并不排斥從特定視角出發的對“浪漫精神”的解讀。前者是已有的語言事實,后者是思想史研究的任務。這就是區分兩者的意義。
其次,對浪漫“精神”的理解應有更加開放的視野。浪漫精神并不只屬于羅曼司和浪漫主義運動,它可以在更加廣闊的時空背景上確認。威廉斯解讀浪漫主義的時候說,the Romantic Movement中的romantic一詞承繼了romances中的“自由解放的想象力”和“強烈情感”這兩個方面的意義,但又注進了romance沒有的新的內容:其一,對強烈情感的關注偏向情感的“新奇性”和“真實性”。其二,強調“從規則與慣例中解放出來”的內涵。其三,重視非理性、潛意識、主體等人性內容和傳奇、神話、民間歌謠等文化形式。威廉斯談到的“想象”、“情感”、“從規則與慣例中解放”這一類浪漫的“精神品質”和行為方式應該說是隨著人類的產生就已經出場了的。俄底修斯的十年飄泊,忒修斯尋父時的莊嚴宣誓,就都是典型的浪漫之舉。施米特說,浪漫情緒也許見之于“在一個灑滿月光的甜蜜夜晚為了上帝和世界而變成抒情的狂喜”,也許“是因塵世的疲憊和世紀病而嘆息、悲觀地撕裂自我、抑或瘋狂地鉆進本能和生命的深淵”。[4](P18)如此情緒和感受在哪一個時代不曾萌發呢?
與廣闊的時空性對應的是,浪漫精神是跨學科領域的。除了突出地出現在文學文本中,浪漫主義還是哲學、美學、心理學、政治學、倫理學、思維科學的共同主題。現代學術思想對浪漫主義的廣泛研究已經充分地證實了浪漫主義的跨學科性。也正是因為有這種跨學科性,伯林才把浪漫主義看作是整體性地改寫西方歷史的第三次觀念變革。浪漫主義的跨學科性從一個角度說明了浪漫主義的無法定義,導致了“無法定義浪漫主義簡直是這個世紀的恥辱”[1](P230)這樣的懊惱的出現。洛夫喬伊甚至提出,不應該再使用romanticism這一單數的詞語,而應該用它的復數形式:romanticisms。后者“已經表示許多東西,因此單就它本身而言,它已經沒有意義了”[1](P230)
浪漫主義要求我們在理性地審視它的時候,更多地注意它的非理性特征。浪漫主義并不只是理性的思考,并非只是以明確的信念、觀點、原則、理論表現出來的精神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浪漫主義是由情緒、感覺、無意識、本能沖動以及相應的行為方式和身體結構凝聚而成的。如果說,理性的解讀必然眾說紛紜,因而只存在復數形式上的浪漫主義;非理性層面上的浪漫主義倒是可以具有同一性的。理解這種同一性是我們言說浪漫主義的一個基礎。非理性的浪漫主義之所以具有同一性,原因就在于它不是概念的言說。不同的出發點可以導致同一的結果。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意志可以凝結成共同的情緒。當我們從情緒、無意識,而不是從明確的理論觀點出發來解讀浪漫主義的時候,就可以賦予浪漫主義一種或某些同一的品格。切斯特頓說,浪漫主義這個詞就是對浪漫主義的最本質的表達。[1](P231)切斯特頓的所謂最本質的浪漫主義應該就是具有深層意義的情緒、無意識的浪漫主義。由此,我們更關注浪漫主義“精神”而不只聚焦于浪漫主義“觀念”,因為前者可以更多地著眼于浪漫主義的情感、態度、無意識及其所構成的同一性體驗
從既往的經典解讀中,我們還可以獲得的另一啟示是:應該更多地從否定性上理解浪漫主義。施米特說,機緣的真正含義是通過對立獲得的。[4](P15)施米特在這里提示了一種解釋學的方法。有必要在修改施米特觀點的基礎上將他的“對立論”改造成為解讀浪漫主義的一種基本的思維方式。我們首先需要的應該不只是“通過對立”來“獲得”浪漫主義的肯定性“含義”,而應該是直接在“對立”的層面上理解浪漫主義。浪漫主義的在場首先就體現在它同自身宿敵的對立之中。浪漫主義是在挑戰中產生、在挑戰中成長的。它就是它同它宿敵的對立,它對宿敵的挑戰。這樣的理解意味著賦予浪漫主義以真正的歷史性、現實性。循著這樣的思路,才可以明白,浪漫運動何以出現在18世紀末,又何以在19世紀遭遇沉重打擊時仍然“負隅頑抗”。從對立的角度理解浪漫主義,也就是從功能上、而不是從實體上理解浪漫主義,也就是把浪漫主義視為否定的、革命的功能。現代學術思想認為,功能高于實體,功能概念具有更高的哲學品格。功能與實體的互不可分決定了二者的同一。但在二者的同一中,功能具有主導性。實體最終由其功能構成;某種特定的功能一經產生可以脫離原在的實體以“異形”的方式出現:這兩方面都是功能主導性的體現。浪漫主義在19世紀初取得煊赫地位、形成巨大影響之后,實際上就逐漸消失其原來的實體形態,而以新的方式、以類似于中國古人所說的“借尸還魂”式的方式出現。雖然,功能并不能只從否定角度來理解,功能同時還是建設性的,但后浪漫主義時代的浪漫主義的否定功能應該是我們理解19世紀以來的浪漫精神時需要特別關注的一個維度。指出這種“特別關注”的重要性是本文的任務。由此,本文不擬再進入對“后浪漫主義時代的浪漫主義的否定功能”的具體闡釋。
[1][美]羅蘭·斯特龍伯格.西方現代思想史(劉北成,趙國新譯)[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2][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馬元德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3][英]以賽亞·伯林.現實感(潘榮榮,林 茂譯)[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4][德]卡爾·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馮克利,劉 鋒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德]施勒格爾.浪漫派風格—施勒格爾批評文集[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6]劉小楓.詩化哲學[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
[7]海涅.浪漫派(薛 華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英]威廉斯.關鍵詞[M].北京,三聯書店,2005.
Romanticism:Modern Fate,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and Enlightenment
ZHANG Wen-ch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Romanticism is rejected by the direct social mind of people in 20th century,but at the same time still develop as a deep cultural trend.The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of romanticism by Schlegel,Heine,Schmitt,Russell,and Berlin provided much enlightenment.It showed the importance of deferenciating romantic spirit from romanticism as a word,and expects more open understanding of romanticism.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romantic spirit should especially be focused on romanticism’s tributes of its transcending particular time-space,its surpassing particular subject,its irratiopnality,and its negativity.
romanticism;emotion;occasion
B83-06
A
1000-2529(2010)02-0097-05
2009-10-21
張文初(1954-),男,湖南長沙人,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責任編校:譚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