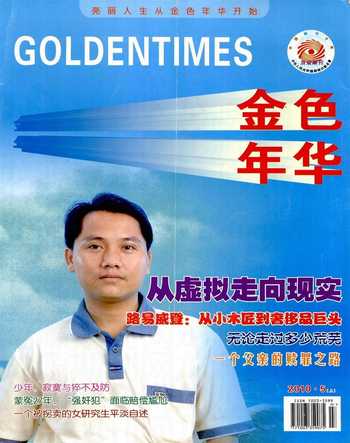點一盞燈 問暖漢旺
金 丹
“到目前為止,90%的人都認為:王琦,你做這件事情不切實際,對你一點幫助沒有。”2月9日晚,提起他和隊友們去四川地震災區過年的活動計劃遭到大量反對時,那個名叫王琦的高個子男生非但沒有顯出沮喪,反而信心十足。
“我們真誠地期望更多的人能參與進來,那里需要我們的關注,需要我們的支持,不只是金錢,更是心靈的關懷和體貼;不只是口頭,更是行動。”一個月后的3月7日,王琦和隊友在學校舉行總結交流會,向老師和同學們介紹了他們此行的經歷和收獲,并發出了上述呼吁。
王琦、蔣欽、李璟寒、王沂淳,這4位來自北京大學體育教研部的研究生和來自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大四的丁子凌一起,自發在2010年春節奔赴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災區之一的四川省綿竹市漢旺鎮,與當地的居民和留守志愿者一起過年。
“大學生歸根結底要服務社會,他們的行為,在這日益冷漠的時代,如同給靜水投下一枚石子,這是一次真誠的、無私的呼喚。”北京大學體育教研部主任郝光安這樣勉勵他們。
“沒有想太多,只知道一定要去,那是一份心愿”
“大約在一個月以前有了這個想法。第一是快過節了,我想春節放假的時候應該做點什么事兒,我和大家聊天時聊到了四川,我就想,可以為他們去做點事兒。”出發前一晚,活動發起人王琦在和中國青年報記者談起去四川災區和當地居民一起過年,他的座位邊上,是滿滿兩塑料袋剛采購來的明信片、記事本、T恤衫等印有北大標志的紀念品,準備發給參加活動的孩子們。交談期間,蔣欽又帶過來一個大黑袋子,里面裝的是給孩子們準備的體育活動的道具——“同心鼓”。
“我一想,快過年了,我們該為誰做事兒呢?于是就想到孩子了。過年的時候可能沒有人陪他們,他們在那里會倍感孤獨。哪怕我們只是陪他們過個年,只是陪他們待那么幾天,給他們送一些溫暖,不讓他們感到孤獨。”這位北大賽艇隊的高個子男生說。
“到災區陪孩子們過年”的想法得到了北京大學體育教研部一些同學的認同,在與家人商量后,王琦和另外3位同學最終確定能夠成行。在確定了與災區的孩子們“同度溫暖新年,沐浴體育陽光”的活動主題后,體育教研部的同學們還于1月27日在北大未名BBS上發帖招募志愿者。原本已計劃好去廈門過節的丁子凌在即將預訂旅店前恰好看到了這個帖子——“BBS上王同學的一個帖子改變了這一切。我絕對不會后悔,把這些日子給了那個叫漢旺的地方,給了那些也許再不會相見的老人孩子,給了四個像家人一樣的同伴。”丁子凌后來在她的日志中寫道。
按計劃,他們將在2月12日(農歷臘月廿九)上午在成都會合,在當天下午啟程前往漢旺,并在大年三十和已經聯系好在漢旺當地提供志愿服務的愛心組織一起吃年夜飯。但在前期的籌備過程中,他們還是遇到了很多“坎兒”——“想拉贊助,但結果拉到自己頭上來了。”王琦在提起籌集活動經費的過程時有些哭笑不得。而家人和很多朋友對他們不回家過年團聚都不理解。
“家人其實挺想讓我回家過年的,因為由于要打比賽、訓練,我已經好幾年沒回家過年了。后來我跟家里說了自己的想法,他們也只能忍一下,說你去吧,其實心里還是挺不樂意的。作為家長,尤其在北方,總是希望孩子能回家過年的。”王琦說。
除了王琦,其他4人此前都沒有不在家過年的經歷。為了能讓活動順利進行,李璟寒和王沂淳各自提前回家,先陪陪家人。
“父母還比較開通,同意我去漢旺過年。主要是先陪陪老人。”家在四川達州的李璟寒告訴記者,雖然他是四川人,達州在地震時也有震感,但他在此前還從沒有去過漢旺等地震災區。“后來,家里還希望我能把年紀稍小、正在念中學的兩個表妹也帶過去體驗一下。”
為了能按時到達成都,王琦和蔣欽在春運期間凌晨3點出發去火車站買票,一直排到上午9點才買到普快列車的3張硬座車票。“票價是216元,要坐30個小時。”王琦說。好在他們在出發前又買到了該趟列車臥鋪票,并把硬座車票轉讓了出去。“當天晚上7點的火車,下午4點拿到(臥鋪)票。轉出去又轉進來的,蔣欽差點被當作‘黃牛抓起來。”丁子凌說。
2月10日晚。帶著六七件大件行李的王琦、蔣欽和丁子凌從北京西站出發前往成都;2月12日,李璟寒和王沂淳分別從四川達州和貴州貴陽出發前往成都。
“我們沒有想太多,只知道一定要去,那是一份心愿。”王琦在3月7日下午的活動總結交流會上說。
體育,也許是能給孩子們快樂的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
由體育教研部同學為主的團隊把送溫暖的主題定為:和孩子們一起開展素質拓展項目與體育活動。在活動的策劃中,他們安排了盲人方陣、穿越繩網和信任背摔等游戲。但正月初四那天來參加活動的孩子年齡大小不一,“出于對孩子力量、身高等因素的考慮,有些游戲不能做,我們臨時做了調整。”李璟寒說。
記者在他們為本次活動制作的視頻短片里看到,隊員們組織孩子們參與了同心擊鼓、“信任之旅”等素質拓展游戲,還和孩子們組隊踢了一場足球友誼賽。其中,“信任之旅”的游戲由兩人合作。兩人被系在一起,一人扮演“盲人”,被蒙住眼睛,但可以說話;另一人雖然沒有被蒙住眼睛,但不能通過說話提示同伴。游戲要求兩人一起穿越高臺、溝塹等障礙,抵達終點,以此建立朋友之間的信任,并培養參與者關愛別人的意識。
游戲中,李璟寒問一位在游戲中扮演“盲人”的小朋友“怕不怕”,得到的答復是“不怕”。他追問“為什么”,小朋友用手指了指和自己系在一起的同伴說:“有這位朋友。”因為在前一個回合中,該小朋友扮演的是“指路人”的角色,他顯然已經明白:朋友間的信任有助于大家共同克服困難。
讓隊員們感到欣喜的是,他們和當地愛心組織一起舉行的活動不但吸引了孩子,許多家長也來到了現場,有的一起參與游戲,也有的就坐在場邊,一邊織毛衣,一邊看著自己的孩子在場地里快樂地游戲。
在隊員們看來,體育,電許是能給孩子們快樂的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而當地愛心組織負責人事后發來的郵件更讓他們感到高興。郵件中寫道:“這些天我們一直在想,你們的這次活動真的給我們機構帶來了一種新的思路,那就是體育不僅可以增強一個人的體質,而且確實能改變一個人的精神面貌……還記得大年初四的體育活動嗎?雖然孩子不多,但有很多家長也加入了進來。其實這里的人真的很缺少可以運動的場所和玩伴,有很多人正是因為閑著無聊才會去干一些不好的事情。還記得叫你哥哥、哥哥的小朋友嗎?現在他幾乎天天來我們這里,當初做游戲是膽小的小孩子,如今是那么的勇敢和強壯,感謝你們,感謝體育精神帶來的這一切改變。”
“當地的愛心組織已經表示愿意和我們合作,在心靈康復中加入體育的元
素。我們也在考慮在‘六一節的時候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李璟寒告訴記者。
先點一盞燈
隊員們在漢旺的“問暖活動”并不只有“沐浴體育陽光”這一項。大年初一到初三,他們還去當地的兩所敬老院和一些板房區的家庭里拜年,和當地居民一起拉家常,向他們贈送慰問品。
讓隊員們牽掛最多的,還是災后重建的進程。他們看到,漢旺新城的重建腳步比別的震區邁得更快,產業重建和教育恢復也都進展順利。但他們關注的是,物質層面的重建在震后短期內已經初見成效,但精神的重建和心靈的恢復可能需要長期的投入和關注。
2009年3月25日,《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刊發報道《哄地來了,倏地走了》,反映了地震災區的心理咨詢工作無序的問題。李璟寒告訴記者,目前漢旺還是很缺愿意長期扎根在那里的專業心理治療師,“更多的是來了又很快走了,沒有太大作用,甚至還會有副作用”。在他看來,心理上的治療需要長時間的跟蹤研究,而心理師的來了又去,只是反復地向被幫助者捅刀子,可能會引起更嚴重的心理問題。當地的愛心組織負責人也告訴他,“這里的人并不是很缺乏物質上的幫助,他們的心理狀況更需要去關心,這是我們這些草根組織希望做的。”
隊員們短暫的問暖活動好像飛過漢旺的一盞孔明燈,在路過時帶給當地居民光和熱;當地愛心組織開展的志愿工作好像蠟燭,可以維系一定時間的光亮;但當地居民的心靈康復需要的是一張電網,能夠源源不斷地給當地居民輸送溫暖。現在,有了燈,也有蠟燭,但電網還有待搭建。
“能不能有一種比較合適的長效機制,給當地居民提供心理上的長期指導?”隊員們在總結里這樣寫道。他們在總結交流會上也提出類似的問題:北大學子的社會公益活動如何走向長久的堅持?如何建立起適合北大學子參與的社會公益平臺?
對此,參加了交流會的北大學生鐘藝告訴記者,她建議建立一個學生公益活動的網絡平臺。這個平臺需要由一些人挑頭先行建起來,需要學生社團的參與并結合NGO的廣泛參與。“對于一些需要幫助的地區,前人去過的地方,留下經驗供后人繼續補充借鑒。”
在蔣欽看來,源于自我的坦誠和內在的真實。會將一次簡單的“問暖”形式內化為一種長久的公益堅持。
“在我看來,一個內心黯淡的人,終究難以點亮別人心底的光明。于是,點一盞燈,先照亮自己。”蔣欽在總結中這樣寫道。
(注:NGO——在特定法律系統下,不被視為政府部門的協會、社會基金、慈善信托、不以營利為目的非政府組織、公司或其他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