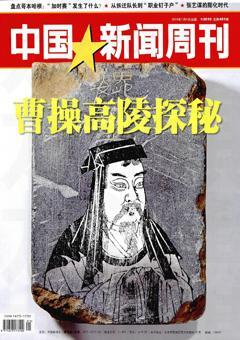張經武:"暗戰"布達拉宮
韓永



“他不僅是中央政府的代表,還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
1952年4月8日中午時分,一條距離西藏軍區作戰室100來米的小河邊,西藏軍區作戰參謀楊一真拿著望遠鏡,警惕地觀察著500米外布達拉宮的動靜。
此時,在布達拉宮內,一場眾人矚目的會談正在舉行,一方是十四世達賴喇嘛,另一方是中央人民政府首任駐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書記張經武。
8天前,張經武位于拉薩桑都倉的住所突然被上千人包圍。他們喊著“解放軍撤出西藏”的口號,在周圍的房頂上架起了機槍。那時距張經武抵達拉薩尚不足8個月。在他日后駐藏的十多年間,這樣的危險還會時有發生。
身陷險境
這起事件背后的組織者,是“人民會議”的代表。其背后是西藏地方政府兩個手握重權的司曹(達賴以下權力最大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員):魯康娃和洛桑扎西。在張經武1951年8月7日抵達拉薩時,他們沒有出現在歡迎的隊伍里。
張經武赴藏的一個重要使命,是做好對西藏上層的統戰工作。這也是他被任命為駐藏代表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統戰方面,張經武業績斐然:他曾以毛澤東“欽定”的紅軍軍事聯絡官的身份,在華北各省尋求抗日的盟友,爭取到了宋哲元、傅作義等地方實力派的合作。此后毛澤東又密令張經武再赴濟南,促使韓復榘釋放了400多名被關押的革命人士,即后來八路軍山東縱隊的骨干。
但張經武一到拉薩,就發現這次的挑戰非同以往。他在抵達拉薩第四天給中央軍委的匯報中說:“從側面了解,他們(西藏地方官員)對協議(“十七條協議”)第15條人事問題有意見。一般表示,解放軍來了,糧食很困難。此外,懷疑對宗教不利。貴族害怕分財產。”
張經武抵藏前,西藏的帕里宗宗本(地方官員,相當于縣長)雪康?索朗塔杰接到接待張經武一行的任務,他對此頗為猶豫。他聽到從境外傳來的消息,說“共產黨對西藏的地方官和喇嘛一個也不留”。此前,接待張經武的任務曾經交代給其他人,但遭到拒絕。“當時,我不相信共產黨,” 雪康?索朗塔杰說。
對張經武反對情緒尤為激烈的,是司曹魯康娃和洛桑扎西。后來張經武拜訪魯康娃,后者對他說:“過去清政府有一個入藏大臣也姓張(指張蔭堂),他只在拉薩設立了一個衙門,沒有帶什么兵,大家稱他‘張大人。現在又來了一個張大人,你何必帶那么多部隊?”
1951年,一個意圖西藏“獨立”的組織“人民會議”在拉薩成立。魯康娃和洛桑扎西公開對其表示支持,并敦促其向張經武“請愿”。1952年1月13日,魯康娃和洛桑扎西召集噶廈(西藏地方政府官員)開會,決定“采取武裝行動,把解放軍趕走”。
1952年3月31日,“人民會議”組織了上千人,武裝包圍了張經武的住所,擬定了一份請愿書,要求面見張經武。這份請愿書提出了三條意見:一、解放軍撤出西藏;二、反對改編藏軍;三、西藏原有制度不能變更。
除了第三條外,另兩條意見都是對《十七條協議》的顛覆。而張經武進藏的主要使命,就在于落實《十七條協議》。達賴此前也在1951年10月24日,以他本人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名義,表態擁護《十七條協議》。
西藏軍區彼時的作戰參謀楊一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張經武住所的守衛力量當時只有一個班,他們也在房頂架起機槍,以應對可能的突然襲擊。
獨上危城
張經武采取了兩種應對之策:他一方面召集噶廈開會,將包括幕后組織者在內的三位噶廈留在自己的官邸,讓舉事者不敢輕舉妄動;另一方面,張經武迅速將此事上報中央,尋求應對之策。
在張經武就任駐藏代表期間,事無巨細地向中央匯報成為一項制度。張經武的兒子張華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這種匯報有時候細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就算是建一所小學,也要匯報。”
解放軍裝甲兵工程學院指揮系主任盧繼兵是這段歷史的研究者,也是當年入藏部隊十八軍宣傳部長夏川的兒子。盧繼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中央政府當時對西藏政策的核心,就是爭取達賴集團。能否忠實地執行中央的政策,成為挑選駐藏代表的一個重要的考量。張經武過去曾多次擔當毛澤東的“私人信使”,無疑獲得了更多的信任票。
1952年4月5日,中央對這一事件的處理作出指示:爭取達賴,同時借機痛懲兩個司曹。“最好由張經武設法親自同他(達賴)商談處理辦法,使他覺得我們是信任他的。”
但此時的布達拉宮神秘莫測。達賴在這一事件中態度不明朗,而魯康娃和洛桑扎西就在達賴的身邊,張經武前去,有可能會自投羅網。
張經武還是決定去一趟。他說:“清朝政府先后派遣了78任駐藏大臣,被殺的不是只有一任嗎?我看那幾個反動分子還沒有對我下毒手的膽量!”
時任西藏軍區作戰參謀的楊一真告訴記者,當時軍區領導對這一事件的判斷是:對方殺害張經武的可能性不大,“他們還沒這個膽量,但對方扣下張經武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為此,西藏軍區進入了戰備狀態。楊一真奉參謀長李覺之命,在作戰室不遠處的一條小河邊觀察布達拉宮的動靜。
中午1時左右,楊一真透過望遠鏡看到,張經武開始進入布達拉宮的東大門,然后拾級而上,走向達賴的住處,身邊跟著一個副官、一個翻譯和一個警衛員。軍區為其精心挑選的一個警衛班被他留在了布達拉宮門外。達賴對張的這一舉動印象深刻,他曾表示:“每次張經武來探訪我,都把侍衛留在外面,即使他明知生命的神圣性。”
為了預防可能發生的意外,西藏軍區專門擬定了一個預案。“我們和張經武的警衛員約好,里面一有情況,就伸出來一面紅旗或者打一發信號彈。我在小河邊看到后,打三發信號彈,就等于進攻的命令。”楊一真說,當時解放軍在拉薩的部隊共有4個營,“他們(藏軍)人數比我們多,但我們戰斗力要強得多。”
此時,在布達拉宮達賴的臥室內,正在上演一場心理攻防戰。張經武首先向達賴介紹了騷亂的情況,繼而轉達了中央政府的態度:這次騷亂并非偶然,而是有個別人在幕后操縱,已構成對《十七條協議》的嚴重破壞,要求撤銷兩位司曹的職務,同時解散“人民會議”。
張經武態度堅決,而根據《中國共產黨西藏歷史大事記》記載,中央對此事已有了明確的指示:“不論騷亂是擴大,還是收場,我們必須借此次無理騷亂為題,盡可能將反動派痛懲一下。否則,西藏政局不能穩定,愛國分子不能抬頭,生產、貿易、醫藥、修路、統戰等工作均不能開展,我們將經常處于被動地位。”
“達賴在這件事上說了些來回話,”楊一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他一方面承認兩位司曹犯了錯,要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辦,同時又說這兩人是 “不懂事”,看能否給予寬宥,不撤這兩人的職務。而此時的達賴,年僅17歲。
達賴被認為是“說來回話”的表現,在1959年叛亂前夕再度發生。當時,他給中央政府代理駐藏代表譚冠三寫信,將叛亂描述為“反動的壞分子們借口保護我的安全而進行的危害我的活動”,并一再表示“正設法平息”。但達賴后來表示,寫信的目的在于“盡一切可能爭取時間”“希望借此再拖延一陣子” 。
令達賴失望的是,1952年,張經武沒有理會達賴的求情。他強硬地表示:“從即日起,本代表不承認魯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司曹職務,因而也就不再和兩人商討任何問題。”“請您命令噶廈從即日起在您的直接領導下與本代表直接辦公。”
毛澤東的“軟”與“硬”
張經武的這種強硬態度,為后來一件事的發生埋下了伏筆。1954年在京參加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期間,達賴曾經有過想換一位駐藏代表的意思。多位學者分析,引發達賴對張經武不滿的“禍根”,正是源于對那次騷亂事件的處理。
不過,在盧繼兵及《中央駐藏代表張經武與西藏》一書的作者宋月紅看來,張經武在此事件中的表現,幾無本人的意思表示,其一言一行的背后,都是中央政府尤其是毛澤東個人的指示。
據《張經武與西藏解放事業》一書記載,毛澤東曾在1953年3月致達賴的一封信中說:“張經武同志不僅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
現為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的宋月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這一時期中央的對藏政策,重點在于維持制度的現狀,以贏得藏族上層的信賴,等待民主改革的良機。
中央這一決策的背景,源于西藏上層對民主改革有著超乎尋常的敏感,以至于讓彼此信賴的建立顯得異常艱難,中間任何的風吹草動都有可能打破這種脆弱的平衡。1956年,部分駐藏官員受周邊省份民主改革的感染,對西藏的民主改革產生急躁情緒,提出“要在今冬明春在昌都和日喀則地區實行民主改革重點實驗”,并打算吸收培養大批藏族干部,同時抽調大批漢族干部進藏。對此,西藏上層中出現了不安情緒,昌都地區發生了局部叛亂。
此時,張經武正奉調在京休養,受命迅速返回西藏,領導西藏工委,堅決貫徹中央“6年(在藏不實行民主改革)不改”的方針。綜觀張經武的駐藏經歷,會發現他總是出現在中央的對藏政策亟需堅定執行之時。
但對西藏上層的不懈攻關,始終未能根本扭轉其對中央政府下意識的敵意。與張經武單槍匹馬說服各路軍閥聯合抗日的情況不同,西藏貴族很難被說服,很難放下對自身利益受損的顧慮。
毛澤東對這一狀況早已心知肚明。早在1956年11月,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當言及達賴去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2500周年活動是否會留滯不歸?他提醒大家對西藏的發展前景不要太過樂觀,“要估計到最壞的可能性。”毛澤東同時指出,即使達賴真的跑到國外去,也沒什么了不起,“我們的事業一樣會蓬勃向上。”
同時,毛澤東也在尋找最終解決西藏問題的良機。根據《黨史文苑》作者文鋒在《文韜武略——毛澤東與1959年平息西藏叛亂》一文里的記述,1959年1月24日,毛澤東在給西藏工委的一份指示稿中寫道:“在西藏地區,幾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總要來一次總決戰,才能徹底解決問題。”同年2月19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一封有關藏區平叛的信中說:“這種叛亂,有極大好處,有練兵、練民和對將來全面平叛徹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
毛澤東寫這封信后不到20天,3月10日,西藏一些地方官員以達賴去軍區看戲有可能被軍方劫持為借口,發動叛亂,并由拉薩迅速擴展到了西藏全區。達賴逃亡印度。毛澤東始終希望爭取達賴回國。1959年4月,他在接見班禪時說:“達賴叛逃了,這種事是我們所不希望的。但只要他們回心轉意,我們還是歡迎的。”1964年12月,中央作出了《關于撤銷達賴職務的決定》。
而1959年的這次叛亂,將西藏民主改革的進程至少提前了3年。按照原來對西藏改革的設計,至少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1958年~1962年),中央不打算在西藏實行民主改革。而中央政府內部的一個底線,是在整個第三個5年計劃期間都不實行民主改革。
為了領導這場改革,1959年5月,張經武再次離京赴藏。1959年3月15日,毛澤東在武漢東湖接見張經武時,給他吃了一顆定心丸。毛澤東說:“要相信90%以上的人民是站在我們一邊的。”
1952年4月8日,是西藏革命的前奏。下午3點左右,楊一真看到張經武從達賴的行宮走出來。他壓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以百米沖刺的速度跑向100米外的作戰室,告訴等候在那里的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政委譚冠三和參謀長李覺:“張代表回來了。”
4月26日,噶廈政府終于根據達賴的命令,發出了《宣布撤銷反革命組織“偽人民會議”后臺兩司曹職務的布告》。★
本文參考書目《張經武與西藏解放事業》
往事欄目郵箱:wangshi@chinanews.com.cn,歡迎讀者投稿或提供線索。
“十七條協議”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簡稱,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簽訂。具體內容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