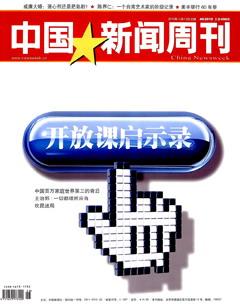讓農民帶著土地做城里人
黨國英
人們都說中國農村社會經濟事務復雜,豈不知它也有簡單的一面。復雜局面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有兩個顯著特點,一個是小農經濟,一個是計劃經濟。這樣的社會當然需要轉變,具體說,是把小農經濟轉變為高度城市化、工業化的現代經濟;同時把軍事管制體制轉變為市場化、民主化的經濟管理體制。完成這兩個轉變,我們遇到了特殊難題。
第一個難題是我們的農業生產落后,如果太多的人進入城市,城市需要的糧食就會增加,而農民減少以后產出的糧食卻會減少,中國人的吃飯會有麻煩。
第二個難題是我們為了發展工業,對城市有很多壟斷性的“福利”。政府的公共財政好像就是服務城市居民的財政,農民大量進城后,也要求同等的福利待遇,政府便說財政吃不消,至少大部分城市如此。
但是,這兩個難題并非“死扣”,中國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解這兩個扣的過程。
為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我們把農民從傳統集體經濟中解放出來,給了農民耕作的自由,加上科學技術的作用,一舉解決了吃飯的問題。現在的華北平原,一畝地的糧食產出是1949年的8倍左右。
農業效率提高以后,農村有了剩余勞動力,而城市經濟發展恰好需要勞動力,這時,我們又給了農民第二個自由,允許農民進城務工,做所謂“農民工”。于是,中國便成了有些人講的“世界工廠”,農民發現城里的錢“好掙”,流血流汗,拼命工作,制造了廉價的工業品,打開了世界市場,促成了資本積累,帶來了中國經濟繁榮。
然而,兩個難題都解決了一半。
中國人飯吃飽了,但農民靠農業掙的錢不多;來自農業的收入占農戶總收入的比重越來越低。小農戶的經濟規模小,一些技術不方便采用,以致中國農業的競爭力比不上發達國家。按我的調查,如果農戶經營規模平均在50畝以上,每畝地的綜合效益可能提高30%左右。這就要使農民的土地通過流轉,有所集中,將經營規模適度提高。但是,我們的土地承包制不是太方便土地流轉,承包期限最長30年,期限到了怎么辦?麻煩!我把承包制改革叫做“半截子產權改革”,主要就是因為這個麻煩。
農村剩余人口進城問題也解決了一半。農民工在城市工作,但他們的根留在農村。本來中國有城鄉二元結構,現在城里也有了“二元結構”:農民工和城里的原住民權利不平等。農民工被統計局統計為城市“常住人口”,但他們沒有被真正被當做城里人對待。有學者把這種城市化叫做“偽城市化”,多少有點道理。
近些年還有另一個麻煩。地方政府為了發展工業、擴張城市,想廉價獲得土地,于是瞄準了農民的耕地和宅基地。而國家實行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又方便了政府拿地,農民沒有真正的土地財產權,爭不過政府。于是,農民便想出了很多法子抗拒,有時候還用極端的辦法抗爭。這樣又產生了農村社會穩定問題,讓中央憂心。
怎么辦?中央政府先是在2005年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張,想要在城鄉之間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后來發現把大量人口留在農村搞不好新農村建設,還是不得不遵守基本經濟規律——必須在中國實現的高度城市化。2008年,中央正式提出了要搞“城鄉社會經濟一體化”,推進城鄉統籌發展。這樣,中央便部署了重慶和成都搞統籌城鄉發展綜合配套改革實驗,試圖解決上述問題。
以成都為例,部署了“三個集中”,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農民(本應該是基本脫離農業的農民)向新型社區集中,土地向適度規模經營集中。這種集中不只是簡單的空間變換,基本做到了給城鄉居民相同的權利。留在農業領域的農民少了,土地相對多了,農業的效率也提高了。成都試驗的另一個亮點,是下大力氣做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把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固化為土地財產權,這樣就方便了土地流轉,有利于農村土地綜合整治,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前不久,成都市還宣布,要在全成都的轄區內實現農民的“市民化”,并且允許農民保留土地,不因為農民變市民就喪失土地。這不像有的地方那樣,硬要求農民用土地換社會保障、用宅基地換城市樓房。農民要不要換,以什么比例換,不和農民的權利實現捆綁在一起,各算各的賬,給農民自由。這個思路不是搞強制,而是讓農民自愿選擇,當然不會讓農民有被剝奪感,有利于社會穩定。
成都的目標是,今后一個農民和城里人的區別僅僅是職業的區別。為了這個目標,成都用了6年的時間,市縣兩級財政投入了594.8億元,宣告要在2012年底實現城鄉戶籍統一。給農民以市民待遇,這是中國歷史的偉大一步。★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