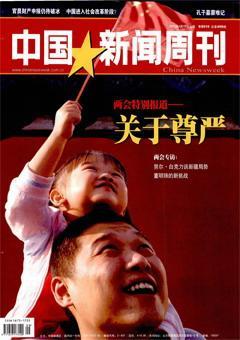愛金牌更愛運動
洪 鋼


對待奧運會,加拿大人追求勝負,也追求塑造民族認同,但是除此之外,他們還擁有另外一些,比如極高的冰雪運動普及率,比如對公平競賽的維護,比如對運動本身的熱愛。
溫哥華是個氣候宜人、風景秀麗的城市。世界上很少有哪個地方,能夠像溫哥華那樣一年四季北望雪山、西抱大海,既得北極空氣造就的冰雪晶瑩,又享赤道暖流帶來的和風細雨。多年前第一次去溫哥華回來,就頻頻向朋友形容那里的氣候“好到你不出門跑跑步、騎騎車、遛遛狗,就會覺得暴殄天物,浪費了好空氣、好陽光”。溫哥華只要不下雨必是風和日麗,公園、海邊滿是跑步、騎車鍛煉的人,像我等游客,腿腳健全卻在閑逛,會覺得自己是個異類。那里的空氣、氛圍,都讓人蠢蠢欲動,
彼時溫哥華已經在申辦2010年冬奧會,一年后該城以絕對優勢贏得舉辦權,筆者也得到故地重游的機會。在奧運氣氛的籠罩下,更深切地感受到加拿大人對體育的了解、喜愛,體會到冰雪運動已經像衣食住行一樣存在于他們每個人的生活中。
人人都有首金“情結”
2010年冬奧會已經是加拿大第三次舉辦奧運會,在此之前,他們從沒有機會作為東道主奪得一枚奧運金牌。本屆比賽,他們要打破這個宿命。
期望被重點寄托在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選手、都靈冬奧會冠軍珍妮弗·海爾身上。到加拿大之前筆者對她一無所知,因為雪上技巧非我國強項,無人問津。但到了溫哥華之后,當地各體育頻道播放的宣傳片、采訪中,這位美女不斷出現,不由得你不知其何許人也。然而比賽并不遂愿,上屆冠軍盡管表現優異仍然屈居第二,金牌被美國人奪走。不過海爾的銀牌仍然占據了當天報道的相當篇幅。
略顯失望的媒體還沒來得及醞釀下一個熱點,在都靈冬奧會時僅獲第11名的23歲小將亞歷山大·比羅杜就在第二天的男子雪上技巧比賽中勇奪東道主首金,電視臺的宣傳攻勢像禮花彈一樣被點燃了。比賽重播、演播室專訪、專題介紹,各個體育頻道循環播放,觀眾完全不用擔心錯過了任何一段,只要換個頻道,這個還未脫稚氣的帥小伙馬上又出現在你眼前。亞歷山大取代珍妮弗,成為了那兩天的電視明星。
奧運會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現代國家和民族的一種精神圖騰,每個國家都需要奧運金牌去凝聚民族認同、激發民族自信。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的移民國家,與美國這樣的經濟、文化強鄰為伴,加拿大十分需要確立清晰獨立的、全體加拿大人認同的民族身份,所以在他們的媒體宣傳中,自然也會和中國一樣去放大每一枚奧運金牌的影響力。在這個層次上,加拿大和中國,對于奧運會的認識毫無二致。
不過我們也看到,加拿大媒體重視金牌,卻并不“唯金牌論”。當地電視體育頻道的排行榜上,始終按獎牌總數排序,盡管東道主最終以14金獲金牌總數之最,但媒體上始終老老實實地把自己列在美國、德國等獎牌大戶之后,從未以金牌榜排,列出自己高居榜首。
三個小店里的經歷:運動氛圍無處不在
到達溫哥華不久,筆者就前往惠斯勒山下采訪(注:該雪山1992至1995年,連續四年獲滑雪雜志SnowCountry“北美第一滑雪勝地”及“最佳度假勝地設計”等稱譽)。我們選中一家銷售、維修滑雪器材的商店,想要拍攝如何給滑雪板打蠟。他們的店里擺滿了送來磨邊、打蠟的滑雪板,完工的板上貼著收費單,從幾十到上百加元不等,生意不錯。兩住經營店面的小伙子對滑雪如數家珍得超出我們的想象,從職業高手到業余級別的滑雪板選擇,從普通愛好者的滑雪蠟到貴得嚇人的頂級快速蠟的成分差別,從高山滑雪的速降、super-G到單板滑雪的U型池選手的不同需求,其專業精深程度超過筆者認識的任何國內同行。
在這家冬天經營維修滑雪器材、夏天經營維修自行車器材的小店里,我們學到了迄今為止幾乎全部的滑雪知識。
冬奧期間到冰壺賽場附近的一家食品店買面包,店主是一位六十多歲的白人大嬸,她和相熟的顧客閑聊中,冒出一句“我喜歡看冰壺,那是一項考驗心理的運動”,作為冰壺解說員,我自然要多問幾句。大嬸強調,她看冰壺比賽,就是看選手們玩“最后的心跳”,最后一投之后,結果往往天翻地覆,可真是一項美妙的“mental garlic”。
到了冬奧會最后一天,加美爭奪男子冰球金牌的時候,筆者在商店購物。售貨員是一位日裔中年女性,聽到店外不時傳來的歡呼,她告訴我今天可是加拿大人的big day,因為有冰球決賽。我問她是所有加拿大人都喜歡冰球么,她說幾乎是,只是近年來移民增多,這些新移民更喜歡足球,但只要是加拿大土生土長的人,大都對冰球狂熱地喜愛。她說,溫哥華所在的BC省冬天氣候溫暖,所以看不出來,但是在加拿大東部非常寒冷的地方,父親們每到冬天都會在自家后院潑水凍冰,帶著孩子在上面玩冰球。
在這三家經營內容不同的小店里,記者遇到的年齡、性別、種族不同的人,但他們無一例外,和人談起運動都遠非一知半解的水平。即便是那家滑雪器材商店,經營者的專業程度,實際上已遠遠超過了他們工作所需。給人觸動更深的是每個人對運動的描述都輕描淡寫,傳遞給筆者一種感覺,他們尚在普通加拿大人平均體育認知的中下水準。
冰壺賽場內外:以武會友
冰壺起源于蘇格蘭,卻興盛于加拿大,在加拿大被視作僅次于冰球的第二大冬季項目,俱樂部注冊會員占全國總人口數的3%,在全球每10個冰壺愛好者中,有7個來自加拿大。如果拿乒乓球來類比的話,3%的比例意味著中國要有3900萬人打乒乓球才能和加拿大的冰壺普及率相當。據中國乒協官方網站資料顯示,“目前我國經常打乒乓球的人口約一千多萬”。
2010年冬奧會,奧運冰壺終于第一次來到了最熱愛它的國家。組委會興建了三倍于以往奧運冰壺賽場的溫哥華奧林匹克中心,賽場位于市中心,并且全程提供所有場次電視轉播公用信號。果然,從比賽第一天到最后一天,能容納5600人的冰壺館場場爆滿。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幾乎全部觀眾都會看到所有比賽全部結束。而不管加拿大隊是否還在場內。
比賽第一天,旁邊的加拿大解說員問我們來自哪個國家,并告訴我們說他本人也是一個冰壺愛好者,他們非常高興看到越來越多的人喜歡冰壺。當中國女隊終結東道主的連勝之后,場內的志愿者主動上來搭話,真誠地向我們表示祝賀,贊揚“中國女隊可是這次比賽第一個打敗加拿大隊的”,我們只好禮貌地回答說“但你們的凱文·馬丁(本屆冬奧會男子比賽冠軍隊主將)是不可戰勝的”,賓主相言甚歡。相比之下,中國某些人在短道速滑上與對手的對抗心理似乎已經超出了體育范疇,以武會友的精神蕩然無存,大國心態更無從談起。
加、挪男子決賽進行中,挪威隊主將厄爾斯魯德在關鍵投球時,觀眾席上突然響起了一個怪異的喇叭聲。間接造成他投球失誤,此時全場爆發一片譴責的噓聲,之后那個喇叭再也沒敢出聲。實際上除了這一次不和諧音,冬奧運比賽期間現場觀眾沒有向任何選手喝過一次倒彩、沒有有意干擾過任何選手比賽,激烈對抗僅僅出現在冰壺與冰壺之間。
對于喜愛的冰壺,加拿大人當然期望自己的選手取得好成績,但他們更期望看到精彩的比賽。與運動本身所具有的競爭、拼搏、技術、戰術、懸念等魅力比起來。勝負并不是最主要的,這句話哪個國家的人都會說,但是加拿大人能在12天的冰壺比賽中,用自身行為真正表達出這種認識,卻不是誰都能做到的。
也許是因為這是筆者第三次現場報道奧運會,也有了更多的感受和思考。對待奧運會,加拿大人有冰球賽場上戰勝強敵后的狂熱,也有對首金的渴望和連篇累牘的報道,他們當然追求勝負,也追求塑造民族認同,但是除此之外,他們還擁有另外一些,比如極高的冰雪運動普及率。比如對競賽成績的清醒認識;比如對公平競賽的維護,對戰勝自己的對手的欣賞;以及對運動本身的熱愛。
奧運會實際上是由體育文化交流和名次爭奪兩條主線組成的共同體,我們可以因為有金牌爭奪而喜歡奧運帶來的大喜大悲,我們更應該因為奧運會擁有以下這些而愛上它:它擁有運動本身最極致的魅力。它教會人們尊重自己也欣賞對手。它提供了每個民族借助體育語言與世界溝通的平臺。當我們因為后者而擁抱奧林匹克的時候,會感受到更多的體育帶給人類最純粹的快樂,分享到更多人生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