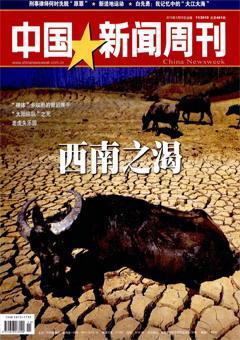她不是女性導演的勝利
朱靖江


如果靠混淆性別界限、攻占男性導演作業面作為女性導演贏得獎勵的前提,對于更多以女性氣質取勝的女導演而言,似乎并無可資參照的價值。
如果以一個宏觀的角度回望2010年的美國奧斯卡頒獎典禮,人們或許會記住兩樁歷史性事件:《阿凡達》的高調入圍與《拆彈部隊》的光鮮獲獎。前者是因為詹姆斯·卡梅隆繼《泰坦尼克號》之后,再度以全球電影票房奇跡締造者的身姿亮相于好萊塢的頒獎典禮。后者之所以同享殊榮,正是因為《阿凡達》的登頂之夢斷送在這群灰頭土臉的拆彈專家手中。
這部低成本、低票房卻在影評人的推介下咸魚翻身乃至風生水起的獨立電影,如同用彈弓擊敗巨人歌利亞的牧羊小子大衛,贏得了長期對“大神”卡梅隆腹誹有加的好萊塢“議員”們的一致青睞。
《拆彈部隊》的導演凱瑟琳·畢格羅是最新出爐的夢幻偶像。這位身材高挑、面容堅毅的女士,是美國電影藝術學院自頒發奧斯卡獎以來,首位奪得最佳導演獎殊榮的女導演,82年的一棵獨苗,難怪贏得觀禮現場的滿堂喝彩。更富于戲劇性的,是被凱瑟琳擊敗的對手詹姆斯·卡梅隆,曾經是他的藝術引路人與前夫,究竟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還是如臺灣文人李敖所言:“前妻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動物?”究竟是眾望所歸,還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對于凱瑟琳·畢格羅的此次獲獎,不少人都有發言的欲望。
凱瑟琳導演,一個好萊塢電影的異數
“凱瑟琳·畢格羅贏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象征性地終結了一個男性統治電影藝術的時代,”美國影評人萊妮·弗蘭克評價說,“但這部獲獎的《拆彈部隊》卻依然是一部男性價值觀的電影,這意味著一個女導演如果想在好萊塢獲得承認,她必須比男人表現得更像個男人,不同之處僅在于她可以穿著裙子出現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
從某種意義上說,凱瑟琳·畢格羅的確是一名執著于硬漢情結的女性導演,從出道時的處女作《無情》,到為她贏得聲譽的《K-19:寡婦制造者》,以及這部揚威奧斯卡的新作《拆彈部隊》,都是“兵哥純爺們,鐵血真漢子”的人物和情節,兒女情長一筆帶過,金戈鐵馬才是激情所在,令人忍不住思忖這位女導演莫非北歐神話中“瓦爾基里”女戰神轉世,不愛紅妝愛武裝。她女性化的縝密思維,往往表現在對機位的安排和對鏡頭的細致規劃上,如在《拆彈部隊》中用多機位表現爆炸場景,以及士兵們在險惡環境中的表情和行為細節,這也為其作品的藝術成色增分不少。
凱瑟琳·畢格羅從不諱言她對男性權力的渴望擁有。“在電影的行當里,男人能做的事情我都能辦到。”她曾在答記者問中做過如是豪言。的確,在《拆彈部隊》的劇組訪談中,所有身形粗獷的男演員在談到導演的時候,無不由衷地感到敬畏。他們與這位強悍的女導演之間,存在一種超乎性別的情誼。“毫無疑問,在劇組中凱瑟琳擁有絕對的權威。她是我們這群男人的核心。”在好萊塢這個格外注重性別特征的浮華世界,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異數。
而對于更多的女性電影人而言,凱瑟琳·畢格羅作為她們的代表,領取了奧斯卡史上第一尊最佳導演獎,是一樁喜憂參半的事情。一方面,好萊塢主流電影勢力終于在多年的無視和拖延之后,承認了女性在電影導演領域的能力和貢獻。這無疑是劃時代的進步。即便是在男性雄踞主宰地位的美國政壇,賴斯和希拉里·克林頓等杰出女政客早已證明女性在外交、安全等國事部門完全可以和男性政治家媲美,更遑論歸屬于藝術領域的電影創作活動。因此,當一名有著20多年導演經歷的女性站在舞臺的聚光燈下,手握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兩尊奧斯卡大獎,終歸讓電影導演界的“第二性”感到揚眉吐氣。
但另一方面,凱瑟琳·畢格羅過于男性化的創作方向雖然有其價值,卻并非女性導演樂于遵循的常規套路。不少人因此而質疑,這份顯赫而突兀的榮譽是否意味著另一重隱性的性別歧視:即女導演們更擅長的情感、家庭、喜劇和女性題材電影,依然沒有得到奧斯卡評委們足夠的重視。如果靠混淆性別界限、攻占男性導演作業面作為女性導演贏得獎勵的前提,對于更多以女性氣質取勝的女導演而言,似乎并無可資參照的價值,畢竟拍攝《K-19;寡婦制造者》一類的電影不是大多數導演系女生的藝術志向。
女性導演何時獲真正的藝術肯定
盡管人數有限,活躍在國際影壇的女導演卻并非鳳毛麟角,她們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藝術成就和票房佳績。當我們提及簡·坎皮恩、索菲婭·科波拉等著名女導演,首先會想到她們氣質迷人的女性視角以及溫婉清新的視聽語言。無論是前者執導的《鋼琴課》,抑或是后者操刀的《迷失東京》,都是當代世界影壇的精品,但均與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失之交臂。
在身為獨立電影工作者的姿態上,坎皮恩和科波拉甚至比凱瑟琳·畢格羅更為純正,她們對電影藝術的探索之功也更早被國際電影界肯定。
因此,我們不應以一尊奧斯卡獎的歸屬來判定某位電影導演的藝術成就,更不能因此忽視大多數女性電影人為這門藝術奉獻的激情、淚水、欲望、風情乃至八卦、時尚、神經質的敘事方式。
即便將凱瑟琳·畢格羅的女性導演身份忽略不計,獲得奧斯卡全面肯定的《拆彈部隊》能否被視為伊拉克戰爭題材電影的代表作,依然值得商榷。按照褒譽者的評價,“這部影片具有紀錄片一般動感粗糲的影像風格,同時彰顯了悲劇境遇中的人性之光。”然而僅此美育并不足以構成一部經典電影的核心價值。當我們回想起《野戰排》《獵鹿人》和《現代啟示錄》等一批名垂影史的越戰電影杰作,我們能夠聽到電影導演們透過一幅幅畫面、一組組鏡頭發出的內心怒吼。這些作品書寫了一個時代的靈魂之痛,反思那場戰爭帶給兩個國家的鮮血創傷。無論經過多少年的歲月消磨,它們依然稱得上美國電影的代表作。
令人遺憾的是,《拆彈部隊》卻并不具有如此深刻的悲劇精神,它試圖構建+日常環境下的戰爭場景,讓一群拆彈狂人如同打電玩一般拆除那些反美武裝設置的地雷和炸彈,卻放棄了對這場戰爭本身價值的直接判斷。凱瑟琳·畢格羅成功地完成了這場真人出演的戰斗游戲,從藝術和技術的層面比很多男性導演更為出色,但是她依然沒有達到她所敬仰的那些電影大師們的高度——賦予一部作品在歷史潮汐中的文明坐標,成為一個時代的代言者。
在這一點上,被奧斯卡貶黜的詹姆斯·卡梅隆甚至尤勝一籌,他將一種終極關懷構建在人類與潘多拉星球之間的關系上,以杰克歸化于納威人,象征著人類對工業文明的反思。以至于有人預言《拆彈部隊》將是一顆在電影史上一掠而過的流星,真正守望在21世紀初電影銀河中的恒星,依然是《阿凡達》這部掀起萬眾狂瀾的神諭之作。
“我不能改變我的性別,我也不能停下來不拍電影。”這是本屆奧斯卡雙冠女王凱瑟琳·畢格羅最鼓舞人心的勵志箴言。無論是繼續堅守“鐵血路線”的她,還是那些拍出了《媽媽咪呀》《欲望都市》《暮光之城》《朱莉與茱莉婭》等優秀作品、內心世界更為柔美親和的多數女導演們,都將繼續在電影的坎坷道路上奮力前行。
在2010年,我們見證了一個奧斯卡奇跡的誕生,希望在未來的日子里,能見證女性電影人破繭而出,真正擁有一片屬于她們的藝術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