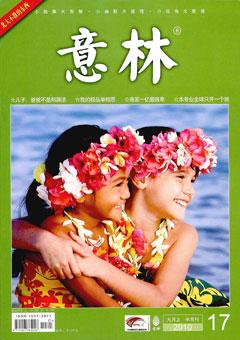法語課
苗 煒
10年前,我在北京二十七中學的教室里學了3個月的法語,現在還能用流利的法語自我介紹,“我叫什么”“我是干什么的”,還會說,“這是什么”“那是什么”,還有“你好”“再見”“謝謝”“干杯,好胃口”。
每周一三五,我下班之后坐公共汽車到東華門,在一家馬蘭拉面館吃一碗面條,然后就去夜校上課。第一節課,老師就說,你們的目標就是把這半年的課程給堅持下來,到最后一課的時候還能坐在教室里,你就相當了不起了。這位老師大概對半途而廢的學生見得太多了,所以再碰見我這一個也不算什么。他在第一節課還問,“你們為什么要學法語呢?”班里有一個女生說,她在SOS國際救援機構工作,經常要和法國人打交道。還有一個時髦的女孩子,是學美術的,她說想去法國留學。我的回答是,法國有個著名作家叫普魯斯特,寫了本小說,不對,寫了7大本小說,叫《追憶似水年華》,我想讀原作,所以來學法語。全班人哄堂大笑,老師先是張大了嘴巴,然后說“太必羊太必羊”,就是“好啊好”的意思,他說:“這可非常非常難。”他手指另一間教室,“那里是高級班,即便是那個班的學生也沒幾個能看長篇小說的呢。”
后來我意識到自己不可能在幾年之內就學會法語讀懂普魯斯特,我就說,先把這事放一放吧。我不是給自己一個過高的目標而后立刻給不去實現這個目標找借口,我是說,那些激發我做一件事的最初的沖動都偉大得要死,我才能有限,而不是那個目標有什么錯,如果你非說這是好高騖遠,那么我也沒什么可辯解的,考慮到我干什么事情都才能有限,我應該更實際一點兒。
10年前要去法國學美術的女孩兒,當時在中戲的舞美專業,她沒畢業就真去了法國,最近我收到她寄來的《藝術法語教材》,她已經開始編教材了。10年前在SOS國際機構工作的女生,后來也去了法國,后來又去了非洲,到處給窮困的非洲黑人看病,我們還通過電子郵件保持聯系。前不久,她發來郵件說,她正在加蓬從事醫療工作,隨身攜帶著7大本《追憶似水年華》,現在正在讀第三本,在這句話后面,她隨手敲下了一個微笑的表情,但在我看來,這個符號旋轉了90度,真的變成了一張人臉,一只眼睜著一只眼閉著,嘴角帶笑。我看著這個符號,心想,我好端端的一個夢想怎么就讓她給偷去了呢,就好像我埋下了一筆寶藏,她在旁邊看著,到最后她把這筆寶藏挖走了,只給我留下一個空空的洞穴。
(田生摘自《新民周刊》2010年第28期圖/廖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