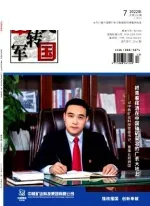西昌:14年青春做伴
■ 文 李鳴生
編者按:2010年10月1日晚,“嫦娥”2號從西昌發射場翩然升空。西昌再次吸引了世人關注的目光。對于軍旅作家李鳴生來說,西昌給他帶來的不僅僅是興奮,還有著許許多多珍藏在記憶深處的別樣滋味——

1970年9月,首批4623名發射官兵抵達“趕羊溝”
36年前,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剛剛脫下學生服、穿上新軍裝的我被一輛軍用悶罐車秘密拉到了西昌。由于當時保密制度極嚴,車門打開時,我并不知道我的落腳點叫西昌,更沒想到我人生的第一步竟會踏入西昌發射場!西昌隸屬于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隨著全中國解放的步伐,涼山從奴隸社會一步跨進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射“嫦娥”2號的發射場40年前偏偏就建在了西昌,建在了距西昌市約50公里的一個原始般的大山溝里。
大山溝是解放前彝族人放羊的地方,故當地百姓叫它“趕羊溝”。“趕羊溝”寬約500米,長約10公里,山高谷深,峰巒疊嶂,四周除了大山,就是大山,除了石頭,還是石頭,從溝里到溝外,一片空寂,滿目荒涼。發射場之所以建在這里,一是緯度位置低,離赤道近,火箭發射時省力;二是地形隱蔽,有利于戰備,符合“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最高指示;三是峽谷開闊,便于多個發射陣地和測量觀察點的布局,有利于將來發射場的發展;四是氣候優越,年均氣溫17攝氏度,全年日照320天,“發射窗口”較大;五是離成昆鐵路線和大型軍用機場不遠,交通條件相對較好;六是周期短,投資少。1970年9月,首批4623名發射官兵從戈壁灘秘密來到大山溝,猶如一支天兵突然從天而降。當地百姓背地里稱他們為“天軍”。“天軍”降臨大山溝時,正趕上季風時節。狂風挾裹著沙子,“呼呼”地撲打在戰士們的臉上,痛得戰士們個個齜牙咧嘴。戰士晚上站崗甚至能聽見野狼嗥叫……由于當地的彝族同胞只見過紅軍,看見我們,男女老少都遠遠地躲在自家門前或者半山坡上,不肯接近半步;對那些成天在山溝里顛來跑去的大卡車、小汽車,更是視如怪物……
部隊生存方面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水土不服。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拉肚子——吃什么都拉,連喝水也拉,而且一旦拉肚子后,吃什么藥都不管用,但只要一離開西昌,就不拉了。官兵們把這種病稱為“西昌病”。“西昌病”大量泛濫,再加上食品供應困難、住宿條件極差(大雪天里還睡在臨時搭起的帳篷或草棚里),致使官兵們的體質普遍下降。一首當年在戰士中流傳的打油詩——“天是羅帳地是床,大涼山下扎營房。三塊石頭架口鍋,野菜鹽巴下干糧。”也許最說明問題。
我進山溝的第一個任務是打山洞,這個山洞就是今天發射“嫦娥”2號的地下指揮所
部隊工作方面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有河無橋。初創時期的發射場無路、無電、無水、無場地,甚至沒有一座通往外界的橋。山溝與外界隔著一條浪滔滾滾的河,叫安寧河。安寧河寬150余米,為雅礱江的一條支流。1935年紅軍路經此地時,靠竹筏子冒險渡過此河。可安寧河流走了無數個春夏秋冬,始終沒有一座溝通山里山外的橋,年年歲歲人來人往,只能靠一艘小木船來回擺渡;創建發射場的航天大軍和物質器材更是無法進山。航天大軍和物質器材不能進山,發射場便無法開工。于是搶建安寧河大橋,便成為部隊打響西昌的第一仗。聽老兵說,大橋開工這天,大雪紛飛,寒風呼嘯,戰鼓“咚咚”,紅旗飄飄,3000多名工兵戰士昂首挺胸列隊成行,雄赳赳氣昂昂地站在安寧河南岸的沙灘上。他們先是面對毛主席畫像集體宣誓,接著一起高聲背誦毛主席語錄,然后抓起軍用水壺灌下幾口烈酒,再紛紛脫下棉衣棉褲,光著膀子扛起草袋,爭先恐后跳進冰冷刺骨的安寧河……
我新兵下連時,安寧河大橋早已建成,被官兵們取名為“長征橋”。可惜1971年林彪事件震驚世界,接著全軍“批林批孔”運動如火如荼,于是曾經轟轟烈烈的西昌發射場像一艘在風雨飄搖中的小船,沒有了動力,迷失了方向。我進山溝的第一個任務是打山洞,這個山洞就是今天發射“嫦娥”2號的地下指揮所。但在當時,官兵們晝夜打洞不止,卻不知為何打洞。打山洞24小時三班倒,不分白天夜晚,苦累不說,危險還挺大。比如遇上塌方,一個班、一個排,甚至一個連都有可能被埋在洞里。我是新兵蛋子,加上保密,對打山洞的意義一無所知;偶爾聽老班長說起將來要發射衛星什么的,也只當是天方夜譚白日做夢。
最讓我感到絕望的是山溝與世隔絕,信息不通。為了排解精神上的苦悶,我曾步行近10公里到一個小鎮買回一個收音機。可收音機在山溝里只能收聽一個臺,而且這一個臺不是斷斷續續就是“刺刺啦啦”,少有能聽清一句完整話的時候。記得到部隊后的第一個春節,我搭乘一輛買菜的大卡車專程趕到七八十公里外的西昌給在老家的母親打電話。可我等了幾個小時,掛了五六次電話,這個僅有500公里路程的長途電話最終也沒打通。最后我只好垂頭喪氣地回到大山溝里,跑到山上望著天空久久發呆。此后,我便有了獨自一人坐在山坡上抬頭望天的習慣:望日落日出,望月明月暗;望風起風止,望云聚云散;望雨粗雨細,望霧濃霧淡……天空成了我精神的棲身地,成了我思想的大容器,同時也成了我渴望與世界溝通的唯一窗口。
1984年4月8日晚,中國第一顆同步通信衛星從西昌飛向了3.6萬公里高的赤道上空
10年后,我終于等來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夜晚。那是1984年4月8日晚,中國第一顆同步通信衛星從西昌發射場成功地飛向了3.6萬公里高的赤道上空。此前由于沒有中國自己的通信衛星,中國人看電視只有靠花費巨款租用外國衛星來轉播。比如當年看女排比賽,租用的就是外國衛星,常常看到一半或者高潮時,電視屏幕上突然一片漆黑,隨即現出一行字幕——“衛星租用時間已到”。這顆衛星讓我們結束了長期租用外國衛星的歷史。中國人終于能收看到由自己的衛星轉播的電視了。這個夜晚我早早便守候在離發射架200米遠的一個山坡上。當我親眼看到“長征”3號火箭在熊熊的烈火中隆隆升起時,我簡直驚呆了。這一刻,我忽然意識到,原來人是不會永遠匍匐在地的;原來人是可以換個角度從天上俯瞰人間的。于是,從此我改變了跪著仰望世界的角度,也改變了跪著看待人生的姿勢。

后來,我走出了山溝,來到北京,成了一名作家。然而多年來我無法忘記西昌、忘記西昌的大山溝、忘記大山溝里的發射場,更無法忘記那些在大山溝里默默生活了40年、至今依然默默生活在大山溝里的兄弟姐妹。每當想起他們,尤其想起他們那些天真可愛的孩子(由于長期困在山溝,在超過20年時間里,這些孩子竟然沒有一個考上正規的大學),我的心里便會隱隱作痛。于是20年來我把書寫航天當作我情感的寄托,把西昌當作我精神的故鄉。我的心常常在“故鄉”的發射場漫步。“故鄉”的每個信息都會撩動我的情思,“故鄉”的每次發射都會牽動我的心弦。從1970年到2010年,短短40年間,西昌發射場從一個零到3.6萬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從3.6萬公里高的赤道上空再到38萬公里遠的月球。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空間的高度,更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民族的高度。
這個高度便誕生在西昌,誕生在我拋灑了14年青春熱血的原始的大山溝里。在“嫦娥”2號成功飛天之際,我寫下此文,就是想祝福西昌、祝福我西昌發射場的戰友們在未來登月的漫長日子里,平平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