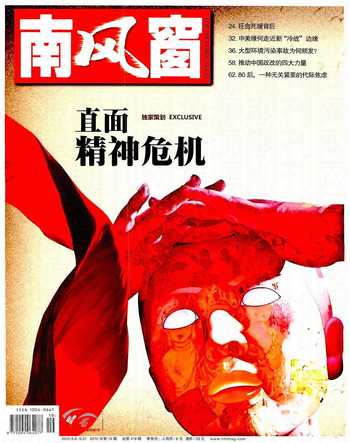行政問責管不住違法用地
田 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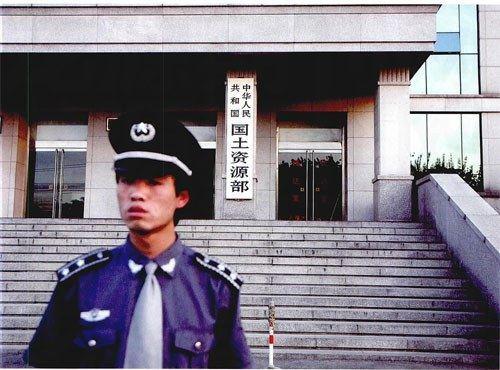
國土問責,大限將至。國土資源部將9月設定為2010年6月以來掀起的國土執法行動的最后期限。2008年6月,國務院的《違反土地管理規定行為處分辦法》(15號令)自公布以來,第一次面臨著真刀真槍的落實。
當年,15號令剛出臺時,“既處理事又處理人”的要求,曾讓對轄區內土地違法承擔責任的各級政府一把手心驚,但兩年多來,不曾有一位一把手真正被處理過。
過去的一個月內,國土資源部部長、司長等多名官員在不同場合放出狠話,要嚴格落實15號令,處理對土地違法負有責任的地方官員,向公眾傳達著,這一次國土大執法行動,要動真格的信息。
但是,在原國家土地管理局土地規劃司副司長鄭振源看來,這樣的狠話對于亂象叢生的中國土地利用現狀來說,根本就是無濟于事。
“從1986年中國有了《土地管理法》以來,違法用地的現象是逐年劇增,到今天,至少已經有過七八次聲勢浩大的違法大檢查了,可是,每次檢查最終都不了了之,風頭一過,違法重來,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
在鄭振源看來,土地違法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是土地法律和制度本身出了問題,不對行政權力高度壟斷的土地資源配置方式進行徹底改革,多么嚴厲的問責都管不好中國土地。
政府之責
在國土管理上,國土部2000年就實現了“衛片執法”,利用衛星遙感等技術手段制作的監測信息及有關要素合成的影像圖片對全國各地的土地利用情況進行監控,至今已經進行了9次大檢查。
這項現代技術的運用,也讓地方政府瞞報土地利用現狀的行為,基本沒有了操作空間。可以說,過去的10年里,對整個國家的土地違法利用情況,中央政府一直都應該是一清二楚,每年也都會照例公布當年查處的土地違法數量、面積等等籠統信息,但在問責方面,幾乎每年都是雷聲大、雨點小,也極少公布詳細的違法地區、責任人、地塊等等信息。
事實上,如果不是在中央領導人調控房地產的強烈決心壓迫下,今年的土地執法大檢查,同樣會同往年的操作模式一樣,不會如此高調,不僅明確公布“7月督察、8月約談、9月問責”的時間表,更是公布了超過3000塊,近20萬畝房地產違法違規用地信息。
這一輪的問責風暴雖然還沒有落到實處,但這些較之往年詳細得多的違法信息披露至少讓公眾看到,整個國家的土地違法現象可謂觸目驚心。不過,在鄭振源看來,這些信息公布起來容易,真的問責卻很難。
“在土地執法上,各級政府早就習慣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鄭振源說,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很多違法違規現象的出現是政府自己的法律和政策造成的,而不是用地者的問題。
事實上,從國土部公布的數據看,第一批各地上報的2815宗閑置土地中,因土地出讓拆遷難、調整規劃等政府和客觀原因造成閑置的超過60%。
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快速發展的超級都市歷來都是違法用地的重災區,這一輪問責風暴中也不例外。以廣州為例,一共有54塊閑置土地屬違法違規之列。
8月底,廣州市國土房管局新聞發言人在接受記者采訪,談及閑置土地的產生原因時,給出了四大因素:一是因企業資金實力不足、合作單位之間存在糾紛等自身原因無法動工;二是存在司法查封,企業暫無法對地塊實施開發;三是存在規劃調整、控制未穩定、市政道路建設占用等政府因素影響;四是存在拆遷補償未完畢等遺留問題。
該新聞發言人特地強調,絕大部分土地閑置不是單一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種原因交錯影響的結果。就廣州而言,拆遷難度幾乎是各個地塊都遇到的難題,拆遷進度的延誤,進而影響被拆遷戶回遷安置,并產生巨額滯遷費甚至司法訴訟等問題。
事實上,土地違法中的政府因素并不僅僅集中于地產用地中。鄭振源說,國土部以往的每一輪執法大檢查,重點都有所不同,2004年重點查的是“以租代征”,但這種違法形式的出現根本原因是法律規定集體土地不許自由流轉,查了很多案例,最終也沒處理幾個;今年重點查的除了閑置土地,就是“未批先用”,這主要是因為去年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開始以后,地方政府有了錢,就要上項目、搞工程,都需要用地,而土地的審批程序遠遠趕不上用地速度,不違法是不可能的。
制度之弊
從土地規劃司副司長任上到退休以來,鄭振源一直都在呼吁,管理者自身不斷的違法用地是中國土地管理的頑疾,而這也正是制度和法律本身的問題所造成的。
事實上,自從改革開放,中國進入了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以來,在有限的土地資源限制下,建設與農業爭地的矛盾就是中國土地管理最核心的問題。對于糧食安全的擔憂、傳統農業國家的執政習慣都讓保護耕地成為執政黨這60多年來在土地問題上的最重要訴求之一,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在土地管理領域,中國目前的最高法律是1996年修訂后的《土地管理法》,這部法律將國家土地利用管理的目標設定為嚴格控制建設用地,保護耕地,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后來在具體的操作中,這一目標更加明晰化為保護18億畝耕地紅線。
為此,國土部先后編制了多部以分配指令性控制指標為特征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由中央確定耕地保有量、基本農田保護率、建設占用耕地量、開發整理補充耕地量等指令性控制指標,層層分解下達到鄉鎮,各級政府都按指標制定規劃。
為了保障土地規劃的落實,土地管理部門設計了一套復雜的,高度集權的行政審批制度,在中國眾多的行政審批事務中,土地審批稱得上是最復雜的一項。
但在社會經濟的現實發展面前,這些詳盡的土地規劃總是很快就淪落為一紙空文。以1997-2010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為例,制訂該規劃時,耕地總量動態平衡和居民點工礦用地零增長。但是,規劃實施不到兩年,耕地保有量和建設用地總量就全面突破。
“規劃、計劃的指標不切實際,而且依據的信息失準,計劃趕不上變化,這是造成違法、違規用地的根本原因。”鄭振源說。
復雜的土地審批制度無從保障這些不切實際的土地利用總體目標的實現,其高度集權的特征又讓它往往淪為土地審批權力尋租的工具。今年,剛剛被媒體披露的遼寧撫順國土資源局順城分局原局長羅亞平貪腐案就是最好的案例。一個科級官員貪賄1.45億,被公眾冠名為“土地奶奶”,被中紀委定性為“級別最低、數額最大、手段最惡劣”。
《土地管理法》禁止集體土地自主進入建設用地市場,規定只能由國家壟斷提供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流轉指標和供給,同時在使用權流轉方式上限制只有劃撥和征用兩種。
事實上,“劃撥”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豪華辦公樓、政府大廈的出現正是因為政府用地劃撥,就相當于免費使用。征用雖
是“有償”也意味著并非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比如招拍掛房地產用地,實行半饑餓狀態的限量供應和壟斷價格,必然抬高地價從而導致房地產的供不應求和房價高漲。
在工業用地上,政府官員為了招商引資,將地價壓得很低,甚至是零地價,國土資源部關于工業用地定價的種種規定在很多時候都是形同虛設。地方政府熱衷賣地,用房地產招拍掛的溢價填補工業用地的虧損,最近20多年來,這都是中國各地政府最慣常的生存方式。
在土地問題上,地方政府的利益與中央政府制訂法律的訴求是完全沖突的。而行政審批制度的設計則高度集權又缺乏監督,諸如土地利用規劃方案、核定基準地價、土地出讓年度計劃、土地出讓收益管理和土地用途管理等事項的決策權全都集中于國土部門,土地違法也就變得輕而易舉。問責還是改革?
2009年,已經無法有效規制國土違法現象的《土地管理法》也進入了重新修訂的議程。但是,對于國土部提出的修訂草案,諸多相關學者批評聲居多,國土部的草案被認為強化本部門權力的初衷遠大于國土管理效益的考量。
“去年6月份就提交國務院了,可是被擱置以后,就沒音訊了。”鄭振源說,那份草案沒涉及根本問題,意義不大。在他看來,法律和制度的修訂應該是場對現行土地管理制度根本意義上的改革,其中最根本的是改革土地資源的配置方式。
事實上,改革開放至今,在財政分灶吃飯的體制下,地方政府不僅是行政主體,而且還是獨立的經濟主體。作為經濟主體,其行為目標就是要追求財政收入最大化,在現行分稅制的條件下,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極不相稱,地方政府領導都要想方設法上項目,發展經濟,擴充財政收入的訴求大于保護土地的訴求也合情合理。
鄭振源也認為,地方政府這種發展經濟、擴充財政收入的積極性是國民經濟得以快速發展的動力之一,也是改革開放中制度創新的重要源泉,無可厚非,更不能簡單否定。
正是因為現有土地管理制度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趨勢和需求,各地才出現想方設法沖破制度的情況,由此產生的層出不窮的違法用地亂象,根本不是行政問責這樣的手段所能根治的。
中國的教育制度、醫療制度雖然改革的進程也一直步履蹣跚,但至少都已經啟動,并逐步走上正確的道路。但是,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顯然還沒有提上日程。
多年以來,不論是在位期間,還是退休以后,鄭振源一直都通過各種途徑呼吁對中國土地管理制度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他看起來是個市場經濟的信徒,試圖將市場經濟那一套理念引入到土地管理中,并且堅信運用市場機制來配置土地資源一定能比計劃手段更加有效率。不過,他的主張事實上一直都沒有被真正重視過,不論在政府機關還是學界,土地管理這樣計劃性十足的公共事務被認為更需要周密的計劃,遠不是市場機制所能解決的。
但無論如何,當我們在一項政府事務中,每年面對數十萬件違法案子,且屢治屢敗,管理失效時,行政問責的把戲顯然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對制度性弊病的檢視和修正是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