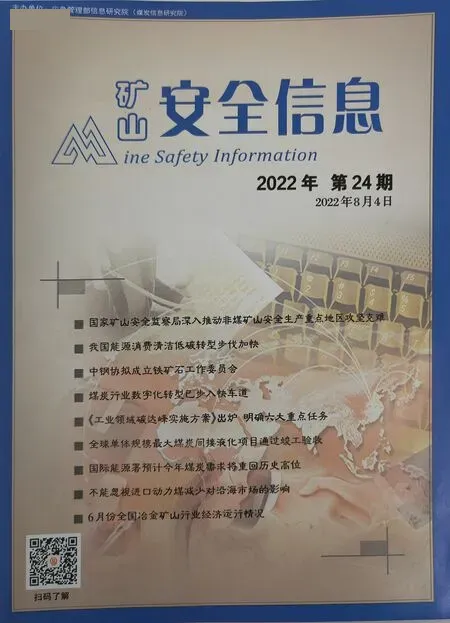內蒙古局:召開2022年上半年監察執法工作會議
近日,國家礦山安全監察局內蒙古局召開2022年上半年監察執法工作會議。會議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安全生產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國、全區安全生產電視電話會議精神以及上級各項決策部署,總結交流上半年監察執法工作中的好經驗、好做法,謀劃下半年監察重點工作。內蒙古局黨組書記、局長馮廣存出席會議并講話。
會議指出,上半年內蒙古局組織對煤礦開展了7 個專項監察和13 家不放心企業“開小灶”檢查指導工作;推進了對非煤礦山4個專項檢查;強化了重大災害治理和信息化智能化建設使用;保障了全區礦山安全生產的良好形勢。
會議強調,目前,監察執法工作要認清“四大風險”。增產保供超強度開采帶來的風險。部分煤礦生產能力和開采強度已近極限,采掘失調、采剝失調的問題逐步嚴重,事故概率和風險也會大幅上升。企業主體責任不落實帶來的風險。在日常監察和事故調查中,發現還有不少企業存在安全管理松懈,上級公司日常監管和業務保安作用發揮不到位等問題;煤礦現場管理糾治不力,違章作業、違章指揮導致多起事故發生;當前全區仍有不少企業對外委隊伍以包代管,部分外委施工隊伍存在安全投入不足、員工教育培訓不嚴、現場管理混亂等問題。安全風險防控措施不落實帶來的風險。部分企業安全技術管理不規范,既存在管理制度、規程措施與現場實際“兩張皮”,不具備操作性的問題,又存在制度措施執行不嚴、落實不到位的問題。非煤礦山和尾礦庫礦點多、散亂小問題突出,開采工藝落后,管理水平低下和技術裝備落后帶來的風險。
會議要求,下半年,黨的二十大即將召開,必須抓好“四個不放松”。抓上級決策部署落實不放松,以實際行動踐行“兩個維護”。要拿出更大的決心和勇氣,過硬的舉措和辦法,迎難而上,做好三年行動收官、安全生產大檢查、煤炭安全保供等各項工作,用礦山安全生產的實際成效踐行“兩個維護”。抓監察執法不放松,堅決防范遏制礦山生產安全事故。要持續保持打非治違的高壓態勢,嚴肅事故和舉報案件查處,深化開展非煤礦山安全監察,加強執法標準化和規范化建設。抓責任落實不放松,推動安全生產長效長治。要充分發揮上半年“開小灶”取得的工作成效,推動企業增強抓安全生產的內生動力,嚴肅整治“違章指揮、違章作業”行為,推動重大災害治理。執法重點由單純針對煤礦轉為煤礦和上級公司并重,切實推動企業主體責任和全員安全生產責任制的有效落實。抓基礎提升不放松,筑牢礦山安全生產防線。要加強信息化系統的建設使用,繼續強力推動煤礦智能化建設,各事業單位做好監察服務支撐保障工作。
會議期間,與會人員還以講故事、講案例,談經驗、談心得、談問題、談思路的方式進行了座談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