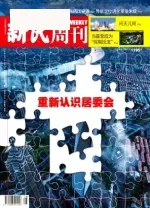被低估的城市
汪偉



重慶是一座被低估的城市。至少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如此。
說實話,山水和吃食不足以讓人一直勾留在重慶。這里霧氣太多,地勢太陡峭,吃的東西雖然美味,可是未免太單調了一些。大足石刻值得一看,但較北方佛教造像藝術相比,也拘謹粗糙了一些。但想到這里是三峽起點,一切都得到了補足。
在傳教士拍攝的照片中,20世紀初的重慶城,是嘉陵江南岸一塊楔入長江的不規則三角形,尖銳的頂點是朝天門,左右兩翼臨江的峭壁上布滿了城墻和吊腳樓,迤邐地向西延伸而去。
重慶是沿著長江入川的門戶,也是從中原翻越秦嶺入川的鎖鑰之地,與黔北和湘西的大山相連。政治上的重要性取決于重慶之于成都平原和云南高原的軍事價值。此為“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地,軍事價值又完全是由于其獨特的地理決定的。
重慶被高山環抱,尤其是北方的秦嶺阻隔,使得長江水道長時期是出入重慶的第一選擇。水汽上升,被山勢所阻,當地所以常年陰云低垂,濃霧彌漫。黯淡、潮濕的環境里,船工為了驅寒祛濕,在江邊生火取暖,用吊爐把葷素食材一鍋燴,添加海椒和花椒,由是發明了味重麻辣的火鍋。
說到重慶,中國人的第一反應幾乎都是這兩個字:火鍋。
還有呢?
這……
如果只是發明了火鍋,當年的重慶又怎么當得起“中華民國永久之陪都”?
對了,還有三峽。這里是三峽的起點。
還有呢?
嗯……三線!說明你有點兒年紀。
還有呢?
陪都。說明你不僅有點兒年紀,還相當淵博。
這就是全部了。20世紀對重慶的改變,也許要超過此前的1000年。1940年代的陪都歲月、50年代的三線建設和90年代的三峽工程,徹底改變了重慶。
但重慶是一座被低估的城市。至少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如此。
無抗戰,則無重慶性格
王康住在沙坪壩熱鬧的商業街上,門口有重慶陪都文化有限公司的牌子,他的椅子背上卻寫著“正在寫字,勿擾”的字樣。鄰居的門上大多也掛了各種各樣的公司牌子,不知里面的景象如何,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的門牌背后其實是個巨大的書房。
身在商界,但王康的真實形象是一個學者,遞來的名片上印著抗戰勝利紀功碑的圖案。
抗戰勝利后,重慶人在市中心豎起一座仿燈塔的紀念碑,紀念民族戰爭的偉大勝利。這是其他城市所沒有的殊榮。
王康是重慶現代史的發掘者,但其發掘絕不局限于重慶。他發掘重慶的歷史,是為了從中探求中國的命運。他眼中的重慶毫無疑問是現代中國歷史的關鍵之一,正如他所說:
1940年5月9日,素以酷愛獨立、自由稱譽世界的歐洲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法蘭西共和國,在納粹德國戰爭機器僅僅六個星期的進攻后便可恥地投降,任由首都巴黎可恥地陷落35天前,重慶臨時參議會通過議案,呈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及國防最高會議:重慶為戰時首都,成為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之樞紐者,三載于茲;且今后抗戰勝利,亦必預計其為西南建設之中心,并得在歷史上成為千秋萬世永值紀念之名城。因而建議政府明令,定重慶為中華民國永遠之陪都。
經受了三年狂轟濫炸和南京汪偽叛逆政權強大沖擊的重慶,已成為戰斗中國名副其實、堅不可摧的戰時首都。
這是重慶歷史上的光榮一頁。但這光榮是血淚斑斑的。
根據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軍部曾制定“大陸令第241號”、“大陸令第345號”、“大陸令第925號”、“大陸令第1252號”作戰令,將重慶確定為“敵國戰略及政略中樞”,確定為“航空戰略轟炸”,為期五年半,史稱“重慶大轟炸”。
最嚴重的兩次轟炸,一次發生在1939年5月3、4兩天,63架日機首次轟炸重慶,炸死3991人,炸傷2287人,炸毀房屋4871間。第二次時為1941年6月5日,日機持續轟炸重慶達300分鐘,釀成死傷逾3000人的“大隧道窒息慘案”。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22天,在曾數度一片火海、斷壁殘垣的民族路、民權路和鄒容路三條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聲中外的木質紀念建筑物,公議定名為“精神堡壘”。“精神堡壘”通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戰之意,頂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內貯燃油、棉條,每遇重大集會,即倒入酒精點燃,焰火熊熊,象征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浩然正氣。
在王康看來,重慶的遭遇有其世界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各國首都中,重慶成為最早、最久、最多的遠程戰略轟炸目標,成為取消了前線與后方、交戰人員與普通民眾之間界限的“無區別轟炸”的濫觴,成為戰爭手段和戰爭哲學惡性轉變,遠程運載工具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相結合,將整座城市作為人質和對象的毀滅恐怖轟炸的開端,這個開端,清晰地通過德軍轟炸倫敦、英軍轟炸柏林、美軍轟炸東京、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以及戰后各次戰爭中同類手段和同類性質的遠程戰略轟炸,及至2001年9月11日國際恐怖組織對美國紐約世貿大廈的劫機轟炸等“空中屠殺”,它們都與“重慶大轟炸”有戰史邏輯繼承關系。
他寫過七集電視紀錄片《重慶大轟炸》。重慶在血與火中升華了城市的性格:“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中,重慶成為第一個在決定人類命運的世界性決戰中始終站在正義、民主、自由、光明與和平一方,并享有崇高國際聲譽的偉大城市。”不管是輝煌的古都如西安、洛陽、開封,還是現代政治經濟中心如北京、南京、上海和廣州,即便它們有和重慶一樣的不幸遭遇,卻也無緣和重慶共享這一份光榮。
聽王康談重慶的歷史,會產生過一種錯覺,眼前這個髭須森然、目光銳利的男子,和巴文化中的巫師差不多。
巴人沿著長江進入重慶,把神秘感性的巴文化也帶到這里。巴人信仰的中心是巫師。他們戴著風格夸張、造型奇特的面具,穿著紅黑兩色的大袖寬袍,手執法器,在咚咚的鼓聲中翩翩起舞。據說巫師可以和死去的祖先的靈魂溝通。他們帶有催眠功能的歌聲讓活著的人慢慢進入迷醉的狀態,由此喚醒了對部族歷史的記憶,獲得勇氣。
王康的父親是安徽人,40年代考入西南聯大,去昆明上學途中,不知為何流落成都,入四川大學,在那里認識了他母親。他的母親姓唐,舅舅唐君毅是著名學者。王康生于風云變色的1949年,一生坎坷,和巴人的巫師一樣,執著地發掘被遺忘的歷史,試圖喚起人們面對事實的勇氣。
但知南京、北京,不知有重慶
四川人身材矮小,幽默、強韌、吃苦耐勞。他們口音鮮明,鄉土意識濃厚。抗戰中專門有紀念本鄉子弟參軍作戰的紀念碑“川軍出川作戰紀念碑”,為其他各省所無。川軍出川之后,未幾參加臺兒莊之役,戰斗頑強,損失慘重,一舉洗刷了川軍沒有戰斗力的污名。抗戰中,川籍軍官、士兵和壯丁中死傷者不計其數,戰前的省主席劉湘力戰身死,是中國最早戰死的高級將領之一。這一切,造就了四川和重慶在現代中國的特殊地位。歷史也給了四川和重慶特別的報償。
重慶的工業化是抗戰時期打下的基礎。學者李紫翔說,西南的工業是東部工業家的遷建,和后方投資者轉變途徑,于戰時短促的幾年中合作起來的產物。在他看來,原來的西南是沒有工業的處女地,戰時卻設立了幾千個中小型工廠。“我們回想起這塊處女地上工業建設的經過,常在缺乏一切工業的必要條件,甚至在缺乏或不能使用近代交通條件下,一切大大小小的機器、零件、原料、技師和工人,用著一切老的、新的運輸方法,從各條可能通過的道路,潮涌似的移植了進來。原來不重視工業,或無意于投資于工業的人民,一是對工業發生了濃厚的熱情和興趣,并在支持戰爭的認識下,在各方面減少了一切可能的障礙,而給予了難能的援助。在西南的這種情形,是和抗日戰爭激發了一個撼動社會精神傳統的愛國主義一樣,亦激發了一個撼動國民經濟基礎的工業遷建運動。另一方面企業家和工程師們,也發揮了空前的克服困難的精神和創造的能力。例如倉促遷移工業設備,既多陳舊,復不完全,但他們不但因陋就簡地迅速復工,并盡了一切智慧經驗,給予補給、仿造和改良,以生產必需的用品或代用品。”
在李先生看來,由此取得的物質成就尚不是最重要的,像所有的樂觀主義者一樣,他認為,“這種改良技術的精神和成就,開創了我國工業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假如我們能保有并加繼續進步的話,則它的價值,也比生產若干合用的產品,是更重大得多。”
王康說,無抗戰則無重慶人的現代性格。就地理、軍事和政治而言,四川是中國的腹地,這塊腹地物產豐饒,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僅以規模來說,幾乎是一個或者若干個歐洲國家之和,而重慶就是這塊腹地的最后門戶和精神象征。
凡是有關戰時重慶經濟的展覽,都有大量的篇幅是專門留給盧作孚的。這個樣貌典型的川人有一種不計利害的精神,幾乎是靠他旗下的民生公司一己之力,將長江中下游的大量工廠、學校、政府和人民,搬運到了重慶。今天的重慶是中國的工業基地之一,是名副其實的西南經濟重鎮,如果沒有盧作孚,沒有李紫翔所擊節贊賞那種因陋就簡的頑強精神,確乎是難以想象的事情。
抗戰之后,中日罷兵而國共對峙,于是有重慶談判。1945年,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籌備開幕,毛澤東在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的陪同下,趕到重慶參加和談。
重慶和談是中國現代史的十字路口。經過八年抗戰,國土殘破,經濟蕭條,厭戰情緒深入人心,人們普遍希望聲望正高的國民黨和在抗戰時期發展壯大起來的共產黨能夠息兵止戈。
毛澤東在重慶住了47天,最后國共雙方于1945年10月10日簽署了“雙十協定”。
如果這場決定中國命運的談判沒有流產,中國將少死幾百萬人,戰后建設至少提前數年。在冷戰的放大效應下,這次談判還將改變世界的命運。如果和談成功,按照雙方商定方案,國共和其他黨派組成聯合政府,選舉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選舉總統,施行憲政。中國將成為美國而不是蘇聯在東方的盟友。冷戰的格局將完全為之改觀。重慶曾經被歷史的當事者寄予厚望,但在后來的歷史故事中,這場和談被舉重若輕地處理成國民黨釋放的煙霧彈:談判不過做做表面文章,協議只是徹頭徹尾的文字游戲,給東北、山東和陜西的戰事打掩護而已。
歷史在重慶發生了,但重慶從歷史上消失了。此后的幾十年時間里,學習歷史的孩子被告知,戰爭才是解決意識形態爭議的終極力量。他們知道南京和西柏坡,知道三大戰役,知道北平被改名為北京,知道金門炮戰,不知道有重慶。
遺失歷史拼圖
抗戰勝利紀功碑就建在“精神堡壘”的原址上。1949年,人們鑿去了“抗戰勝利紀功碑”的字樣,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在原來題字的位置上重新題寫了“重慶解放紀念碑”幾個大字。
重慶的歷史像是泡菜罐,不論蘿卜白菜,不論新舊真假,統統雜糅在一起。
“抗戰勝利紀功碑”也許還算不上完全消失。重慶博物館(又名“三峽博物館”)里藏有這座紀念碑的復制品。不管怎樣,“解放碑”從此成了重慶的地理標志,西南地區商業繁榮的象征。歷史在重慶不是淤積起來的,就像古都開封那樣,歷代街道重疊在一起,唐代的通衢上面有宋代的市井,20世紀的柏油下面深埋著17世紀的石頭地基;重慶是山城,是一座石頭裸露在空氣中的城市,一切都赤裸裸地呈現在表面,歷史如同風化作用,不同時期的痕跡都直白地印刻在同一個表面上,全部呈現在你眼前。
當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才是市井人生的常態。無數皮膚白皙、雙腿瘦長的重慶妹子和肩扛竹杠,竹杠上系著繩索的“棒棒”川流不息地經過此地,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塊碑的歷史緣由。也許這并不重要。在大多數重慶人心目中,解放碑只是一個商業步行街的代名詞;歷史的形式還在,但所有內容都已經遠離了這條繁華而起伏不平的街市。
陪都的歷史遺跡和其他抗戰名勝往往難以尋找。幸存的如戰時國民政府的駐地,如今在中共重慶市委的大院里,崗哨森嚴,難得看到全貌。建筑物的更新換代太快了,很難在這座城市里發現一棟老建筑——即使它們還在,也已經被高大的現代建筑淹沒了。這未免和這座城市的歷史有點兒不匹配。
向游人開放的歷史建筑大多集中在一條經典的紅色旅游線路上,沿著嘉陵江次第展開,從市中心的曾家巖50號(抗戰時期為八路軍重慶辦事處,也是周恩來的住處,人稱“周公館”)往西,依次經過桂園(原為張治中公館,國共談判期間,作為毛澤東辦公、會客和國共談判的場所)和紅巖村的大有農場(抗戰時期為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也是中共南方局的秘密辦公場所,毛澤東在渝期間主要居住地),再往西去,還有歌樂山下的“中美合作所”原址,這個機構本來是二戰時期中美政府合作建立的情報機構駐地,后來因為轄內臭名昭著的白公館和渣滓洞(曾經關押中共政治犯)而著名。
大有農場位于紅巖村,如果沒有對面小區里豪華的高層住宅,從農場的半山腰上應該能夠俯瞰嘉陵江。這座農場的主人叫饒國模,是一位有傳奇色彩的女性,她大概是中共在革命年代里最著名的同路人之一。大有農場是她從丈夫手中繼承下來的產業,后來無償地提供給中共,作為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駐地。隨著日本對重慶的轟炸升級,市區的各類政治和軍事機關陸續遷往重慶郊區,戰時中國最高的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也遷到了大有農場。
饒國模的歷史眼光堪稱獨到。重慶解放之后,她寫信給西南軍政委員會,將大有農場捐贈給新政府,希望這里能作為一處紀念場地,永久保存。這個動議最終得到了支持和響應。革命史的展覽場所兼具保存史跡和宣傳教育兩種功能,當然,決定建筑命運的功能是后者,所以,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浪潮中,其他建筑史跡被夷為平地的時候,紅色旅游的景點才能夠安然無恙地幸存下來。
現存的能夠和大有農場的規模相比的歷史遺跡,恐怕只有重慶南郊的黃山別墅群。經輪渡、大橋或者索道渡過長江,一路驅車盤山而上,南山深處的黃山別墅群,現在成了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進入大門后,樹木幽深,下有一條石板鋪成的林中路,通往山間的蔣介石、宋氏姐妹和史迪威等人的別墅,其中兼有中國政府、軍隊和駐華美軍指揮人員的住所和辦公機關。盡管許多房屋年久失修,室內的展品簡陋,陳設一概以復制品示人,不復可見當年的景象,但整體的格局和當年應無很大的差別。
黃山別墅群的核心是蔣介石的官邸“云岫樓”。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軍戰略轟炸司令兼第三飛行團團長遠藤三郎少將親率27架轟炸機,低飛席卷式轟炸“云岫樓”,差一點將正在召開重慶軍事會議的中國國家元首和各戰區長官和參謀長一舉消滅。
戰前,黃山上的別墅大多為洋行買辦黃云階的私產。1949年后,這里為西南軍政委員會接收,后來改為黃山干部療養院。云岫樓和宋美齡住的松廳,或改作病房,或者給療養院里的職工做了宿舍。直到1992年,這里被公布為重慶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療養院撤出,這些折中主義風格的房屋經過修整,作為歷史遺跡向公眾開放。
說到建筑風格,有重慶地方特色的建筑是川湘一帶常見的吊腳樓,除了洪崖洞那面鋼筋水泥的仿制品,已經看不到活生生的遺跡,但另一座仿古建筑值得一提,那就是重慶人民大禮堂。它開建于1951年,充分體現了雜糅的作風。大禮堂上半部分是有金頂的三層圓形宮殿建筑樣式,酷似北京的天壇,而下半部分是天安門的縮影——中間部分還特意加了類似天安門城樓的觀禮平臺。它于1954年竣工,落成后立刻和解放碑、朝天門一起,成了重慶的重要地標。門票上的介紹說它“氣勢雄偉,裝飾華麗”,“舉世聞名”。大禮堂二樓內部的走廊上,掛著一幅照片,顯示出大禮堂的特殊風格已經被周圍乏味的方盒子建筑淹沒了,圖片說明遺憾地說,“人民大禮堂是重慶直轄后首次公布的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之一,其周邊環境與禮堂的協調和保護工作任重而道遠,還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的努力”。
這座皇家氣派的建筑的氣質和重慶可謂格格不入。它坐落在重慶市中心,和對面造型奇特的三峽博物館,還有那座碑文寫了又鑿、鑿了又寫的解放碑,以及失去了陡峭的臺階的朝天門一起,構成了一個謎一樣的城市。它們分別屬于不同的歷史階段,拼起來卻合不成一個完整的城市。到底是什么造就了重慶?什么從重慶的拼圖中遺失了呢?
那些消失了的陪都史跡并不是重慶的歷史拼圖中缺失的最大的部分,但重慶和談有可能是。沒有這一塊拼圖,不僅不能了解重慶,更不能了解中國。問題是人們怎么看待城市,就會怎么看待歷史。有時候,拆掉一座房子,歷史就被改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