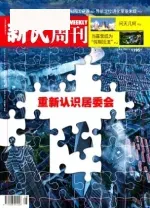獨立公正的調查是一切的前提
不管你地位多高,名聲有多大,不管是哪一年的學術成果涉嫌抄襲,只要被舉報了,就會一查到底。即便真的是疏忽導致的不規范,如果你還沒有忘記作為一個專業人士的職業道德的話,你馬上就應該出來做一個解釋,為此道歉,而不是期待這個事情悄無聲息就過去了。
媒體與學術不端
“汪暉涉嫌抄襲事件”意外引起一個爭論,那就是大眾媒體是不是討論學術不端問題的合適的場所。我認為,如果所有的大眾媒體都來討論學術界的剽竊問題,是不公平的,但要阻止嚴肅的媒體討論學術界的剽竊問題,更加不公平。一個國家出現了影響面很大的關于剽竊問題的爭論,如果這個國家的嚴肅媒體不去關注,并且把爭論用嚴肅的方式向這個國家的公民——至少是受過較好教育的公民——進行報道的話,媒體就喪失了公器的基本責任。
我用英文Mediareportingonplagiarism(媒體對抄襲行為的報道)搜索了一下,得到13萬多條搜索結果,然后用Media reporting on academic plagiarism(媒體對學術界抄襲行為的報道)進行搜索,至少有140多萬條結果,可見在英語世界,媒體報道學術界的抄襲事件非常常見。不僅常見,還是一個日益增長的趨勢。隨著信息傳播和資料收集的技術手段的進步,抄襲和反抄襲的博弈在增長,導致嚴肅媒體對此類事件的關注,也有明顯的增長。
當今時代,學術界抄襲行為不但牽涉到知識產權,牽涉到個人榮譽和學術界內部人際關系,還牽涉到公共資源(資助研究活動的政府撥款和私人捐款)的使用是否得當。如果媒體不報道,請問,媒體對這個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和社會,豈非嚴重失職?
把黑箱中的東西曝光出來,是社會進步的體現。曝光黑箱作業一定會觸動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就會出來想盡辦法封殺嚴肅媒體對此的報道。在過去20年里,這種事情在中國和其他國家比比皆是。媒體報道讓公眾有機會利用輿論糾正潛規則,培育公民意識,是媒體發揮公共利益守護者的體現。
當然,做報道與下結論是兩回事。媒體對任何專業領域的事務的報道,不能替代專業人士的專業判斷。
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世紀之交物理學界最大的一次學術丑聞,以進一步明確這個問題。丑聞發生在德國學者J.H.舍恩(J.H.SCHONE)身上。1998年,他從德國來到美國新澤西州的貝爾實驗室,一年后成為博士后研究員,研究超薄塑料的超導性能。接下來的幾年,他在《自然》和《科學》上發表了好幾篇重量級的論文,影響極大,被認為世紀之交物理學界最大的明星,極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但過了一段時間,很多科學家開始報告,根據舍恩論文中發表的實驗過程,無法得到同樣的結果。貝爾實驗室作為全世界最重要的應用物理實驗室,曾經出過6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得到報告之后,馬上成立內部調查委員會,調查舍恩在實驗中是否存在不端行為。貝爾實驗室還深怕內部調查不公正,不具備權威性,又在2002年召集了一個外部調查委員會,其成員都不是貝爾實驗室的成員。委員會的調查結果顯示,舍恩確實存在嚴重的多次欺詐行為。報告公布之后,成為爆炸性的丑聞。對這樣一個非常專業的學術領域內的不軌行為,全世界媒體的報道大概有幾十萬條。
貝爾實驗室處理此事的流程是一個標準。他們先是組織了內部調查,接著又組織了外部調查,為什么中國學術界,包括清華大學,至今沒有采取這兩個步驟中的任何一個?如果清華大學采取了這兩個步驟,還會有今天的爭論嗎?
所以,學術界自己進行的及時、公正、透明的調查,是最重要的環節。這個環節一直不出現,說明學術界存在根深蒂固的制度性黑洞。
如果學術界或教育界出現有關抄襲的爭議,學術界和教育界作為專業團體又不去采取即時措施,進行公正、及時、有效的調查,媒體的高度關注就顯得更加必要。因為專業團體已經失職,向它們持續施加壓力,防止情況又被封鎖在黑箱里,是媒體的義務。
如果反過來指責媒體對此事的報道,以及人們對此事的評論,難道要把此事變成下一個三鹿奶粉嗎?
蹊蹺的沉默
區分抄襲和不規范的標準是什么?根據學術界的常識,抄襲是學術不規范中的嚴重行為。學術不規范描述的是一種普遍現象。只有對具體的案例進行調查,我們才能夠做出判斷,這種情況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現象。
在沒有調查的情況下,大談抄襲與不規范的區別,沒有價值,反而容易攪渾水、擾亂視聽、誤導非專業人士和公眾,使得獨立、有效、公正的調查變成不可能。
如果把證據交給一個有公信力的調查委員會,判斷有沒有抄襲并不困難,只需要做一個簡單的對照,就能夠得出比較客觀的結論。
當然,如果委員會本身沒有公信力,那什么都有可能發生。幾年前,也有一個學術界的評獎委員會,把所評的獎項授給了自己。有這樣的先例的話,我們就知道,獨立和有公信力的委員會在中國是多么的難。(指2000年的“長江讀書獎”事件。李嘉誠出資、《讀書》雜志承辦了首屆“長江讀書獎”,汪暉當時任《讀書》雜志主編,是評獎委員會的成員,他的著作《汪暉自選集》是得獎著作之一,引起了很大爭議。——編者)
為調查學術不端行為而召集起來的調查委員會,負有更大的責任。通過他們的判例,公眾可以增強保護知識產權的意識,提高對抄襲和剽竊行為的警覺。調查本身就是學術界和全社會進步的必要的臺階。這也是舍恩和黃禹錫的不端行為被揭穿之后受到嚴厲處罰的原因。
如果有人指控一位學者行為不端,他有沉默的權利嗎?當然有。在調查結果還沒有公布之前,他當然可以對公眾和媒體保持沉默。
但他不能對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保持沉默。而且,一旦調查結論公布,結果對他不利,他就沒有權利繼續沉默下去。韓國的功勛科學家黃禹錫,在造假指控被證實之后,最后不是向韓國民眾道歉了嗎?
法律是一回事,職業倫理又是另一回事。當一個學者被指控抄襲,如果他具有普通水平的職業道德,在此事成為公眾事件之后,通常會主動出來有個交待;如果他的專業素養和道德感特別強,即便別人對他的指控還沒有被公眾知曉,他也會主動出來解釋。只有那些完全不尊重專業和職業道德的人,才會自始至終保持沉默。
我讀書的時候,哈佛大學心理學系有個著名的講座教授,同時又是哈佛商學院的教授。他是美國心理學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負責哈佛非常著名的心理學研究中心。當年有人舉報,說他多年以前的一篇論文有抄襲行為。他馬上主動承認,進行道歉,同時為自己辯護說,那不是有意的,而是個疏忽。他繼續留在哈佛當教授,但辭去了所有學術機構的領導職務。這要得益于他的教授職務是很多成果累積起來的,而那篇論文是唯一被舉報的案例。換句話說,假設他的教授的職務主要是依賴這篇論文的話,連教授的位置也保不住。
這個案例給學生的教育是很深的。不管你地位多高,名聲有多大,不管是哪一年的學術成果涉嫌抄襲,只要被舉報了,就會一查到底。學術界的規章制度如此嚴厲而有效,每個經歷此事的人,都終身不會忘記。
即便真的是疏忽導致的不規范,如果你還沒有忘記作為一個專業人士的職業道德的話,你馬上就應該出來做一個解釋,為此道歉,而不是期待這個事情悄無聲息就過去了。只有把職業道德和學術規矩完全不當一回事的人,才會死豬不怕開水燙。
而那些學術頭銜——包括中國的國務院特殊津貼——是一種額外附加的榮譽,一經查出當事人有抄襲剽竊的行為,必須取消。這種頭銜絕對不能和不端行為有關聯,不然就是鼓勵更多的學術不端行為。
有人有這樣的顧慮:如果學者面對任何指控,都必須自證清白,會不會鼓勵惡意的攻擊行為,從而干擾正常的學術工作?
我們把防止剽竊和抄襲作為一個優先的價值對待,確實可能引來各種麻煩。但由此帶來的不便,是我們為了保護知識創新而不得不忍受的代價。如果通過調查,發現舉報人是有意陷害,可以對他采取法律手段。但這些事情都要以獨立、公正、透明、有效的調查為前提。首先是要弄清事實。弄清事實之后,才能對爭議牽涉到的各方的行為,做一個公正的判別,然后根據規章制度,進行激勵或懲罰。
這就像有人舉報餐館用“地溝油”,如果有人舉報醫院里用過期藥品,第一步要做的事情都是調查,調查舉報是否屬實。如果你拒絕調查,還要指責舉報者,那是非對錯就完全顛倒了。
80年代的遺留問題
在中國,抄襲行為的確曾經比較普遍。它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中國古代獨尊儒術,社會上不再把知識創新、學術創新、思想創新和觀念創新當作最重要的價值,學術界、知識界、教育界能做的就是為圣人做注釋。注釋做久了,哪一點是這個人的成就,哪一點是那個人的成就,其間的界限慢慢就淡化了。這是歷史原因。1979年之前的30年里,學術界、知識界的自由越來越少,主要工作是為領袖著作做注釋,更加談不上獨創性。這是政治原因。
這兩個原因導致學術界對抄襲的意識非常淡漠。所以才有些80年代的過來人,喜歡強調80年代的學術規范和如今不一樣,讓人覺得,用現在的學術標準去衡量80年代的作品,不夠公平。
恰好我也是個過來人,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中國對學術規范的強調,恰恰是從80年代開始的。80年代初,我在上海讀書的時候,看過于光遠先生的一個講話,他提議創辦一個社會科學研究刊物,就像《中國科學》一樣,有中英文兩個版,體例跟國際一致,引用、注釋都要遵照國際通行的標準。這說明80年代已經開始強調學術規范了。
這本由于光遠倡議創辦的刊物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這本雜志一開始對體例的要求就已經相當的嚴格。對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篇論文投過去以后,匿名評審通過了,但字數超出了很多,編輯部喊我過去,要求我壓縮。我說,正文已經是從80000字壓過來的,沒有辦法再壓了,唯一能壓的,就是把大量的注釋給壓掉。幾位資深的老編審商量了半天,說注釋不能壓掉,現在做社會科學,就是要有這樣的一種體例。你引用了別人的東西,一定要有根據、有來源。
在80年代初期,學術規范雖然不能說是普遍共識,但已經在大聲呼吁地這樣做了。歷史有案可查。說學術規范沒有人提、沒有人強調、沒有人推動,錯了!那個時候已經是非常強調。黑格爾說,天黑以后,所有的牛都是黑的。那個時候天已經不黑了。有些人提到這個問題,目的是把水攪渾,不但要把水攪渾,而且要身邊所有的人都拖進去,涂得人人都是黑牛。把所有人都涂成黑牛,他就安全了。
還有人認為,寫一本書很不容易,但要舉報這本書不規范是很容易的,同樣是攪渾水的說法。我贊成對學術不端進行舉報,尤其贊成實名舉報。但對舉報而言,關鍵不是實名,而是有沒有實據。舉報抄襲和舉報性騷擾有很大不同,舉報他人抄襲一定會有白紙黑字的證據。相比起來,抄襲最容易核實,也不難處理。
處理抄襲行為,有幾個原則可以把握。比如,抄襲行為發生的時間越早,也就是越靠近70年代末,處理上就要輕微一點。前提是抄襲者必須道歉。中國的法律說坦白從寬,你不能不坦白就要從寬。
第二,如果抄襲行為發生時間很早,還要看抄襲者有沒有對抄襲行為進行更正。如果著作再版加印的時候還是老樣子,說明你延續了抄襲行為,處理應該從重。
第三,如果抄襲行為發生的時間很早,抄襲者并沒有從抄襲行為中間獲得任何的好處,也可以從輕處理。
這是三個政策標準,非常合理。如果舉報過于夸大,你自己認為只是一個疏忽,也不能什么都不做,不道歉,不吭聲,不糾正著作,就是要求全國人民忘掉這件事,然后繼續享受特殊待遇,還要對舉報人進行追究。這不是混淆是非嗎?這不是顛倒黑白嗎?(本文根據丁學良教授口述整理。未經作者本人審閱。本刊實習記者陳靜茜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