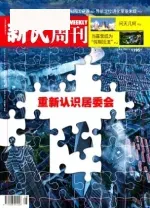日本文化的香港表達
嚴飛
在強勢文化向心力的吸引下,年輕一代香港人的潮流風向標相應得到改變;與此同時,本地文化人則應努力向內延伸挖掘出新的含義,藉以滿足本土文化的需要。
作為特定時空下的特殊產物,香港曾被外國作家形象地比喻為“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在經歷了164年的殖民淬煉之后,香港受英國文化影響至深,成為名副其實的中西交匯之地。然而近年來,隨著日本文化的強勢崛起,并伴隨著日劇、電影、卡通、飲食、服裝等多領域潮流的涌入,香港的中西交匯改了方向,成了港日融合。
翻開香港的報紙,幾乎每家主流媒體的娛樂版,天天都會有日本明星的大幅照片和海報,每家主流媒體的廣告版,也天天會刊載日本旅行團的宣傳和推介。事實上,自從日本外務省于2004年4月1日開始讓香港人享有90日內免簽證短期逗留日本的待遇后,香港人旅日的風潮就好像內地開放香港自由行一樣,猛烈而瘋狂。與此同時,銅鑼灣世界貿易中心前的一家壽司店,每天無論任何時候,永遠站立著眾多等候進場的食客;專門售賣日本貨品的Citysuper超級市場里永遠人山人海,尤其是那些高學歷、高收入的城市中產階級,更是把逛Citysuper視為每日必修的功課。至于今天的香港年輕人,一提起日本,更是有說不完的話題,“卡哇伊”時刻掛在嘴邊,Cosplay成為服飾代名詞,電車男、御宅族(Otaku)、單身寄生族(Parasite Single)紛紛現身,壯大為當下至潮的新生代族群,經過漫畫改編的電影《娜娜》、《死亡筆記》等更是高票房的保證。這一切,都在潛移默化間放大了香港年輕人對日本文化的瘋狂,并逐步成為影響他們價值取向的主流力量。
香港對日本文化的多方位移植,引起了本地文化工作者湯禎兆的關注。這位在香港研究日本文化的代表人物,寫作領域主要集中在日本社會文化觀察、日本電影解讀、文學創作及評論等。其最擅長以“社會一分子”的方式主動進入日本世界,感同身受地理解日本文化所產生的社會、人文、心理等多重因素,從而產生一種“共在”的狀態。
這樣的“共在”性觀察,于湯禎兆所出版的一系列觀察日本的書中(例如《整形日本》、《命名日本》、《情熱四國》)表現得淋漓盡致。在這些書中,湯禎兆不僅分析了日本流行文化,亦獨具匠心地巧妙穿插進港日對照作為延伸脈絡,幫助香港認識當代日本年輕人文化的同時,又能清楚地審視港日交融的源頭、發展和未來影響。
舉例來說,湯禎兆認為,這幾年,內地文化事業的發展進步神速,雖然時有反日的潮流與傾向,但在對日本文化的接納與吸收上,較之于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顯得多元和開放。特別是在文學領域,村上春樹已經成為日本文化的一種象征,對于村上春樹的作品,內地比香港、臺灣所推出的翻譯版在產量和速度上都來得快。然而,由于內地作家之生活標準、形態均與日本社會的狀況大相徑庭,他們不曾經歷因極度繁榮富庶而產生空虛感的心理狀態,因而在翻譯村上春樹的作品之時,只會流于表面,無法深刻傳遞出文字背后的文化韻味。
再看香港,在以往,香港人對日本文化多給予較大程度的尊重,若在日本社會里涌現出一個新的名詞,有心做日本文化研究的人士就會熱切地追求該方面的知識、尋求更深入的了解。可是在現如今,香港人在意的往往是如何吸納該名詞、術語,對之進行再利用,而非結合本土特色再創造。以日本的蟄居族(Hikikomori)為例子,在日本,所謂蟄居族,是指在加速運轉的社會壓力面前,因感到不能滿足社會角色的要求,而選擇以逃避來斷絕與社會聯系的年輕人。而當這個詞匯傳播到了香港,在香港的社工眼里,他們所關注的并非日本那些蟄居族、隱蔽青年的真實情況,而只是純粹片面地借用這一名詞,套于香港的狀況之上,繼而用作向政府爭取資源的根據。
由此可見,由于“不共在”的缺陷,使得內地和香港在吸納整合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各潛藏著不同的毛病。在強勢文化向心力的吸引下,年輕一代香港人的潮流風向標相應得到改變;與此同時,本地文化人則應努力向內延伸挖掘出新的含義,藉以滿足本土文化的需要。通過剖析強勢文化來反省自己,原本就是跨文化書寫中的慣性潛臺詞,差別只在于程度、隱顯,以及書寫者的自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