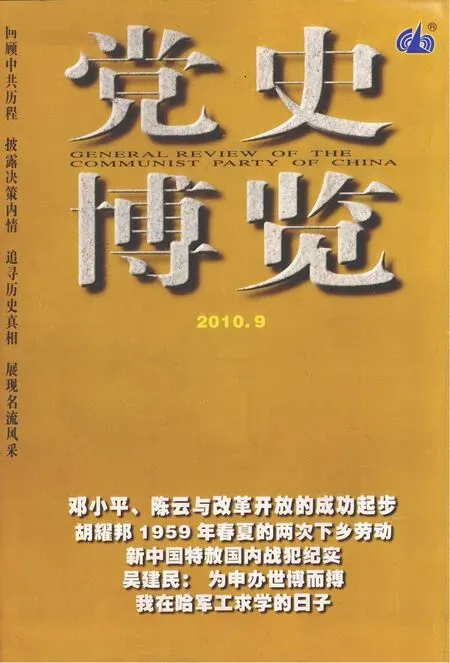鄧小平、陳云與改革開放的成功起步
○陳東林
鄧小平和陳云,有著十分相似的經歷。鄧小平生于1904年,逝世于1997年;陳云生于1905年,逝世于1995年。兩人很早就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共八大確立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最年輕的兩位,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共同成為改革開放的奠基人。
應該說,兩人的性格和作風,又是有較大差異的。鄧小平可稱為“舉重若輕”——敢于抓住機遇,開拓進取,不懼風險,格言是“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陳云可稱為“舉輕若重”——長于治理,善于交換、比較,格言是“摸著石頭過河”。兩人的經濟主張也反映了事物的兩重性,形成了相輔相成的局面。
攜手領導第二次國民經濟調整
鄧小平、陳云相輔相成,始于1979年開始的第二次國民經濟調整。
1978年6月,出國考察和在香港、澳門考察的三個經濟代表團向中央匯報了國外日新月異的情況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后,極大地激發了中央領導層的熱情。中央決定抓住有利時機,大規模引進國外資金和技術設備進行高速建設。1978年7月至9月,國務院召開務虛會,研究加快建設速度問題。會議總結報告號召,要組織國民經濟新的大躍進,要以比原來的設想更快的速度實現現代化,放手利用國外資金,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八年基本建設投資從原設想的4000億元增加到5000億元。十年引進800億美元規模,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億美元。

1978年12月,鄧小平(右一)、陳云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主席臺上。
陳云對這個大引進計劃持保留意見。7月31日,他向主持務虛會的李先念建議,會議最好用幾天時間專門聽聽反面意見。他又向谷牧提出,務虛會是否多開幾天,聽聽反對的意見,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見。他專門找有關人說,引進資金那么多,又那么容易,但考慮過沒有,引進了國外資金,我們中國要有配套資金。就算人家借給你那么多錢,我們自己有那么多配套資金嗎?
12月10日,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發言,提出五點意見。針對黨內普遍要求快的情緒,他提醒大家要清醒,引進項目要循序而進,不要一擁而上。生產和基本建設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樣樣有缺口,實際上擠了農業、輕工業和城市建設。
陳云的不同意見,引起了本贊成建設速度快些、規模大些的鄧小平的注意,重新考慮幾年內引進800億美元規模的想法。
1979年1月5日,陳云將新華社的一份材料批轉給鄧小平,指出:“我認為有物資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鄧小平批示:“請計委再作考慮。”1月6日,鄧小平找余秋里、方毅、谷牧等談話,再次肯定陳云的意見“很重要”。他說:我們要從總方針來一個調整,減少一些鋼鐵廠和一些大項目。今年計劃有些指標要壓縮一下,不然不踏實,不可靠。
更重要的一步是,鄧小平又同主持財經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議成立國務院財經委員會,陳云任主任,主持全國財經工作。李先念贊同,并主動表示給陳云當副手。
3月21日,陳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搞現代化要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我們國家是一個有9億多人的大國,80%的人口是農民。革命勝利30年了,但不少地方還有要飯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別的國家發展快,只看到可以借款,沒有看到本國的情況。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債,靠不住。
鄧小平十分支持陳云的意見。3月23日,他在講話中說,中心任務是三年調整。這是個大方針、大政策。經過調整,會更快地形成新的生產能力。這次調整,首先要有決心,東照顧西照顧不行,決心很大才干得成。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中央制定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開始國民經濟調整。9月,陳云將財政部整理的《關于1950年——1979年國家財政收支總額及基建撥款的資料》印發中央負責人。材料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是出在基本建設超過了財力物力,大上大下,情況一好就折騰等。陳云在中央會議上重申,經濟調整是必要的。一是不能靠赤字搞建設,二是利用外資的可能是有限的。像寶鋼、平果鋁礦、三峽水電站等那樣大的工程,每個五年計劃大體上只能建成一個。陳云總結說,我們應該探索在不再折騰的條件下有較快的發展速度。
1980年3月,鄧小平對陳云的“不再折騰”給予高度評價:陳云同志出了個題目,就是積累和消費保持什么比例。過去的教訓是超過了,總以為積累率越高,建設速度就越快。年底,他又表態說:“我完全同意陳云同志的意見,今后一段時間內,重點是要抓調整,改革要服從于調整。”
同時,鄧小平對調整的側重點與陳云又有所不同。關于發展速度,他說:“我贊成勁可鼓不可泄。”調整是為了什么?“是為了創造條件,使得在調整過程中,特別是調整以后,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又比較快的發展速度。”“如果到1982年、1983年,我們的速度不能夠更快一點,我看交不了賬。”關于利用外資,鄧小平贊成陳云的要有限度的考慮,也贊成陳云的意見,對引進項目要一個一個具體研究,特別吃虧的我們不干。他又指出,外資“不管哪一種,我們都要利用,因為這個機會太難得了,這個條件不用太可惜了”。“現在研究財經問題,有一個立足點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資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而陳云在領導經濟調整工作中,也注意遵循鄧小平“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資”的長遠戰略。從日本引進資金和技術設備建設寶鋼,是當時22個大引進項目中最大的,占當年合同引進資金的60%。1978年為寶鋼建設已經追加投資十幾億元,是上馬還是下馬?為了補救寶鋼倉促上馬的不足,陳云親臨上海,反復考慮。第一次,認為應該基本立足國內,買技術,買專利,只進口關鍵設備。第二次,他到上海聽匯報后,擔心單靠現有技術上不去,想設備全部進口,同時也買制造技術,買專利。第三次,他離開上海時,又認為還是按照三委(國家計委、建委、經委)三部(冶金部、外貿部、機械部)和銀行的意見辦。1979年9月,中央同意陳云、李先念批準上報的報告:寶鋼一期工程繼續干,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對外已簽的合同進行賠償,已進口的設備妥善保管。這樣,在調整中對外引進仍有發展,避免了一些經濟損失。
事實上,鄧小平也在陳云的“自由外匯不足”的考慮之外,開辟了一個“善于利用外資”的新思路。他說,利用外資是一個很大的政策,我認為應該堅持。問題是怎樣善于使用,較快見效,解決好償還能力問題。我們干幾件事,慢慢就懂了。當時,22個大引進項目中的儀征化纖工程被調整下馬后,因國內確實急需,有關部門心有不甘,繼續探索新辦法。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長榮毅仁找到鄧小平,在鄧小平的支持下,1981年通過在日本發行100億日元債券,分別從西德和日本引進主要裝置及技術,使工程于1982年1月開工,1984年第一套生產裝置就投產。此次集資被稱為“儀征模式”,開創了國家重大項目由財政撥款改為境外發行債券的先例。
兩人關于經濟建設發展速度側重點的比較
鄧小平的側重點是他晚年總結的“上臺階”飛躍思想
1991年8月,鄧小平在談到改革開放時說:“這一段總結經濟工作的經驗,重點放在哪里?我看還是放在堅持改革開放上。沒有改革開放十年經濟發展的那個飛躍,取得順利調整是不可能的。強調穩定是對的,但強調得過分就可能喪失時機。”“可能我們經濟發展規律還是波浪式前進。過幾年有一個飛躍,跳一個臺階,跳了以后,發現問題及時調整一下,再前進。總結經驗,穩這個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我們不抓住機會使經濟上一個臺階,別人會跳得比我們快得多,我們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總覺得有這么一個問題。機會難得呀!”
1992年一二月間,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又指出:“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看起來我們的發展,總是要在某一個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發現問題及時加以治理,而后繼續前進。”“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個問題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當,造成誤解,就會變得謹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開手腳,結果是喪失時機,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從上面可以看出,鄧小平強調經濟發展要抓住有利機遇,進行跳躍式的發展,不能過于求穩。用技術語言表達,是一波飛躍后,進行平臺整理,再繼續下一波飛躍。總體是均值快速提升的一條波浪式斜線。
陳云的側重點是他一貫強調的“綜合平衡”思想
關于經濟建設發展速度的問題,際云認為:一、建設規模與國力要平衡,要和國力相適應。這是他“綜合平衡”思想的主線。他提出:“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建設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二、部門、行業之間要平衡,包括計劃與市場,農、輕、重,財政支出和收入,進口與出口,中央與地方,貨幣與市場之間的平衡等。三、基本建設與人民生活要平衡。他指出:“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看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種平衡大體上是個比較緊張的平衡。建設也寬裕,民生也寬裕,我看比較困難。”這是改革開放前的30年制定建設方針的基本考慮。四、長線與短線要平衡。長線就是指五年計劃、長遠規劃,短線指年度計劃。他主張短線平衡:“按短線搞綜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綜合平衡。所謂按短線平衡,就是當年能夠生產的東西,加上動用必要的庫存,再加上切實可靠的進口,使供求相適應。”“過去幾年,基本上是按長線搞平衡,這樣做,最大的教訓就是不平衡。”他主張:“必須瞻前顧后、前后銜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損失。”
總結起來,陳云的“綜合平衡”思想中的特點是:一、平衡是積極的平衡,“必須從我國的經濟現狀和過去的經驗中去尋找。既要研究那些已經形成的比較合理的比例關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來的矛盾”。也就是說,平衡是為了發展,而不是為了停滯。平衡要造成緊張、持續的狀態,發揮最大效益。二、“所謂綜合平衡,就是按比例”,就是高速度。1979年,他在給中央的信中說:“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在穩定和發展之間,陳云比較注重穩定。他說:“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必須避免反復和出現大的馬鞍形。”“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他主張經濟發展應當盡可能做到起伏不要大,是一條平穩向上的斜線。
怎樣理解兩人側重點的不同
鄧小平、陳云的主張,反映了國家經濟建設在不同時期的側重點。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是打基礎的時期,綜合國力比較弱,抗御風險能力不強,國際環境也比較嚴峻,長期面臨封鎖,后來基本沒有外援。這樣,任何大的經濟起伏都會造成嚴重的后果,所以強調穩和平衡,是正確的方針。陳云講平衡最多的三個時期:一是1957年,“大躍進”冒頭;二是1962年,“大躍進”造成嚴重困難局面;三是1979年,追求高指標又超過國家承受能力。因此,他是有針對性的。
而鄧小平強調不斷“上臺階”,是在經過前30年建設,國家初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能夠承受一定風險的改革開放時期。面臨國際環境相對緩和,世界進入新科技飛躍時期,如果不以超常速度發展,中國將難以趕上世界水平。所以強調高速度發展,是主觀允許和客觀需要的方針。1984年至1988年上了一個臺階,1989年起用三年治理整頓;1992年至1994年又上了個臺階,1995年起用兩年宏觀調控。兩次“上臺階”,都沒有發生大的動蕩,說明是可行的。

1981年6月27日,陳云、鄧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從左至右)在一起。
兩人的主張都不是片面的,而是有重點的兩點論。鄧小平的“上臺階”,“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跳躍也不是無休止地連續跳躍。上一個臺階,再調整一下,調整就是平衡階段。總體上看是包括著平衡的,可以叫做均線平衡。陳云的平衡是積極的,不是停滯僵化的,長期積極平衡才能保證高速度。他強調綜合平衡就是按比例,這個比例不是一成不變的計劃,而是通過市場調節,在解決暴露的矛盾中有變化的。
鄧小平的“上臺階”,是指的一定發展時期。他說:“總是要在某一個階段,抓住時機,加速搞幾年。”至于穩,“以后還用不用這個字?還得用。什么時候用,如何用,這要具體分析”。
兩人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關系側重點的比較
鄧小平的側重點是“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過去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不是商品經濟,更不是市場經濟。同樣,西方經濟學也一直把市場經濟當做資本主義特征來確認。
鄧小平早在1979年11月就提出了質疑:“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應該說,當時的市場經濟,實質還是商品經濟,指的是市場調節。但是,鄧小平的質疑,拓寬了人們的思路,有著振聾發聵的意義。
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首次提出了“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斷。對此,鄧小平高度評價說:“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開前,鄧小平又突破性地指出:“為什么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
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根據他的意見,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針。
陳云的側重點是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鳥籠經濟”關系
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陳云就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陳云為了刺激經濟快速恢復,曾經大力借助商品經濟手段,如搞了高檔商品的高價出售,使貨幣快速回籠;向毛澤東建議:在農村實行分田到戶,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兩條都是對計劃經濟的“離經叛道”。因此,他遭到嚴厲批判,長期被斥為“老右”。在1978年的國務院務虛會上,李先念正是汲取陳云要用市場經濟對計劃經濟進行大補充的意見,在總結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口號。
但是,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后,陳云卻多次提醒注意計劃的作用——“鳥籠經濟”關系。
1982年12月,陳云借用黃克誠的“鳥籠”比喻闡述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效果顯著。……但是,我們也要防止在搞活經濟中,出現擺脫國家計劃的傾向。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指導的搞活。這就像鳥與籠子的關系一樣,鳥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在籠子里飛。當然,‘籠子’的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經濟活動不一定限于一個省、一個地區,在國家計劃指導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區,甚至不一定限于國內,也可以跨國跨洲。另外,‘籠子’本身也要經常調整,比如對五年計劃進行修改。但無論如何,總得要有個‘籠子’。就是說,搞活經濟、市場調節,只能在計劃許可的范圍以內發揮作用,不能脫離計劃的指導。”
如何看待兩人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上的側重點方面的不同
兩人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上的側重點方面的不同,可以這樣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鄧小平針對過去的計劃經濟脫離市場需要的弊病,大膽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體制的主張,這是一個偉大的開拓。沒有這個開拓,社會主義制度就不能充滿活力,就不能在經濟全球化的新局面下取得立足之地和勝利。
陳云的“鳥籠經濟”,是探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的重要補充和保障。他的“鳥籠”,不是僵化固定的,而是一個隨著需要可以靈活變化的,甚至“可以跨國跨洲”,這自然包括著市場經濟的含義,不存在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
陳云的“鳥籠”,是針對20世紀80年代搞活中出現經濟犯罪猖獗和經濟秩序混亂等情況而發的。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確實隨時需要一個“鳥籠”,為搞活加上一個“不亂”的安全閥。
兩人領導機制產生相輔相成效果的原因
鄧小平、陳云這一對人物,與毛澤東、周恩來這一對人物的關系十分相似。毛澤東、鄧小平是最終的戰略設計者和決策者;周恩來、陳云不僅是參與決策者,更是執行者和管理者。毛澤東、鄧小平善于大刀闊斧的宏觀開拓,周恩來、陳云善于運籌帷幄、日理萬機的管理。
但是,毛澤東、周恩來的領導機制卻沒有完全得到鄧小平、陳云那樣的相輔相成效果。如1956年周恩來就提出要反對“冒進”,但以后兩年連續遭到嚴厲批判,終于導致了“大躍進”失敗的嚴重后果。其原因在于當時黨的民主制度的不健全,毛澤東、周恩來領導機制最后只有單補的一定作用,沒有制約的作用,最終單補作用也因為缺乏制約而失效,變成事后的補救作用。
鄧小平、陳云領導機制能夠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果,首先在于,通過總結“文革”教訓,由鄧小平倡導,黨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有了比較鞏固的基礎。鄧小平尊重和信任陳云這位黨內經濟大管家的見解和能力,提議陳云出山主持財經工作;陳云也首先提出并完全擁戴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領軍地位。
其次,鄧小平、陳云領導機制的成功,不僅因為兩人互相尊重的品格和作風,更因為兩人對中國國情的認識,有著實事求是的共同基礎。他們關于中國現代化應當走什么樣發展道路、現代化目標是什么樣的,即對中國特色的認識,是一致的。
關于發展道路,1979年1月,鄧小平就指出:今后引進的重點要放在見效快、賺錢多的項目上。這樣能增加就業機會,對改善人民生活也有利,更不會發生償還不起外債的問題。這和陳云基本建設要適應綜合國力,積累率不能過高,要適當減少重工業投資、發展輕工業積累資金的認識是一致的。
關于現代化目標,1979年3月,鄧小平同外賓談話時,用了一個新名詞,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他說:現在我們的技術水平還是你們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紀能達到你們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同月,他還進一步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特點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在這個基礎上,鄧小平設計了中國式的小康社會目標。這和陳云關于中國是個落后的農業大國,搞現代化不能起點過高、避免欲速則不達的“再折騰”的認識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