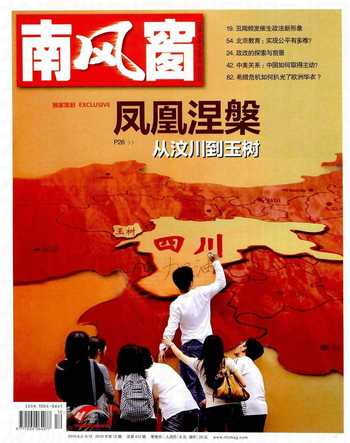“人的重建”剛剛開始
陳統奎
“人的重建”是災后重建更為核心的主題。然而,“造人”之難遠在造建筑之上。
“浪漫小鎮,自在龍池。Long Chi Comfortable,Romantic Town。”
這句中英文對照的主題語和新設計的龍池LOGO無處不在,從巨大的戶外廣告牌到鄉村旅游信息中心小樓的墻體上,從農家樂的遮陽傘到停車場的指引牌上。震后兩年,一個時尚前衛的新龍池已經躍然山谷中。九曲十八彎的龍溪河從高山上奔流而下,河畔兩邊,色彩飽暖的“山地別墅”錯落有致,掩映山水間。不久后,龍池還將成為“免費使用覆蓋全鎮無線網絡”的無線小鎮。
龍池鎮位于都江堰市西北17公里,下轄5個村和一個社區,總人口約3200人,占地面積89平方公里,地廣人稀,森林覆蓋率達87%,擁有大熊貓、羚羊等珍稀動物。“5·12”地震,距震中映秀鎮僅3公里的龍池鎮受災特別嚴重,房屋毀損率98%。今天,廢墟上已經建起一座新集鎮,人們正陸陸續續從板房中搬進美其名目“山地別墅”的安居房。余下不多的安居房和臨水商業街正在加班加點修建,以迎接今年9月的開業大典。
而在都江堰市副市長、龍池鎮黨委書記王晉看來,“人的重建”是災后重建更為核心的主題。然而,“造人”之難遠在造建筑之上。
社區意識從哪里來?
地震前,40歲的陳朝華在龍池鎮云華村過著“原始生活”。2009年9月起,她有了一個新身份——上海市閘北區熱愛家園青年社區志愿者協會(以下簡稱“熱愛家園”)“美麗新家園”震后社區發展示范站共建項目兼職職員,月薪600元。
從都江堰市去往龍池,汽車不斷爬山。在車上,陳朝華興奮地講述自己半年多來的成長:“原來我理解,這個工作給錢我就干,不給錢我就不干。后來我慢慢接受了服務社區的精神,知道這不是錢的問題。是服務當地人的一種理想。”不久前,陳朝華被邀請去上海開了6天的NGO會議,使她的眼界和價值觀發生了180度的轉變,“唐虹6歲的女兒也是志愿者,還有60多歲的老爺子也是志愿者,原來當志愿者不分老少”。
更令陳朝華印象深刻的是,上海的志愿者們不僅付出時間服務他人,開會時吃飯還要自己掏錢。地震前,在山上過著散居生活,那是一個閉塞的世界,陳朝華自稱是“坐井觀天”,不知“志愿者”為何物,“社區”是何概念。上海之行,對她來說是一次“觀念震蕩”。
震后,云華村村民被迫遷居山下,住到政府搭建的臨時板房屋中,由散居變成聚居。2008年7月,唐虹和其他“熱愛家園”志愿者第一次來到云華村板房區時,已經發現“村民對新社區的熟悉感與認同度不一致”,意識到“幫助村民認同新的社區。自覺保護與建設新社區,是災后重建的重點與難點”。因此,唐虹等人提出“美麗新家園”項目的愿景是:培養村民自治組織。培訓農村“能人”,最終建立起一個有自己獨特文化背景、可以互幫互助、自我管理的新型農村社區。
云華村的平均家庭人口少于3.5人,家庭呈小型化,伴隨著家庭的小型化,家庭對每個成員的支持在減弱。同時,老齡人口已經大于總人口的10%,老齡問題將成為云華村新的社會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都需要社區的發展與支持。”2008年9月28日,“美麗新家園”震后社區發展示范站共建項目正式進駐云華村板房聚居區,開展各項文化活動,加強村民間的交流,栽培“社區凝聚力”。
如今,云華村大部分人已經搬進“統規統建”的新龍池鎮“山地別墅”,和其他村的人一起聚居成一個1500多人的大社區。2010年五一前后,“美麗新家園”項目志愿者又來了,他們給村民上了“新群居”生活第一課——用氣用電安全知識培訓。村民搬入新房后,第一次用上了天然氣。但卻不知道該怎么使用,志愿者通過PPT形象地介紹安全使用方法。此外,送“福”上門活動、重建“攝影展”、“垃圾分類”體驗式環保宣傳活動、“愛牙護牙”健康講座、影片放映和“大家都來唱”五一歌會,“美麗新家園”項目組為村民營造起公共活動空間,幫助村民適應聚居生活方式。
耳濡目染中,陳朝華慢慢理解了社區概念。“以前各家住各家的山頭,現在住在一起,如果不講衛生,很容易引發疾病。”陳朝華已明白聚居和散居的一些區別。“美麗新家園”項目舉辦的公共活動從豐富鄉村文化生活出發,透過社區共同生活體驗來培養“社區共同體”感受,進而激發個體萌發社區精神。當地居民觀念的轉化與行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志愿者的作用是“扶上馬,送一程”,催生和培養社區公共服務意識和能力。
“唐虹他們的努力5年后就看出效果了。”龍池鎮政府辦公室主任王丹說。
而陳朝華之前,“美麗新家園”項目在云華村的專員是陳佩。2008年國慶期間,上海應用技術學院社會工作專業大四學生陳佩作為志愿者,第一次來到云華村。后來,唐虹等人看重陳佩的專業背景,就招她為項目專員。
唐虹的構想是,讓陳佩發現并培養當地人才,“提高當地人自我發展的能力”。項目“執行委員會”的5個人,唐虹在上海,陳佩在當地帶3個村民。半年時間里,陳佩和一位老奶奶合住一個30平方米左右的板房屋。初來乍到,因為年紀小個子小,“大人把你當小孩看”,陳佩常感力不從心:“志愿者、民間組織、公益行動,這些概念對他們來說比較新,感覺不是他們做的。我在這邊沒什么影響,他們只知道我是來做好事的,沒覺得這些工作跟他們有什么關系。”
執行委員會一起討論事情,陳佩發現,村民很少主動,必須由她提出具體事情,“他們偏重于執行”。在這種情況下,陳朝華被聘請為兼職職員,陳佩帶這個大姐做“徒弟”。“培養村民做社區公益服務很難,他們去打工至少能賺錢,但做公益沒有回報,你描繪的東西,他們看不到。”陳佩說,“災后重建以村民為中心,道理是正確的,但是村民不這么認為,那是你們想改變他們的想法而已。”只有讓陳朝華快速成長,才能“示以實例,以誘人民”。“讓人民改變”這5個字不應是一廂情愿的想法。
陳朝華陸續接受了NGO工作方法、財務、電腦等培訓。2009年9月,陳佩到成都念研究生,陳朝華順利接棒,成為項目當地志愿者,協調政府關系,安排外地志愿者開展工作,與村干部配合組織村民活動,一切都上軌道了。不過,陳朝華遠未具備“社區領袖”的能力和影響力,她還無法靠自己的人格魅力來凝聚社區共識和推進工作。農家樂是知識經濟
龍池最富裕的村是南岳村。從新集鎮沿著龍溪河逆流而上,已經修起兩車道的柏油路。南岳村4組災后重建的“自建房”就分布在路兩邊,家家辦“農家樂”。去都江堰國家森林公園,南岳村4組是必經之地,這里距離新集鎮3公里左右,被規劃為龍池“國際山水田園風情旅游小鎮”的副中心。
在南岳村4組,每一棟建筑都是獨一無二的,既有傳統川西民居建筑元素,又有典型羌族石砌碉樓建筑形態,“漢羌結合”。今年4月,全國政協委員、徐悲鴻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之子徐慶平先生來到這兒,贊賞不已:“這些房屋的質量和美感俱佳,比我見過的意大利、法國的房屋還漂亮,此地的建筑水平一下躍進了50年!”
那些農家樂的名字。個個都起得優雅別致:“仙足客棧”、“迎亭園”、“紫怡小筑”、“龍溪人家”、“如意山莊”……王丹告訴記者,原先農家樂主人起的名字都很土氣,政府便一一幫他們設計新店名,同時融入時尚設計,人文內涵,而且與建筑風格融為一體。農家樂起名這件事讓村民們感受到知識的力量和魅力。這些農家樂的目標游客都是擁有知識的中產以上家庭,知識型店名可以制造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
龍池的“鄉村課堂”便是為構建知識型農家樂而開設。“陽光客棧”的女主任黨曉紅上課后收獲不少:“以前修房子圖方便,修在公路邊,客人來了車都停不了;為了多出幾間房,把房間做得小,連個掛衣服的地方都沒有。參加了鎮里舉辦的鄉村課堂講座后,我們思路打開了,現在把新房子修得離路遠些,留足停車空間,栽上樹,鋪上石子路,反而更有吸引力。大房間寬大敞亮,可以放上大床,擺上裝飾品,檔次品位提升后。房價也可以漲一漲。”王丹介紹,“鄉村課堂”還請過香港一家著名酒店的管理者來講課。這個不定期課堂會繼續辦下去。
據王丹介紹,龍池也已經成立了農家樂協會,但因為格局有限,這個協會遠未發揮出“造人”的功能和作用。事實上,農家樂是一種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鄉村生活創意產業,當地政府已經認識到這個高度了。龍池不只是“賣山水”,“賣農家川菜”,更要“賣服務”,“賣生活方式”,呈現一種生態、悠閑、慢拍的生活方式,并提供給市場檢驗。而這些,都離不開“人的重建”及其意識和行為方式的躍升。
而“人的重建”離不開相應社會土壤和機制。這就需要一個多元合作平臺,來整合政府、企業、NGO等方方面面的社會資源,形成日常化、持續化的社區活動機制,系統而有步驟地陪伴龍池人一起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