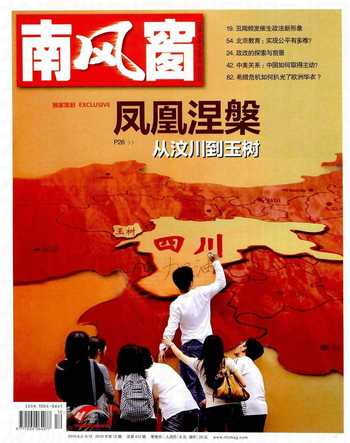北京教育:實現公平有多難?
田 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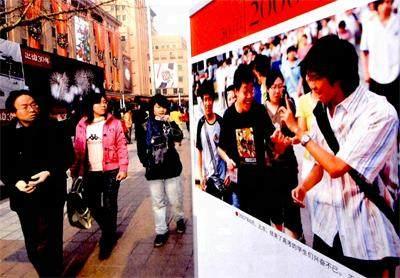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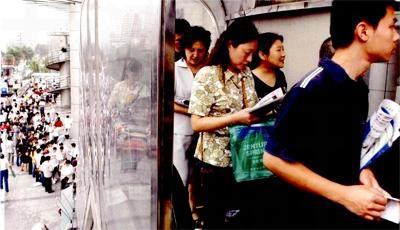
讓人沮喪的不是制度進步的艱難,而是歧視與偏見根植于每個人的心中,在記者接觸的各類家長中,權貴歧視平民,普通市民歧視外地人,不愿讓自己的孩子與外地人為伍,有錢的外地人歧視那些引車販漿人的后代,害怕他們把自己孩子帶壞。
6月是中國的高考時節,每年這個季節也都是章冬翠最揪心的時候,從1985年開始,她舉家從浙江溫州農村搬來北京已經25年了,她自己早已適應了沒有戶口的北京生活。但她的女兒、15歲的丁璇卻無法適應。
從小學開始,丁璇已經在北京讀了10年書,無論在哪個學校,一直都是各類考試的第一名,因為學業優秀,她的父母并沒有讓她像大部分外地同齡孩子那樣中途輟學,而是選擇了將讀書進行到底,“其中經歷的千辛萬苦都已經走過來了,但現在面臨高考的門檻,無論如何也邁不過去了。”章冬翠說。
過去的5年,北京城里像丁璇這樣的外地孩子越來越多,到現在已經有40萬左右,早已成為政府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實際問題。對外地人口子女入學的限制最關鍵的兩個環節,一是“小升初”,一是高考。
今年5月,北京市政府廢除了1986年沿用至今的《中、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并規定非京籍享受同等入學待遇,并為其建立學籍。
雖然教育部門同時也不忘強調,這樣的待遇僅僅限于義務教育階段,而不包括高中和高考,但畢竟北京教育向外地人開了一扇窄門。不過這項變革卻引起了不少家里有孩子的北京市民相當強烈的反彈。
有學籍就意味著外地人的孩子可以參加派位、推優、評選三好學生,可以堂而皇之地跟京籍學生一起競爭優質教育資源。在記者的采訪中,不少北京家長驚呼“狼來了”,對這項改革的抱怨、對外地孩子的憎惡溢于言表。
“我們已經被教育折磨得痛不欲生了。”一位姓孫的北京家長說,北京那點可憐的優質教育資源被權貴階層壟斷一部分,如果再被外地人搶走一部分,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該如何生存?
作為首善之區,北京擁有全中國最優質的教育資源。卻也面臨著從小學就開始的最殘酷的競爭,權貴與平民、窮人與富人、本地人與外地人,人人都希望通過教育維系或者改變家族下一代的命運,教育層面的沖突和斗爭也才剛剛開始。
統考、派位與“共建生”
1998年是北京基礎教育的一個分水嶺,在那之前。跟全國各地一樣,北京的小學生要想升入初中,都需要經過統一的升學考試,但這樣的統考制度,從1980年代開始,實行了將近20年后,已經讓那個年代的小學生們苦不堪言。
時任北京一中校長的王晉堂告訴記者:“那個時候,考試的題目一難再難,可是,語文數學兩門課總共200分,大量孩子還是能夠得到滿分,以至于很多中學的分數線都劃在了198分。”
這樣的高分數更多是小學生們死讀書、背試題的結果,沉重的課業負擔已經讓小學教育異化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1998年,北京市的教育部門終于下定決心,取消了小升初的統一考試,引入了一項名為“電腦派位”的入學機制。這項源自于西方主要是英國倫敦等大城市的教育制度被當時的學生家長稱為“洋抓鬮”。
電腦派位以公平為導向,取代了統考制度下的以分數為導向來分配學位,在當時的教育環境下,可以說是一項激進的、充滿著理想主義色彩的教育制度。但它在北京落地的第一天起,就遭遇了極大阻撓。
“一開始,主要是兩股力量反對。”王晉堂說,一是學生家長,另外就是當時的名校,即使被派去了比較差的學校,家長們也都會想盡一切辦法將孩子的學籍調出來,再送到心目中的好學校,有錢的用錢,有權的用權。而學校則以各種理由,拒收派位生。
對電腦派位最致命的破壞則源于共建學校制度。這是一項最具北京特色的招生模式,其基本內涵就是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為了滿足員工子女入學,通過單位贊助錢或物的方式與知名中學建立“共建”關系,從而使雙方“互惠互利”,單位員工子女可以輕松享受極為緊缺的優質教育資源。
軍隊和外交部的共建校是較早的,后來擴展到各大中央部委,再后來,北京市級機關、大型國有壟斷性企業,甚至是實力雄厚的民企,都有了自己的共建校。據北京媒體報道,到今天,房地產商、中小企業,甚至街道、派出所等也與學校建立了共建關系。不同單位與學校的共建門檻有所不同,比如共建費用問題,每個學生不同單位之間相差十多萬乃至幾十萬元。
在電腦派位之外,共建制度給特權留了個后門,而且越來越大,越走越順利,到今天,這已經成為北京子女人學最省錢、省力又便捷的途徑。共建生擠占了很大一部分優質的教育資源,尤其是在那些知名的中學,有的學校共建單位從一開始的一兩個發展到后來的十幾個。
“共建生”對電腦派位規則的破壞遠不僅僅是擠占名額,哪個學校的共建單位多,共建單位級別高,越是能吸引更多家長們趨之若鶩,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去,從而也讓學校教育質量的差距也越來越大。這樣的惡性循環讓北京基礎教育離均衡化越來越遠。
在特權面前規則總是不堪一擊。10多年下來,電腦派位這個充滿著公平精神的入學規則,早已名存實亡。據家長們統計,全北京不接收派位生的學校已經達到20多所。
條子,票子和孩子
共建生為各個名校帶來了大量的資金、社會資源,但并不能帶來優質的生源。學校的管理者很清楚,長此以往名校也可能會變成爛校。因此,最近3年,又誕生了另外一項制度——推優。主要是由各個小學根據平時成績推薦優秀學生。但成績并不是唯一標準,除此之外,三好學生、各類藝術特長都是錄取依據之一。
在王晉堂看來,這一制度的初衷就是為了保護優質教育資源,因為當時取消了市重點、區重點等劃分標準,必須出臺一種政策來保護原來的重點校,繼續維持教育的不均衡狀態。
事實上,推優原本就是電腦派位制度的配套制度之一。中國各地的電腦派位制度多是借鑒廣州海珠區1990年代的試驗,北京也不例外,廣州的派位制度則直接照搬了當年香港的制度,而香港則基本沿用了英國大城市的入學模式。
電腦派位雖然保證了公平,但卻不可避免地會抹殺一些天賦出眾的孩子。在英國最初制度設計者的思路中,這些是被考慮在內的,因此,電腦派位的同時也輔以擇優選拔,以完成普遍公平與成才效率的有機結合。
在西方國家,擇優選拔權大多都是直接賦予各校校長。名校的校長是享有崇高聲譽的社會職位,人們相信,如果他濫用權力,名校很快就會變為爛校,而且,大多數公民不相信一個聲名狼藉的校長能治理好學校,并給予自己的孩子最優秀的教育。因此,校長的擇優選拔權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純潔。
在中國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以北京為例,名校校長的品格或許并不足夠可信,他也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抵擋權力和金錢壓
迫,但這并不影響他的學校獨占鰲頭,因為那里邊集中了權貴階層的孩子,在每次的政策修訂中,也總會有更多的話語權,政策無論如何改變,總會起到強化自身利益的作用,保證更好的老師、更好的設備和更好的學生。
與電腦派位一樣,推優制度也遭遇了嚴重異化。最近一周,正在進行的如火如荼的特長生考試就是最典型的結果,為了讓孩子們在升學時增加砝碼,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各類以推優為目標的特長培養就開始了。
但無論如何,對于那些無權無勢的普通市民家庭而言,推優畢竟是一條進入名校的小路。一位孫姓的北京家長,在網上建立了一個QQ群,命名為“無權不牛小升初群”,吸引了無數的家長參與,他們建有自己的論壇,每天圍在論壇上討論小孩考初中的門路。
他用了這樣幾句話描述自己孩子的生活:每天回家一小時作業,一小時樂器,一小時奧數,一小時英語,加上磨蹭時間,基本每天晚上11點半睡覺。咖啡和茶水是生活必需品。總結一下,我們是家長沒權,孩子沒才。他的自述引來了無數同病相憐的家長們唏噓不已。
“孩子吹薩克斯吹得嘴都變型了。”這位家長說,我自己都痛恨自己的教育方式,可是,轉念一想,再痛苦也就痛苦這幾年,如果放任不管,孩子只能進入爛校上學,痛苦的將是一輩子。
在北京各類教育論壇上。這個群體都是最活躍的,他們都是普通的北京市民,自認為屬于中產階級,無權無勢,重視教育,將改變家族命運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而改變命運的第一步就是進入名校。“有權的用條子、有錢的用票子,像我們這樣的小市民。只能是拼孩子了。”
到今天,這些北京城里的中產階級家庭早已習慣了特權林立的教育現狀,在夾縫中為自己的孩子開拓空間,付出了巨大成本之后,他們反倒成了這種不公正的教育制度最堅定的擁護者。
2009年,新的教育部長袁貴仁上臺,高調提出了教育均衡化,不僅大力打擊擇校風,更要求各地逐步向外地孩子開放義務教育,這些被媒體呼喚了多年、顯然更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教育訴求。遭遇的阻力卻不僅來源于特權階層,更來源于普通的市民家庭。
“教育部長說要搞均衡化,可為什么不先把教育部的共建校取消了?領導的孩子為什么不接受派位而都是往好學校擠?”那位孫姓家長認定,教育均衡化只是一句騙小老百姓的空話。
在他看來,自己的孩子付出了這么多,卻要跟那些毫不重視教育的家庭一樣,接受電腦派位,學得好不如運氣好,這是一種多么大的不公。更嚴重的是,現在居然那些外地孩子也想跟我們一起來搶奪資源。
他們抱怨特權,卻又無可奈何,只能將所有的憎惡集中于外地孩子身上。
校門外的孩子
丁璇就屬于那個被憎惡的群體。2000年,不滿6歲的她,被常年在北京打工的父母帶到了北京。她的母親章冬翠湊足了5000塊錢借讀費,為她找到了一所小學,這是母親做小時工、父親拉人力車攢下的血汗錢。
在備齊了暫住證、勞動合同、派出所證明等七項證明后,丁璇終于跨進了北京小學的大門。等到升初中時,章冬翠求爺爺告奶奶,跑了幾十家學校,繳齊了各類名目繁多的費用后,最終找到了一所區內較差的學校,丁璇得以留在北京繼續讀書。
父母的付出得到了些許回報,在過去的10年里,丁璇幾乎取得了現行的教育體制下,她能夠獲得的一切榮譽。她是班長、團支書,學習成績一直都是全年級第一名,市、區、校三級三好學生,奧數、英語口語比賽得過一等獎,書法、繪畫、朗誦、作文比賽都拿獎無數,當過奧運志愿者,剛讀高一,就得到了上黨校學習班的機會。
5月底,記者在胡同里找到他們租住的那所陰暗潮濕的舊房子時,她和她的媽媽正興奮于取得的一項新成就:她成為全校僅有的兩名東城區第九次團代會代表之一。
這個15歲的小女孩,并不能完全理解她所參加的每一項活動的價值。她只是用各種辦法試圖證明自己并不比北京孩子差。10年下來,除了數不清的榮譽,她記得最清楚的另外一件事是,初三的時候,全班評選三好學生,她被同學們選上了,但老師卻取消了她的三好學生名額。理由是反正你沒有學籍、不能參加推優、不能讀好中學,這些榮譽給你就是浪費了。
那一次章冬翠大發雷霆,跑到學校跟老師理論,“三好學生評的是孩子的品質,不是戶口。而且教委有文件外地生也可以評三好。”最終,老師將本屬于她的三好學生還給了她。
這讓丁璇意識到,無論如何優秀。自己都不屬于這個城市。初中到第三年時,就開始不斷有老師找她談話,勸她退學,希望她不要參加中考。
初三時的勸退行為,是各個初中針對外地孩子一項普遍的做法。一旦這些孩子在北京參加了中考,并大量涌入高中后,擠占優質學位、降低北京的高考錄取率僅僅是一個小問題,更嚴重的是,在3年之后,當整個城市出現數以萬計的高中生無法參加考試的局面時,將會成為教育部門一個難以回避的尷尬局面。
最終。當初跟丁璇一起在同一所初中上學的75個孩子,大部分都被勸退了,但章冬翠是個認死理的人,“堅決不退學,不管怎樣也不能把孩子毀了。”
丁璇的故鄉是浙江溫州農村,但她早已回不去了,語言不通,從小學開始的教材、考試方式、科目全都不一樣,這些都讓她不得不硬著頭皮留在北京讀高中。
最終,她在北京參加了中考考試,滿分570,在不算其他加分的情況下,她得了527分,這個分數足以讓她上北京最好的高中了,如果她有北京戶口的話。
2009年,為了女兒進高中,章冬翠又開始了奔波,可這一次,她實在無能為力了,跑了幾十家高中,贊助費最少都是4萬以上,這遠遠超出了她這個一貧如洗的家庭的承受范圍。但幸運的是,她碰到了一個好校長。
“我找到22中時。碰到了一個好校長。”章冬翠說,22中的校長是個開明的人,看到丁璇這么優秀,一口就答應收了下來,僅僅按照教委政策,收了1.2萬的借讀費,其他全免了,全年級只有兩個外地生。
丁璇如履薄冰的求學路又一次得到了延續,但3年后的高考該怎么辦?橫亙在面前的高考制度是她再也跨不過去的門檻,縱是倔強的母親、好心的校長也無能為力。
章冬翠也開始泄氣了,“偌大的中國,再也沒辦法為女兒找到一個參加高考的地方。”她也沒有能力像那些有錢的外地人一樣。直接將孩子送到國外去讀大學。
“不能改的高考”
5月份北京市政府廢除了1986年版的《中、小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隨后各區也陸續表態將會把非京籍學生也納入電腦派位范圍,這樣的舉措無疑將會促進越來越多的外地子女進入北京公立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些孩子在北京完成了義務教育之后,該怎么辦?
由于全國各地教材改革、高考改革的進程千差萬別,義務教育完成后,他們無法回到原籍參加高考,如果北京也不為他們打開高考之門,那么丁璇式的困境將會成為越來越普遍的問題,最終釀成巨大的社會矛盾。
但開放高考,則意味著從根本上動搖了北京在教育領域享受特權的基礎,在絕大多數北京市民以及官方眼里,這顯然是一個不可想象的惡果。
作為北京市政協教文衛體委員會的特邀委員,一直在各種場合疾呼教育公平的王晉堂也認為,高考是萬萬不能放開的。“那樣,外地人就會蜂擁而至,北京的教育優勢將不復存在,教育資源也會嚴重不足。”
迄今為止,沒有一項科學的調查報告,對那些外地人的教育意向做過考察,但這種擔心卻根深蒂固。在我們這樣一個極端重視教育的民族,優質的教育資源產生的吸引力會大到什么程度?沒有人能夠斷言。人們都愿意相信,那些外地人就是只為了讓孩子上學,也一定會舉家老小都往北京遷。
但在著名律師許志永看來,這顯然是想當然的結果,“短期內或許會對北京教育秩序造成一定沖擊,但長遠來看,當北京的高考錄取率不再像現在這樣奇高的時候,問題就解決了。”他認為在高考招生時,完全可以逐步實現按照報考人數來決定錄取率。
事實上,根據教育部門的統計,現在在北京的流動人口適齡入學子女有40萬左右,這才是最大的威脅。一旦把所有限制都取消了,這樣一大批學生將會迅速占據大量學位,老北京人在高考體制下享受了數十年的高錄取率將不復存在。
所以,近幾年,隨著北京戶籍學生人數的減少,北京市教育系統寧可合并、減少中學數量,從而保證北京市高考的高入學率,也不愿意招收外地學生。
可以說,就北京教育而言,不合理的高考制度是阻撓教育邁向公平最根本的原因。但改革高考顯然還沒有被提上日程,也許只有當它釀成重大社會危機時,才會被迫改變。
不過,讓人沮喪的不是制度進步的艱難,而是歧視與偏見根植于每個人的心中,在記者接觸的各類家長中。權貴歧視平民。不愿意讓他們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個學校,普通市民歧視外地人,不愿讓自己的孩子與外地人為伍。有錢的外地人歧視那些引車販漿人的后代,害怕他們把自己孩子帶壞。
這樣的教育會為我們的民族帶來一個怎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