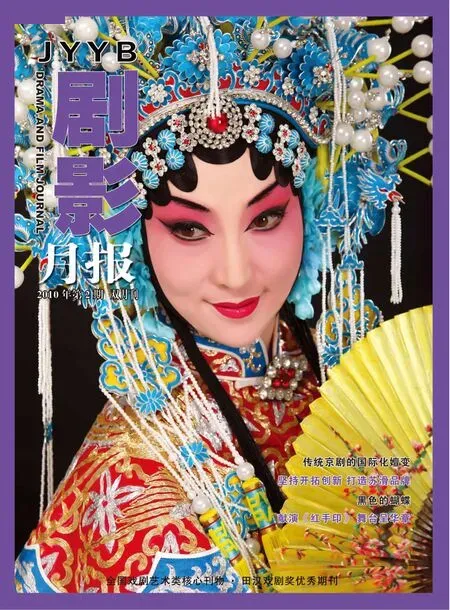小戲也能做成大文章
■顧學軍
“中國戲劇獎·小戲小品獎”是中宣部批準的、由中國文聯和中國劇協主辦的常設獎項,每兩年舉辦一屆。
在2009年11月“第三屆中國戲劇獎·小戲小品獎”大賽中,由我創作的小話劇《歡慶與建國》獲優秀劇目獎、優秀編劇獎(唯一的)兩項大獎。
該劇演出時間26分鐘,講述的是殷歡慶和李建國兩人60年的故事——
1949年,同年同月同日同一個村里出生了兩個男孩,一個叫歡慶,一個叫建國。解放前,歡慶的爸爸是主人,建國的爸爸是長工;解放后歡慶家成份是地主,建國家是貧農,兩家人風風雨雨恩恩怨怨一起走過了60年,歷經了中國各個時期的風浪,見證了祖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和騰飛,也發生了一個個感人至深的故事。
解放初,建國的爸爸聽說地主的兒子也叫建國,便上門興師問罪。經斗爭和協商,地主兒子易名歡慶,貧農兒子叫建國。意在地主仔歡慶貧農兒建國。
1960年,歡慶因營養不良患了浮腫病,命在旦夕。歡慶的爸媽冒著掉腦袋的危險,向建國的爸爸索討解放前的2元錢債。看在“鄉里鄉親”的份上,在政府已經把所有債務一筆勾銷的情況下,建國的爸爸還了那2塊錢,讓歡慶度過了那場劫難。
文革中,歡慶的爸媽為那兩塊錢的事惶惶不可終日,想主動交代自己“反攻倒算”罪行吧,又拍連累建國的爸爸;不交代吧,又怕建國的爸爸揭發出來。就這樣顫顫驚驚、恍恍忽忽、提心吊膽地過了幾年。剛把提著的心放進肚子里,誰知歡慶又闖了禍。禍根是歡慶和建國倆人同時喜歡上了村里一個叫荷花的姑娘。在倆人20歲生日那天,穿上了軍裝的建國,認為自己就是“國家的人”了,想把荷花甩給歡慶,為了促成這份愛情,建國把自己的新軍裝讓歡慶穿上在荷花面前炫耀一下。荷花非但不領情,反認定“四類分子穿軍裝”是大逆不道,并威脅建國“如果你不跟我好,我就大聲喊”。建國只好屈服,把荷花帶進了玉米地才平息了這場風波。
后來,建國在部隊提了干,穿上了四個兜兒的軍裝,跟荷花成了親。再后來,恢復高考,歡慶考上了大學。再后來,建國轉業當了鎮上的書記,荷花成了鎮五金制品廠廠長。1982年,作為恢復高考后第一批大學畢業生,歡慶被分配到荷花手下當了一名技術員。第二年,歡慶把荷花趕下臺,自己當了廠長。又過了二十多年,歡慶把一個當年只有十幾個人的小廠,變成有幾十億資產的股份有限公司。趕上金融危機,歡慶讓兒子頂了自己的班。建國也從鎮黨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并辦了退休手續。于是歡慶與建國終于了了一個共同的心愿:倆人在一起像模像樣地過一回生日。
小戲要小、要精、要簡,歷來是被戲劇理論界所公認的法則。《歡》劇故事容量大,時間跨度長,人物關系復雜,我試圖以中國社會60年前那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為始,以60年為線,以60年中幾個不同歷史時期為點,把兩個家庭三代人的命運變化交織在一起,把新中國成立60年來世態和人情的變遷濃縮在這20幾分鐘內。筆者冒犯小戲創作之大忌的動力在于當下小戲題材相似、主題雷同、人物概念,情節平淡日趨嚴重,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現代觀眾快節奏、新視角、大信息量的欣賞需求。然此舉無疑風險和機遇、成功與失敗共存。








一.選擇題材時的幾分畏懼
時逢建國60周年大慶,以歡慶建國為題創作小戲參賽,自覺題材沾光的同時,也心生幾分畏懼。
1.建國60年的變化太大,無法用一個小戲來完成。否則就犯了小戲創作之大忌。
2.大慶之年,小到歌曲、詩歌、大到電影、電視劇都在炒作這個題材。小戲怎么寫都是炒別人的冷飯。同類題材,寫容易,如何創新?怎樣寫得不一般?難度很大。
3.建國60年來,國人經歷得太多,有太多的事件歷歷在目:斗地主分田地、土地改革、階級斗爭、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等。風風雨雨、坎坎坷坷。這些問題說不清,道不明。小戲一旦涉及政治,更是無法做得鮮活和靈動。
二.創作過程中的幾分恍惚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做人若無畏懼之心,“天不怕、地不怕”,百無禁忌,為所欲為,就會輕浮和膚淺。做作品也是如此。心存畏懼,就有了如履薄冰的謹慎態度;心存畏懼,就有了小心翼翼的戒懼意念;心存畏懼,就有了虛懷若谷的君子風度;心存畏懼,也就有了如負泰山的神圣責任。于是,我又恍惚了起來。
恍惚中,首先想到當年經歷坎坷的人們現在都過上了富裕的生活;香港、澳門回歸了;臺灣和大陸通航了;外國體育代表團來北京參加奧運會,運動員戴口罩入境,國人和媒體也不大驚小怪了;多年漂泊在海外的富人家產也物歸原主了;有點海外關系的僑眷被提拔為僑聯領導了;世界上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已經淡薄了,取而代之的是人類共同面對一個地球,怎么治理環境,怎樣可持續發展,怎么重新尋求新的利益平衡,發展經濟成了重要前提了。
恍惚中,想起了電影《辛格勒名單》,感嘆在那么殘酷無情的年代里,卻有一個法西斯黨員,做出令整個人類震驚的舉動,顯露出人性善良的一面。
恍惚中,又想起了我的干爹。解放前,他是地主,我爸爸是新四軍。一次被敵人追擊,干爹冒險把我爸爸藏在棉花地里十幾天,深夜送吃送喝。后來,他們結成了“把兄弟”;再后來,我就成了地主的干兒子。我長大以后,因為上學和當兵,為了我的前程,父母又為我回避了這段歷史,但父輩人暗中一直來往,直到干爹91歲去世。
幾經恍惚,忽然冒出一個想法:經濟飛速發展的前提是“和諧”,建國60年最大變化是政治上的成熟。于是,腦海里很快浮現出一句至關重要臺詞:“過去的事,該了的都了了”。從這句臺詞展開聯想,似乎任何恩恩怨怨坷坷坎坎都是合理的、必然存在的。因為,一切矛盾沖突的結局是好的——經濟發展了,人們過上了富裕的生活。大家都在向前看,人人都在和諧相處。至此,主題也顯山露水了,歡慶與建國人物形象在電腦顯示屏上也漸漸清晰起來。




三.公開演出后的幾分擔心
《歡》劇第一次公演,演出中,觀眾對作品顯示出濃厚的興趣并不時發出陣陣笑聲;演完后,觀眾騷動不止,議論紛紛。有人說“這個戲有點反動”,有人說“過去還真是這么回事”,也有人說“小戲還能這樣演?膽兒可真大”等等。由戲引發的爭議,讓我為《歡》劇的出路平添幾分擔心。
1.那個年代,年青人唯一出路就是當兵。因為成份不好,歡慶當不了兵,也進不了工廠,只能讀書。人物只能按照知識分子層面走;而建國當兵是因為他不愛讀書,初中都沒畢業。人物這樣定位,是不是在向觀眾傳達——最有文化、最講文明的是地主。
2.歡慶上了大學,有了文化,當了廠長,還把一個幾十人的小廠變成有幾十億資產的集團公司。這會不會引起觀眾聯想——搞經濟建設還得靠他們地主和資本家。
3.60年前,建國的爸爸是歡慶家的長工,主仆關系;60年后,建國兒子是開發區的領導,歡慶兒子是企業總經理。從領導就是服務角度說,他們還是主人和公仆的關系。這一世事輪回,會不會讓觀眾認為時代又倒回到解放前。
4、貧農給地主兒子送滿月雞蛋,還讓地主到自已家里拿幾支洋釘和稻草(修凳子、補房子);大隊支書給有“反攻倒算”嫌疑的地主還兩塊錢;新入伍的建國把軍裝脫給地主兒子穿;鎮黨委書記把自己老婆廠長位置讓給一個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等等我是不是強調了人性善良一面,而犯了嚴重的階級立場方面的錯誤。會不會注重了三代人之間的友情鄉情、兄弟情,而否認了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曾經確實存在過,確實殘酷過,確實過火過。那么,這個故事還有沒有典型意義?會不會為大眾所接受?
自《歡》劇首演之日起,作為編劇,我如劇中那句臺詞一樣,戰戰兢兢、恍恍惚惚、提心吊膽地等待觀眾和評委們的評判。直到我走上領獎臺,稀里糊涂領完優秀編劇獎,我還不能相信這是事實。
四.小戲獲獎后的幾點收獲
1.傳統的創作觀念和技巧,在特定的時期有它存在的意義,但世界潮流在變,編劇的心跳要跟社會前進的脈動保持一致,觀察事物的視角要與時俱進新時期,對從事多年的編劇而言,從“清醒”中回歸“模糊”,創作過程中所產生的畏懼、顧慮和擔心,實際是超越自我的過程——
在我恍惚、猶豫、擔心的創作狀態下,中國劇協藝術發展中心主任周光,收到劇本后回信說:“劇本很有潛力,畢竟今年大慶,用一個小戲寫60年的巨大變化是十分困難的,因此只要寫好了就一定會得到大家的一致肯定”。著名劇作家、評論家、國家一級編劇齊致翔教授看完劇本后說“過去從來沒有人用這種方法來寫這個戲,所以這是一種創新”。進入大賽,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齊士龍點評說“《歡》劇是以一個嶄新的角度來寫的,他用一種嶄新的觀念來處理人與人的關系,寫得很有人情味,立意也很深刻。體現了我們現代人對事物的看法,特別能引起象我這樣年齡的人的很多遐想”。大賽評委、著名小品演員李文啟說“這個戲有點意思,寫得很空靈卻又看得見摸得著,既概括又具體,它用鮮明的音樂形象,為我們烘托了這個時代。”《小戲小品創作園地》在發表這個作品時附言:“《歡》劇在經意不經意之間有意無意地折射出他們背后的大歷史、大時代的變革……”
觀眾和評委的認可,《歡》劇的成功,讓我想起了戲劇大師曹禺一段話:“思想性,政治性,藝術和政治,它們不是兩個門戶,政治就在真實的生活里邊,反映了真實,政治就在里邊了。”
2.小戲不小,小戲也能做成大文章。一位資深專家看完演出后說“《歡》劇有故事,有情節,有人物,有思想含量,如果把這個題材給我,我能寫成二十集電視劇或一部電影。”把“大”做成“小”符合現代人藝術欣賞價值取向。在二十幾分鐘里反映了60年,從一組簡單的人物關系上反映了整個社會的進步,需要借鑒其他藝術形式的優點,如:在各個時期的剪裁上,運用電影技法,把串聯詞如同電影字幕一樣出現;在總體結構上,極力迎合現代人們生活快節奏和其他技術的欣賞特點,讓中心事件發生人物出場之前,演員一出場就把尖銳的矛盾交給觀眾;一個矛盾剛解決,馬上再提出新的矛盾,以此往復,直至結尾。
3.小戲總體風格應力求刪繁就簡。《歡》劇借鑒了中國畫的風格,用一個道具,一段音樂,一套服裝來凸顯一個時代。劇中四個年代,僅用一條板凳、一張太師椅、一張圓桌和一個酒杯托盤,一個演員扮演自家三代人,實現了時空交錯和場景變換,道具由演員自帶上下場,較經濟地利用了舞臺的時間和空間。實踐證明,小戲布景越簡單越能給觀眾想象的空間。
當今社會,人們的文化生活有了越來越多的選擇,各種藝術形態都面臨著形式、內容、主題的創新。作為盆景藝術的小戲,從微觀藝術這個層面來說,更應當思考怎么突破和突破后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