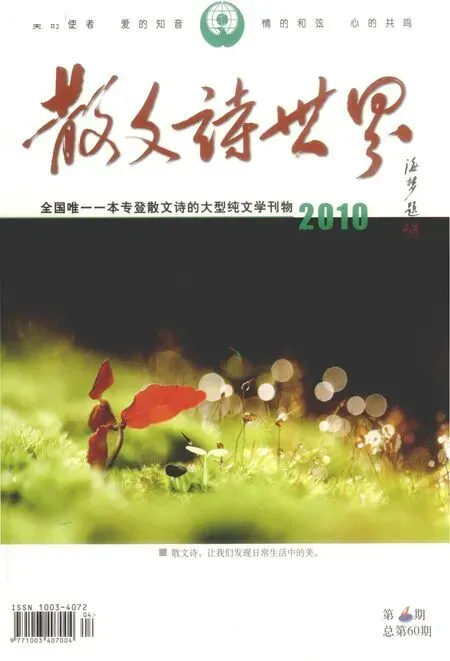向高處看,向遠(yuǎn)處望—在香港散文詩學(xué)會成立十三周年會議上即興發(fā)言
2010-07-12 02:14:34周慶榮
散文詩世界 2010年4期
周慶榮

即將過去的這個(gè)冬天,北方似乎更冷。
來到香港,覺得是春天般的溫暖,原來這里離太陽要近些。
以前,有各種機(jī)會來香港,但總覺得去辦個(gè)通行證太麻煩。而這次因?yàn)橄鸟R主席、祖仁先生及香港詩界同仁的盛情,使我第一次香港之行竟首先與散文詩有關(guān)。
有朋友說,香港離物質(zhì)近,離文化遠(yuǎn)。而我在這里看到的都是一張張?jiān)姼璧哪槪H切的臉。許多前輩一生都在從事散文詩的創(chuàng)作與傳播。我認(rèn)為,在我們的土地上,生長著兩種莊稼:一種是玉米、大麥之類,它們關(guān)乎到人們的溫飽與溫暖;一種是包括散文詩在內(nèi)的文化,它關(guān)乎到人們的精神與信念。
兩種莊稼都是我們?nèi)祟愓滟F的食糧,兩者沒有孰輕孰重之分,就像我們所熱愛的散文詩這一文體,以前或多或少覺得冷清,但作為大的詩歌范疇,散文詩早就是一種客觀存在。散文詩有沒有意義,主要看我們寫作者是否發(fā)掘出意義;散文詩能否從容地站立,亦要看我們自身是否缺鈣。
我們站在大地上,確實(shí)需要向遠(yuǎn)處看,看得更遠(yuǎn);向高處望,望得更高!把小感觸及小感覺升華為大情懷,讓尋常事物有更多的意義性的延伸。
香港曾經(jīng)離世界更近。一個(gè)國家能否有高的格局,能否走得更遠(yuǎn),取決于她的文化。就此而言,我以一個(gè)寫詩的人的激情,對我的國家充滿自信,向別處世界遙望的時(shí)候,總把那里也望成我們自己的家園……
因?yàn)闆]有準(zhǔn)備,只能作一跑題的發(fā)言,謝謝各位。
(3月6日晚,根據(jù)記憶整理)
周慶榮與朋友在一起

左起:宓 月、周慶榮、李 敏、毛國聰
猜你喜歡
新少年(2022年9期)2022-09-17 07:10:54
中國德育(2022年12期)2022-08-22 06:16:18
湖北教育·綜合資訊(2022年4期)2022-05-06 22:54:06
金橋(2022年2期)2022-03-02 05:42:50
金橋(2022年1期)2022-02-12 01:37:04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shù)英綜合(2020年6期)2020-12-16 02:56:41
文苑(2020年12期)2020-04-13 00:54:10
中學(xué)生數(shù)理化·中考版(2019年12期)2019-09-23 06:23:28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shù)英綜合(2018年9期)2018-10-16 06:30:16
北極光(2014年8期)2015-03-30 02: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