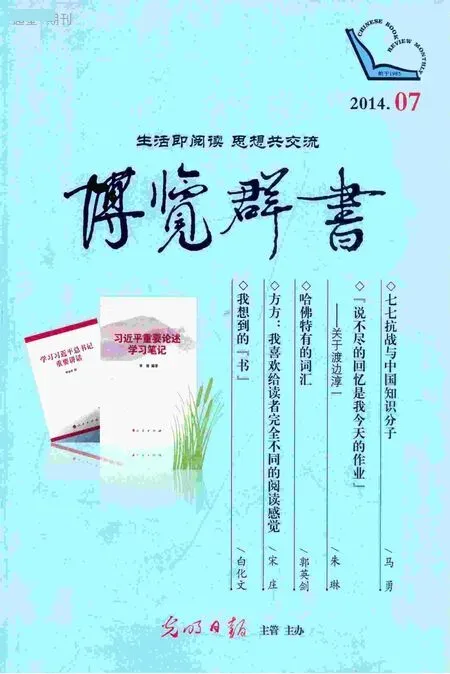漫說高陽的史家功夫
○劉舒曼
體認古人心境,注重描摹細節
高陽以歷史小說名世,剔抉鉤沉的史料功夫卻不為人所知。
不止一位朋友說,看過高陽小說后,對清史產生了興趣。也許有人認為,歷史小說的背景和人物多為真實存在過的,創作起來會比較輕松。其實不然,正因為歷史小說的主人公是真實存在過的歷史人物,讀者自有其想象和評價。而真實的歷史背景,在為創作者提供了大致框架的同時,也為創作者設定了諸多限制,很難進行天馬行空的想象,所謂畫鬼易而畫人難。歷史小說的創作者,需以真實的歷史和虛構的細節互為經緯,小心織就一幅閃亮的錦緞。
高陽無疑是歷史小說寫作的最佳人選。他的腹笥極寬,尤其對清代的人物掌故、風土人情、詩詞文集、典章制度爛熟于心。他寫得最好的幾部作品,無不是以清代為背景,如《慈禧全傳》、《胡雪巖》三部曲、《紅樓夢斷》四部曲等。
《紅樓夢斷》是我所讀的第一部高陽作品。由于個人對《紅樓夢》的偏愛,這些年重讀《紅樓夢斷》及其續篇《三春爭及初春景》、《大野龍蛇》也是最多的。12年前,我剛讀大學,偶有一日,看專業書累了,轉到小說類書架前,發現了高陽的《紅樓夢斷》四部曲。那天抽出《秣陵春》一讀,便放不下手,三天內將《茂陵秋》、《五陵游》、《延陵劍》四部曲全部讀完,仍意猶未盡。《紅樓夢》是一部奇書,作者曹雪芹是位奇人,敢于挑戰這部婦孺皆知的名著,寫出它“背后”的故事,是高陽學術自信的充分體現。
關于《紅樓夢斷》的寫作意圖,高陽在《我寫〈紅樓夢斷〉》中夫子自道:“曹雪芹如何創造了賈寶玉這個典型,比曹雪芹是不是寶玉這個問題更來的有興趣。”高陽何以對曹雪芹的創作心路如此感興趣?或許與他的人生遭際和個性相關。
高陽原名許儒鴻,字晏駢,出身杭州顯赫的許氏家族。家門懸掛三塊御賜牌匾,花廳內的匾額是慈禧太后親筆。他8歲時父親去世,靠母親撫養長大。曾就讀于之江大學,由于戰爭影響,未能完成學業,淵博的文史知識全靠自修。1948年遷至臺灣,1959年起任《中華日報》主筆多年。高陽一生疏于理財,千金散盡。為清償高利貸的利息,動輒將著作版權賣斷給出版社。雖然著述極豐,卻債臺高筑。婚后,妻子郝天俠名下的兩幢房子,都借與高陽抵債,二人結縭十年,于1981年離異。1983年起,高陽與吳菊芬同居,直至逝世,死后還是欠著債。高陽又嗜酒如命,即便酒后不停咯血,也仍是要喝。他說:“人生幾何,對酒當歌,喝酒不能盡興,生有何歡?”與三五好友飲酒談天,是他最為享受的時刻。而高陽最終的病故,也是酒后出血所致。
我們不妨來看看曹雪芹的朋友敦敏、敦誠兄弟對曹的描述:“燕市悲歌酒易醺”(敦敏《芹圃曹君霑別來已一載……》),“新愁舊恨知多少,一醉醉毛白眼斜”(敦敏《贈芹圃》);“接籬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捫”(敦誠《寄懷曹雪芹霑》),“相逢況是淳于輩,一石差可溫枯腸”(敦誠《佩刀質酒歌》),“步兵白眼向人斜”(敦誠《鷦鷯庵雜記·贈曹雪芹》)。在《佩刀質酒歌》的注中,敦誠寫道:“秋曉遇雪芹于槐園,風雨淋涔,朝寒襲袂,時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飲之。雪芹歡甚,作長歌以謝余,余亦作此答之。”曹雪芹嗜酒、佯狂、清談的名士之風如在眼前。
高陽的人生軌跡,與曹雪芹頗為相似。他們均早歷繁華,此后飽受人世滄桑;滿腹經綸,同嗜杯中之物,窮困潦倒而終。高陽的心態和生活方式,不似今人,倒與古代士人更為接近,是個生活在現代社會的“古人”。所謂“借他人酒杯,澆心中塊壘”,高陽在創作歷史小說時,對古人心境的體認,無疑更為貼切。
即便如此,豐滿地再現曹雪芹的早年生活,還是有相當難度的。須知《紅樓夢》的人物情節讀者多能了然,若將曹、李兩家人物與《紅樓夢》簡單嫁接,必然了無趣味。存世的曹、李兩家資料,多以家族男性為主,而《紅樓夢》是一部寫女兒的書,若缺少了女性的內容與形象,《紅樓夢斷》將黯然失色。高陽熟稔清代故實,而且對《紅樓夢》的各個版本極熟,對曹雪芹的創作意圖也有自成一家的深刻體悟。因此,在《紅樓夢斷》四部曲中,真有其人的曹寅、曹、李煦、李鼎、曹雪芹等人固然有生動的描寫,難能可貴的是,高陽摹寫了曹、李兩家家族史中若隱若現的女性群像。這些女性形象,既暗合于《紅樓夢》中諸女的命運,又不是《紅樓夢》情節的機械重復。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很顯功力。從主子輩的李太夫、曹老夫人、馬夫人、鼎大奶奶、震二奶奶,到丫鬟輩的秋月、春雨、小蓮、楚珍,依稀可見《紅樓夢》中賈母、王夫人、秦可卿、王熙鳳、鴛鴦、襲人、晴雯、金釧的影子。
我研習明清史多年,對歷史小說中涉及史實的部分非常挑剔,但高陽經住了我的“考驗”。他不僅把握了歷史大脈絡,而且細節描述也能落到實處。這一點殊為不易。有些歷史小說的作者,粗線條勾勒時尚能蒙混過關,進入細部描寫立馬露餡。高陽的歷史小說最令人著迷之處,是強烈的“歷史現場感”:通過對史實的精準描摹和細節的合理虛構,鮮活地呈現歷史中的生活場景和人物形象,令閱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可以說,高陽藉由小說這一形式,對歷史進行了還原和重現。這些在《紅樓夢斷》四部曲中都有充分的展現。
作者在史實方面的細致隨處可見,如《秣陵春》的開頭,因李鼎奉命往熱河行宮送桂花,才鬧出一場家變。送桂花確有其事。康熙皇帝十分喜歡桂花,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傳旨李鼎從江南“送丹桂二十盆至熱河,六月中要到”。李煦回旨說“奴才即督同兒子李鼎挑選桂花,現在雇覓船只裝載,即日從水路北行”。及至李鼎趕回蘇州,一場家變已經釀成。
生活細節方面,高陽更是不輕易放過。熟悉《紅樓夢》的讀者當然記得書中種種令人垂涎的美食。高陽本人精于飲饌,寫來格外輕松。李府辦老太太的喪事,為吊客端上茶點,是“一碗六安瓜片,菜泥包子、花素燒賣、芝麻松子餡的蒸餃、棗泥核桃方糕”。這四色點心,又是曹家震二奶奶指點廚子做出來的。曹雪芹似乎很愛寫用鵝制成的食物,比如胭脂鵝脯、鵝掌、松穰鵝油卷等。高陽寫震二奶奶回南京時,途經無錫,薛姓商人送來路菜,震二奶奶留下“生片火鍋、一只烤過再煨湯的鴨子,一碟糟釀子鵝”。
曹震送丫鬟繡春的兩樣東西,碧玉耳墜“是小小的一個連環形,上鑲掛耳的金鉤,下垂極細的金鏈,吊著一枚六角長形,上豐下銳的金剛鉆,材料形制,精致異常”。金表則是“景泰藍的底面,周圍鑲珠。撳機鈕打開蓋子,表面與眾不同。一晝夜分成二十四格,正中上下都刻著羅馬字‘十二’,外圈每兩格注明地支,上面的‘十二’是午,下面的十二是子”。種種生動細致的描寫,會讓讀者更為迅速地融入文本的情境。
也許是因為讀書人“掉書袋”的習慣,對所了解的歷史掌故不吐不快。也許是生活所迫,不得不將故事拉長。高陽在敘述一件事的時候,往往喜歡將文筆宕開,牽扯其他不相干的史實或人物,大大鋪排一番。讀者固然會因此佩服作者的見識,其結果卻導致讀了半天,還得從頭再看究竟說的是哪一樁事情。這一缺點在《紅樓夢斷》中已有體現,但尚不明顯。其后期的一些作品,枝蔓過多的毛病就愈加突出,在閱讀時要加以留意。
詩史互證的深厚功力
如果說歷史小說是高陽借以復原歷史的明面,那么詩詞就是他闡釋歷史的暗面,較之歷史小說的眾多受眾,顯得不太為人所知。《高陽說詩》曾獲1984年中山文化學基金會“文藝理論獎”。高陽的歷史“野心”和抱負,在薄薄一冊的《高陽說詩》中一覽無遺。
近代以來,詩歌這一古人運用自如的技藝,漸漸凋零殆盡。我們已很難想象,詩歌曾經作為古人情感的載體,那樣普遍地存在于他們的生活之中。高陽于近代學術人物中獨重陳寅恪,就是佩服陳氏“詩史互證”的深厚功力。高陽曾說:“我作考證,師法陳寅恪先生,以窮極源流為尚。”他在《高陽說詩》中專門寫有《“雙山”一手陳寅恪》一文,箋注了陳氏的幾首詩。他推崇陳氏以李義山為里,白香山為表,“雙山”集于一手,精于用典卻不著痕跡,是難得的詩壇高手。陳氏研究歷史的特點,是由他人未予足夠重視的常見材料入手,抽絲剝繭,最終得出令人咋舌的結論。陳氏于古體詩的典故信手拈來,詩是他經常使用的材料之一。從早期的代表作《元白詩箋論稿》,到晚年瞽目臏足時寫就的《柳如是別傳》,莫不如是。
而《高陽說詩》,則是高陽自己“詩史互證”的一次實踐。《高陽說詩》共14篇,考證時間范圍從唐代直至民國,內容包括杜甫的《詠懷古跡》的自況心跡,李商隱《藥轉》、《錦瑟》、《無題》諸詩的本事,對清初詩壇巨擘吳梅村的評價,“江上之役”詩紀,董小宛入清宮始末詩證,納蘭性德其人其詞述評,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解析等等。高陽一一射覆,娓娓道來。
高陽選擇考察詩詞本事的對象皆有相當難度:唐代詩人中,老杜稱“詩史”,隱晦之句尚不算多,而李商隱做詩用典之偏僻,詩意之飄渺是公認的;清代文網嚴密,如吳梅村等遺民,寫詩慎之又慎,多用曲筆,為箋證增加了不小的難度;今人詩詞難于箋注亦是不爭的事實,而況是長于用典的陳寅恪。解這些難題才能顯出一個學者的功力深淺。
以詩詞證史是一樁相當冒險的事。古人的詩詞,除去應酬部分之外,多為抒發一己情感隱衷,其中曲折,只怕本人才能說清。后人若想還原當時的情境,難免有想當然的成分在內。失之毫厘,便謬以千里。高陽算得上個中高手。即以李商隱為例,《高陽說詩》中有三篇專釋李詩:《白日當天三月半》、《釋〈藥轉〉》及《〈錦瑟〉詳解》。《白日當天三月半》所釋為《無題》之第四首,高陽反彈琵琶,認為《無題》諸詩不難解,后人過分將其與牛李黨爭相關聯,以致附會穿鑿,將感情詩解為政治詩。他以為四首《無題》有兩個歌詠對象,一為李商隱的小姨,一似為王茂元的家伎。高陽對《無題》頗為偏愛,一篇文章尚不過癮,另著《鳳尾香羅》一書專做發覆。而水晶以為“不知所云”、邢杞風視之為謎的《藥轉》詩,高陽直截了當地指出其為登廁詩。水晶、邢杞風因不明“長籌未必輸孫皓,香棗何勞問石崇”一聯中所用典故,或認為是墮胎詩,或說是諷刺達官貴人和女道士偷情,讀來實在令人忍俊不禁。《錦瑟》一詩,高陽考訂出李義山因《牡丹》詩遭人讒言,致使令狐誤解其與媵妾私通。而義山因妻妹已嫁,顧其名節,無法向令狐解釋《牡丹》乃贈小姨之作。至令狐之子令狐高,誤解愈積愈深,累得義山半生蹭蹬。李義山臨終匆匆編平生詩三卷,以《錦瑟》為首,既為求得令狐父子諒解,亦有托孤之意。這三篇考訂文章,都寫得十分精彩。
但即便是高陽,解詩也有不“中”的時候。如對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中“南齋侍從欲自沉,北門學士邀同死”一聯本事,高陽以為“北門學士”為羅振玉,“頗疑為癡心女子以死相要、而負者相約同殉,以堅其必死之志,結果女死而男活”的典故。而據陳先生的弟子蔣天樞上世紀50年代親聆其師的解釋,“南齋侍從”是羅振玉,“北門學士”則為柯劭,“羅、柯曾約王共投神武門外御河殉國,卒不果”。由此可知“今典”索解不易,亦不能苛責高陽。總體說來,《高陽說詩》的觀點還是令人信服,能夠自圓其說的。
高陽還有一部分作品介乎歷史小說與嚴肅的歷史考訂之間。如《明末四公子》、《清末四公子》、《清朝的皇帝》等。《明末四公子》付梓時,臺北發生所謂“誹韓”案,即韓愈第三十九代直系親屬狀告郭壽華的文章誹謗先人,臺北地方法院判原告勝訴,引發文藝界軒然大波。在此書代序《歷史公案惟有歷史能裁判》中,高陽寫道,“不僅‘身后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的詩句可以證明中國向來有褒貶古人的言論自由,而且在世受人誤解,而居心行事有自信者,往往亦表示,‘身后千秋付史評’。”高陽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研究的態度可見一斑。高陽常言:“學問乃天下之公器。”他的歷史小說寫作,詩史互證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還原了歷史姑且不論,這種治學態度和學術精神實在是值得我輩好好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