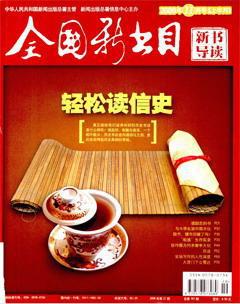我所經歷的“九.一三”
符 浩
本書選編了蕭乾、鄧拓、豐子愷、羅以民、敬一丹、史鐵生、胡絜青、符浩、郭超人、莊則棟、魯光、戴煌、章含之、畢淑敏等65位作者的文章共60篇,從政治、經濟、文化、體育、社會生活、時代人物6個方面,來展示新中國60年來的變遷。其中,有關乎“國家”的宏大敘事,也有關乎“個體”的具體而微,有輝煌,也有疼痛。
林彪外逃,機毀人亡
1971年9月13日下午,外交部辦公夫樓里,人們進進出出,一如往常,沒有任何異常現象。但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已知道林彪和葉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飛機于13日零點32分山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標很可能是某個外國。周恩來總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電報道,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種右能的情況下的交涉或應對方案。
14日上午,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在會議室開會,會議由核心小組組長、代理部長姬鵬飛同志主持,內答是進一步落實周總理昨天的指示。會議的氣氛不像往常,而是有一種嚴峻感。但大家都很鎮定,會開得有條不紊、從容不迫,對林彪出逃作了四種估計:
一、由林彪出面公開發表叛國聲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過外國廣播或報紙發表講話;
三、林彪及其追隨者暫不露面,也不直接發表談話,由外國通訊社客觀報道林彪等已到達某國某地;
四、暫不發表消息,以觀國內動靜。
會議還詳細討論了在各種情況下對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態的問題。
時間過得真快,中午12點的鐘聲已經敲過,但會議還沒有散的意思。這時,緊閉的房門被突然推開,值班秘書忘了平時的禮節,快步徑直奔向姬鵬飛同志。鵬飛同志以他耶特有的沉著和冷靜接過一份手抄特急報告。我們的目光注視著他臉上的表情,部急于想知道報告的內容。從每個人的臉上都可以看出,這是一份極不尋常的“特急件”。隨著他目光離開文件,臉上綻出了笑容,用一種異常的語調向大家說道:“機毀人亡,絕妙的下場!”接著把報告讀了一遍。
原來這是我國駐蒙古大使館,使用中蘇關系惡化后已封閉兩年多的從烏蘭巴托直通北京的高頻專線電話傳來的報告。大致內容是:9月14日上午8點30分,蒙古副外長額爾敦比列格緊急約見許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國噴氣式軍用飛機于13日凌晨2時左右墜毀在肯特省貝爾赫礦區以南十公里處。蒙有關部門在當日上午得知此事后,即派人到出事地點察看,經多方證據表明,這是一架屬于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的飛機。機上共有九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蒙方對我國軍用飛機深入蒙古領空,向我提出口頭抗議,要求我方說明飛機深入蒙領空的原因。許大使向對方提出我方要求到現場調查。
這個報告使會議的氣氛活躍起來。韓念龍同志從姬鵬飛同志手里接過報告,逐字逐句仔細看了一遍——因為對蒙古的事務由他主管。
會議當然不能結束。一個最緊迫的事,就是要把這份報告迅速送給毛主席和周總理,這也是他們急切等待的消息。姬鵬飛同志立即要王海容同志打電話到主席和總理辦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總理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沒有合過眼,剛剛服過安眠藥入睡,總理按習慣要4個鐘頭以后才能醒來。主席和總理辦公室的同志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在這種情況下,黨組決定:立即派人把報告送給主席和總理看,否則就是失職。同時,再一次和兩個辦公室的秘書通電話,強調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別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總理叫醒。
下午兩點鐘過后,我剛剛回到辦公室,從抽屜中找出一包蘇打餅干,權作是午餐。還沒吃兩口,姬鵬飛同志就叫我去他的辦公室。正巧他也在吃餅干,我也就不客氣地不請自拿了。他邊吃邊告訴我,總理來電話說,他剛從主席住處回來,對外交部的同志迅速把報告送到并叫醒他們感到滿意。總理特別對我駐蒙古大使館,在不了解實際情況下,為了使國內盡快知道我機在蒙古境內失事,當機立斷,啟用已經封閉兩年多的專用電話線,以最快速度把情況傳回來表示滿意。接著講到總理交辦的幾件事,要我立即去辦。
總理的指示有:一、將今天收到的我駐蒙古大使館的報告用三號鉛字打印18份,下午6時由符浩親自送到人民大會堂北門內,交中央辦公廳王良恩副主任;二、從現在起,指定專人譯辦我駐蒙使館來的電報,由符浩親自密封后送總理親啟;三、今天的報告,凡經辦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絕對保密。
二人對酌,喬公改詩
因昨夜幾乎沒有睡覺,我回家吃過晚飯后,便想利用這個時間小憩一會兒。但實在太興奮了,怎么可能睡得著。我便信步來到住同院的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同志家里。他一看到我就哈哈笑道:“說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打電話請你來呢。”我也笑著問道:“今晚有什么好節目?”“當然有。”他略有些狡黠地眨了下眼,說道:“我前幾天從箱子里翻出一副章太炎書寫的對聯,剛剛掛上,特請你來一賞。”進了他的書房后,果然壁上新換了一副對子,章太炎篆體書寫的有碗口大小的字,蓋出自太炎先生晚年之筆,神完氣足,味道淳古雋永,在他的墨跡中應屬上品。文日:“龍驚不敢水中臥,猿嘯時聞巖下音。”這是節錄李白《夜泊黃山為殷十四吳會吟》一詩中的兩句。喬冠華聽到我連聲贊嘆,很是得意。他特意指出其中的幾個頗為古異于通常小篆的字說,這幾個字選字得體,尤見太炎的功力。他告訴我說他特意請翟蔭塘同志查出這幾個字由石鼓和彝器中的出處。賞玩了一會兒,兩人的目光不期而遇,他悠悠地說道“該言歸正傳了。”我們不由得放懷大笑起來。
這兩天,我們都太興奮了,也都太緊張了,本急欲暢談一下。林彪叛逃事,那時還不能和家人、朋友談,只能在“知情者”間談。從何談起呢?賞玩太炎這副字,好像使我們都松弛了好多。
我們圍繞著“林彪叛逃,機毀人亡”的主題談了起來。他拿出一瓶未啟封的茅臺,我們邊談邊飲,興致達到了高潮。我又抬頭望著那副對聯,突然想起了另一位唐人詩句,脫口誦出:“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喬冠華聽后,沉思了一會,突然將滿杯茅臺一飲而盡,對我說道:“賈寶玉不是說述舊不如編新嗎?我把這首詩略加改動,你看新意如何。”他又斟滿一杯,端在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蘇北口音吟了起來,吟畢又一飲而盡,真是豪興沖天。后來郭沫若同志看到了他的這首新“塞下曲”后,曾揮毫將此詩書成條幅并加贊語贈給喬冠華:
月夜雁飛高,林彪夜遁逃。
無需輕騎逐,大火自焚燒。
巧合無間,妙不可言。囑題小幅一軸,欣然命筆,以示奇文共欣賞,好事相與祝也。冠華同志座右,望常拍案警奇。
絕對保密,慎之又慎
9月15日下午3時30分,我國駐蒙古使館報告:許文益大使及隨行人員共4人已于下午2時離開烏蘭
巴托去飛機墜毀現場視察。現場周圍覆蓋著三四十厘米高的茅草,飛機著陸點正好在比較平坦的盆地中央,在著陸點以南約30米長的草皮被飛機腹部擦光,西側平行處,是右機翼劃出的深約20厘米的一道槽溝。再往南,擦地痕跡消失了,進入燃燒區,草地燃燒面積長800米,寬度由北邊的50米擴展至南面的200米,呈梯形。在燒焦地上散落著大大小小的飛機殘骸,被炸斷的機尾上可以看到五星紅旗和“256”等標記。在完全燒毀的機頭以北50米處,散放著9具尸體,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開,頭部多被燒焦,面部模糊不清,難以辨認。到現場的同志把尸體由北向南編成一至九從各個角度拍了照片。據事后驗證,一號尸體是林彪座車司機楊振綱;二號尸體是林立果,衣服全部燒成焦麻狀,死前似在烈火中掙扎過;三號尸體是林彪的秘書劉沛豐;四號尸體是特設機械師邵起良;五號尸體是林彪,瘦削禿頂,頭皮綻裂,頭骨外露,眉毛燒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燒焦,脛骨炸裂,肌肉外翻;六號尸體是機械師張延奎;七號尸體是空勤機械師李平;八號尸體是葉群,是唯一的女尸,燒灼較輕,頭發基本完好,左肋部綻裂,肌肉外翻;九號尸體是駕駛員潘景寅。許大使他們在現場察看時發現,每具尸體腕上都沒有手表,腳上沒有鞋子,看來是在飛機緊急降落前,為避免沖撞扭傷,他們都作了準備。許文益等同志在蒙方人員協助下,按照蒙古人的習俗,掩埋了死者的尸體。
請示總理后,我用專線和許文益同志通了話,告其速派專人送回有關資料,并面報詳細情況。
9月18日凌晨1時,使館報告,決定派二等秘書孫一先送現場照片、目測示意圖和有關材料回部,并當面匯報。
第二天晚上駐蒙使館又報告,孫一先于20日乘4次列車離烏蘭巴托回國。
9月21日下午3時30分,從烏蘭巴托開來的國際列車準時到達北京車站。我和秘書王萬慧同志早已到車站等候。孫一先和中建公司的賀喜同志同車到達,一下車我們就迎上去。孫、賀兩人和我們打過招呼后,又東張西望。顯然,孫一先并不知道我們是專程來接他們的。王萬慧同志把孫一先同志拉到一旁,我低聲對他說:“我就是來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暫住招待所。”關于賀喜同志,原來我們不知道他與孫同車回國。我正在猶豫是否要賀喜同志一起到招待所時,賀單位的同志來接他了。我先跟他打了個招呼關于我國有一架飛機墜毀的事,沒有公開之前要保密,不能外泄,家里人也不能說。
來到外交部招待所早已準備好的房間,孫一先同志便把從使館帶來的文件和現場拍攝的膠卷交給我,我馬上要王萬慧同志先把這些東西帶回部,把文件交給部值班室主任徐連儒同志妥為保管,膠卷交給正在待命的孫秀娟同志沖洗。然后,我對孫一先同志說:是周總理要我來車站接他的。并告訴他飛機墜毀,情況很復雜,要絕對保密。并向他交代了幾條注意事項:第一,暫住招待所,不得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內到處走動;第二,不要同外面聯系,包括親屬和所屬單位;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說是臨時回國送文件,現在正等文件,隨時準備返館,有關飛機的事,一句也不能講;第四,隨時準備匯報。并將一個電話號碼和外交部值班室主任徐連懦的名字寫給他,如果有事可與徐聯系。
晚上11時許,我和姬鵬飛、韓念龍等同志來到大會堂福建廳,總理早已到了,正伏案批閱文件。我們盡量在離他較近的沙發上坐下,低聲研究有關問題。大約半個小時后,孫一先同志被領了進來。周總理和他握手后,突然回過頭來問我,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誰。還沒等我講完有關賀喜同志的情況,他一聽說賀喜已回家,便面色一沉,那雙濃眉猛然一蹙,厲聲打斷我的話:“你當過兵嗎?”霎時間,我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總理對外交部的許多干部的經歷是十分了解的,他當然知道我曾在部隊里工作過。記得第一次單獨見總理,是在1950年的7月,我被任命為駐蒙古使館臨時代辦,因為是新建館,臨行前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聽完總理的指示起身告別時,總理半開玩笑地指著我說:“已經是外交官了嘛,怎么還穿軍裝?”此時此刻,總理問“你當過兵嗎?”分明是批評我的警惕性跑到哪里去了。他嚴肅地審視著我,我立即回答:“我馬上把賀喜找回來。”
約一個半小時后,服務員請我到隔壁房間接部值班室的電話,說已按我的交待把賀喜同志從酣睡中叫醒,并已送進招待所佳下,待孫一先同志回去后向他轉告注意事項。此時,我真有如釋重負之感……
過細研究,臨行叮囑
孫一先匯報完情況,我看了一眼手表,已是22日凌晨2時多。服務員送來了夜餐,每人一碗熱湯面,唯獨總理外加了一小碟花生米。據經驗我知道會還要接著開下去。果然,先是李德生和鄺任農同志到了,緊跟著是吳法憲。總理把現場照片交給他們傳看,同時把另一套照片交給楊德中同志,并說,由你主持研究一下,飛機究竟是怎樣墜毀的,又對我說:“你也參加。”
楊德中同志和我來到東大廳,公安部長李震、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等已坐在那里等候。等他們看過照片和示意圖后,我根據孫一先的匯報和使館的報告材料,做了必要的說明。然后大家進行分析、討論,最后一致認為李際泰同志的分析有道理。他的看法是飛機因燃料將要耗盡,被迫做緊急著陸的準備,駕駛員不熟悉較大區域的地面情況,于是選擇一塊平坦的地面,冒險以飛機機腹擦地降落。但在飛機著陸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傾斜,觸及地面,與沙石沖磨,驟然升溫引起油箱起火,從而導致全機爆炸。看來,駕駛員還是有一定經驗和技術的,選擇了野外迫降的處理辦法。當然,也不排除其他原因,例如,機件失靈,或被地面炮火擊傷而墜落,或擊傷后被迫著陸,但這些可能性較小。因為地面上有飛機滑行的痕跡和大面積的燃燒。如果是在空中爆炸,殘骸會分布得很廣,地面也不會形成大面積的燃燒。楊德中同志認為有必要找一架同類型飛機井和駕駛員及有關地勤人員研究一下,大家贊同這個辦法。我又建議,最好把孫一先同志也帶去。
早晨4點多,楊德中同志又向總理匯報分析結果。我走出大會堂北門,天色微明,回頭望去,福建廳的燈光從窗紗中透出,總理仍在工作。
9月26日晚,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里,仍按原計劃出國訪問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全體人員正在向總理匯報準備情況并聽取指示。我作為代表團的成員,離總理坐得很近,燈光下,我發現總理半個月來明顯地消瘦了,但清癯的面孔卻有一種喜悅和輕松的表情。我們告別總理快要走出北門時,一位服務員從后面趕上未對我說:“符浩同志,總理請你去西大廳。”我一怔,顧不得多想,便疾步返回。
大廳里只有總理一人,他看我站在那里等他的指示,便擺手示意讓我坐下,他好像在思考著什么。這時我猜想,莫非有了什么新的任務要我去做,可又不便主動提問。總理終于開口了:“你明天一早就要動身去巴黎了,有關林彪叛逃的事,見到黃鎮同志時,把情況告訴他。”他頓了一下,語氣更加鄭重地接著講道:“中央已決定逮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這些也告訴他。”并叮囑說,只告訴他一個人。
9月29日,我們輾轉抵達巴黎。當晚,我就前往我駐法大使館邸。與黃鎮大使說笑一番后,我暗示他,奉總理之命有要事轉達。他拿著打開的小半導體收音機踱到花園的草地上,一邊漫步,一邊談了起來。顯然,他對帶來的信息,非常興奮激動,我們情緒相互感染,長時間沉浸在喜悅之中。